“绝对不是靡靡之音” ——青年巴金这样回击“造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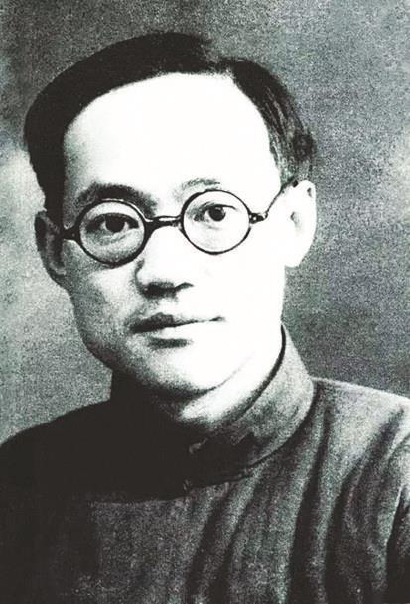
青年巴金
1931年2月,广州《万人月报》第二期“批评”栏,刊有一篇署名“巴金”的文章《〈死去的太阳〉及其他》。该文未曾收入巴金的任何集子,在《巴金年谱》《巴金著作系年》等权威的巴金研究文献中也未查找到有关记述,当是佚文。而该文的写作与发表,却与沪上一家小报对巴金的“造谣”有关。
小报的”造谣”
“巴金研究集刊卷八”《你是谁》刊发的祝均宙《巴金早期史料钩沉》一文,记述了小报“造谣”一事。1930年11月28日,巴金26岁生日才过三天,上海《福报》“新文坛短讯”栏目刊出署名“小侦”的三则“短讯”,涉及他和沈从文、赵景深。现将关于巴金的一则“短讯”抄录于下:
巴金,便是以创作长篇小说《灭亡》著名的巴金,他已往沸着热的血写出那时代之声作品的勇气是没有了,他最近的作风是一转变而成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他那以前喊出的时代之声,确是随着《灭亡》而灭亡去,现在叫出的是“靡靡之音”了。
那时,巴金是一颗刚升起的文坛新星,受到小报记者的“关注”亦属常事。这次小侦批评巴金“最近的作风是一转变而成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应是针对刊于7月10日《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七号的短篇《洛伯尔先生》。该小说用诗歌引出故事,以第一人称叙事,是巴金“作风”转变的代表作品,后收入第一部短篇集《复仇》(新中国书局1931年版)。巴金在该作品集的“自序”中提及:“这几篇小说并非如某一些批评家所说是‘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
从“短讯”可看出,小侦对《灭亡》的评价并不低,认为这是巴金“沸着热的血”“喊出的时代之声”。但对于《洛伯尔先生》,小侦不仅对创作“作风”提出批评,还指摘这种将诗歌直接引进小说的抒情是“靡靡之音”。
12月19日,《福报》发表一篇署名“声燕”的短文《〈灭亡〉的著者巴金的话》。作者“疑惑小侦君的造谣”,“又为巴金君惜”,对小侦的言论提出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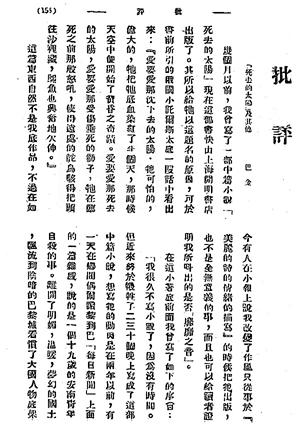
广州《万人月报》创刊号,该刊1931年第二期 “批评”栏发表巴金的署名文章《〈死去的太阳〉及其他》
声燕认为,“巴金君不但是致力于文学而且又很努力于求全人类解放的热情者”,“像他这样的文学者,我们贵国实在不多呢”。作者更相信巴金“不是那些花月文学家,也不是普罗文学者”,于是“忍不住写信去询问”,并“私自公开”了巴金复信中的一段话:
至于《福报》所载关于我的消息更无答复或表示之必要,我写小说是要申诉自己的悲哀,亦即是我所感到的人类的悲哀。我始终反对把文学作宣传工具。文艺是表现人生的面相,并不如某一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我的材料取自各方面。我为自己而写小说,在我是非怎样写不可的。别人的批评我当然不管而且别人也不了解我。我近来的短篇小说具在,《福报》的话,明眼人当然不会相信。承你关切故告。
这段“巴金的话”,表明了巴金的创作态度,间接回应了小侦的“造谣”,也为自己作了“辩护”。
但事情并未结束。在复信声燕后,巴金又很快写成这篇《〈死去的太阳〉及其他》,直接对小侦给予了回击。
“绝对不是‘靡靡之音’”
巴金在给声燕的信中说“更无答复或表示之必要”,为何又著文回击小侦呢?
笔者以为,在给声燕的信中提到的是“近来的短篇小说”,但在巴金看来,能够反映自己创作态度的,还有“快”出版的《死去的太阳》。就如文章的题名,巴金要表达的是,中篇《死去的太阳》及“最近写的一些短篇”叫出的都不是“靡靡之音”。
对“快”出版的《死去的太阳》,巴金明确指出:“在如今有人在小报上说起我改变了作风只从事于‘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的时候把它出版,也不是全无意义的事,而且也可以给读者证明我所叫出的是否‘靡靡之音’。”巴金并用超过全文一半的篇幅,差不多全文抄录了《死去的太阳》的“序”,因为在他看来,这篇“序”文“很可以表明”自己的“创作态度”。
小侦的“短讯”刊出前,巴金已在当年发表了六个短篇:《房东太太》《洛伯尔先生》《亡命》《复仇》《苦人儿》和《谢了的丁香花》,他在文中虽未提及这些篇名,但提到几个“主人翁”:“意大利的革命党”“复仇的犹太人”“失恋的法国老音乐师”“薄命的法国女子”“监狱中的俄国囚徒”。从这些异域的故事中可看出,他们的爱与恨、欢乐与受苦,反映了普遍的人性价值问题。为此,巴金非常自信地给予了“回击”:这些短篇小说“绝对不是‘靡靡之音’”。
巴金在最后说:“知人莫如己,所以与其写文章评论别人,还不如说几句关于自己的话。当作‘自白’也可,当作‘自辩’也可。”确也如此,在文中并没有多少“火药味”,而是告诉自己的读者,我做了什么。笔者以为,这是“自白”,又 是自我“辩护”,恰恰是最好的“回击”。
该文未署写作时间,可确认的是,该文完成的时候,《死去的太阳》尚未出版。该书由索非编入“微明丛书”于1931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前刊有作于1930年6月的“序”。与文中抄录的作比对,发现有细微变化,比如删去了“而且题名也不是以前所假定的‘黄祸’两字了”一句。显然,巴金在付印前对“序”作了删改。一般说来,1月出版的书,最晚应在上年12月底付印。笔者由此推断,巴金12月下旬完成该文后,对“序”作了删改,月底该书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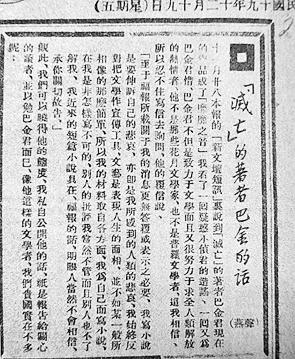
《福报》发表署名“声燕”的短文《〈灭亡〉的著者巴金的话》

《福报》“新文坛短讯”栏目刊发署名“小侦”的“短讯”,涉及巴金等人
从删去的这句看,《死去的太阳》“以前假定”的题名是《黄祸》,初稿完成定为《新生》,托索非转给《小说月报》,但很快被退回,说是写得不好,巴金“很失望”。几个月后作了修改,改为现名,文中也说到改名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该文有1700余字,“序”1000字左右,剩余的700来字,有的引用了先前的文章,有的又被后面的文章所引用。
引用的先前文章,比如1929年写的《〈灭亡〉作者底自白》,只是在文字或语序方面稍有改变。《自白》中的“我从生活里面得到一点东西,我便把它写下来”,改为“我终于获得了一点东西,我便把它写下来”;“我不是为想做文人而写小说”,则改为“我之所以写小说,并非是想做文人”,也有了点“自辩”的味道。
巴金在为短篇小说集《复仇》写的“自序”中提到几个短篇的“主人翁”时,引用了该文的文字。比如,“他们都是同样的有人性的生物,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幸福,爱情。失去了这一切后所发出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而把“凡是曾经感到与我底主人翁所感到的同样的悲哀,曾经追求过与我底主人翁所追求的东西的人,当然会明白这意思”改写为“凡是曾经与他们同样感到,而且同样追求这一切的人,当然明白这意思”写入了“序”。
巴金如此回击“造谣”
最后,把原文抄录于下,从中可看到巴金如何回击“造谣”:
几个月以前,我曾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现在这部书快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其所以给它以这题名的原因,可于书前所引的俄国小托尔斯太底一段话中看出来:“爱要爱那沉下去的太阳,它可怕的,伟大的,它把它的底血染红了半个天,那时候天空中便开始了黄昏之奇迹。爱要爱那死去的太阳,爱要爱那受伤垂死的狮子,它在临死之前那般怒吼,使得远处的鸵鸟骇得把头往沙里藏,鳄鱼也兴奋地欠伸。”
这篇东西自然不是我底作品,不过在如今有人在小报上说起我改变了作风只从事于“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的时候把它出版,也不是全无意义的事,而且也可以给读者证明我所叫出的是否“靡靡之音”。
在这小著底前面我曾写了如下的序言:
我很久不写小说了,因为没有时间。但近来终于牺牲了二三十个晚上写成了这部中篇小说,想写它的动因是在两年以前,有一天在乡间偶尔读黎巴到(应为读到巴黎)《每日新闻》上面的一篇杂感,说的是一个十九岁的安南青年自杀的事。离开了明媚,温暖,梦幻的国土,飘流到阴暗的巴黎城看惯了大国人物底架子,受尽了弱者底种种苦痛,在一个凄凉的月夜里听见街头有人在唱《安南之夜》的情歌,这时候那个逃不出,‘狭的笼’而回到温暖的树林的文弱的安南青年只有走自杀的路了。这种心情当然是法国人所不了解的。
……
这篇序言很可以表明我底创作态度。诚然我最近写的一些短篇在形式上与《灭亡》甚至与这《死去的太阳》都有了显然的差异,但实质上我却不承认他们有什么大的差别。所谓“美丽的诗的情绪的描写”(?)不过是一种装饰,骨子里还是满溢着热情,永远不能熄灭的热情。我底主人翁无论是一个意大利的革命党,复仇的犹太人,失恋的法国老音乐师,薄命的法国女子,或监狱中的俄国囚徒,他们都是同样的有人性的生物,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幸福,爱情。失去了这一切后所发出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这不是感伤,这是呼吁,它要叫彻人间,直接诉诸人类底心灵。这绝对不是“靡靡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