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vs行超:他们的受难就是我的受难 ——关于《云中记》的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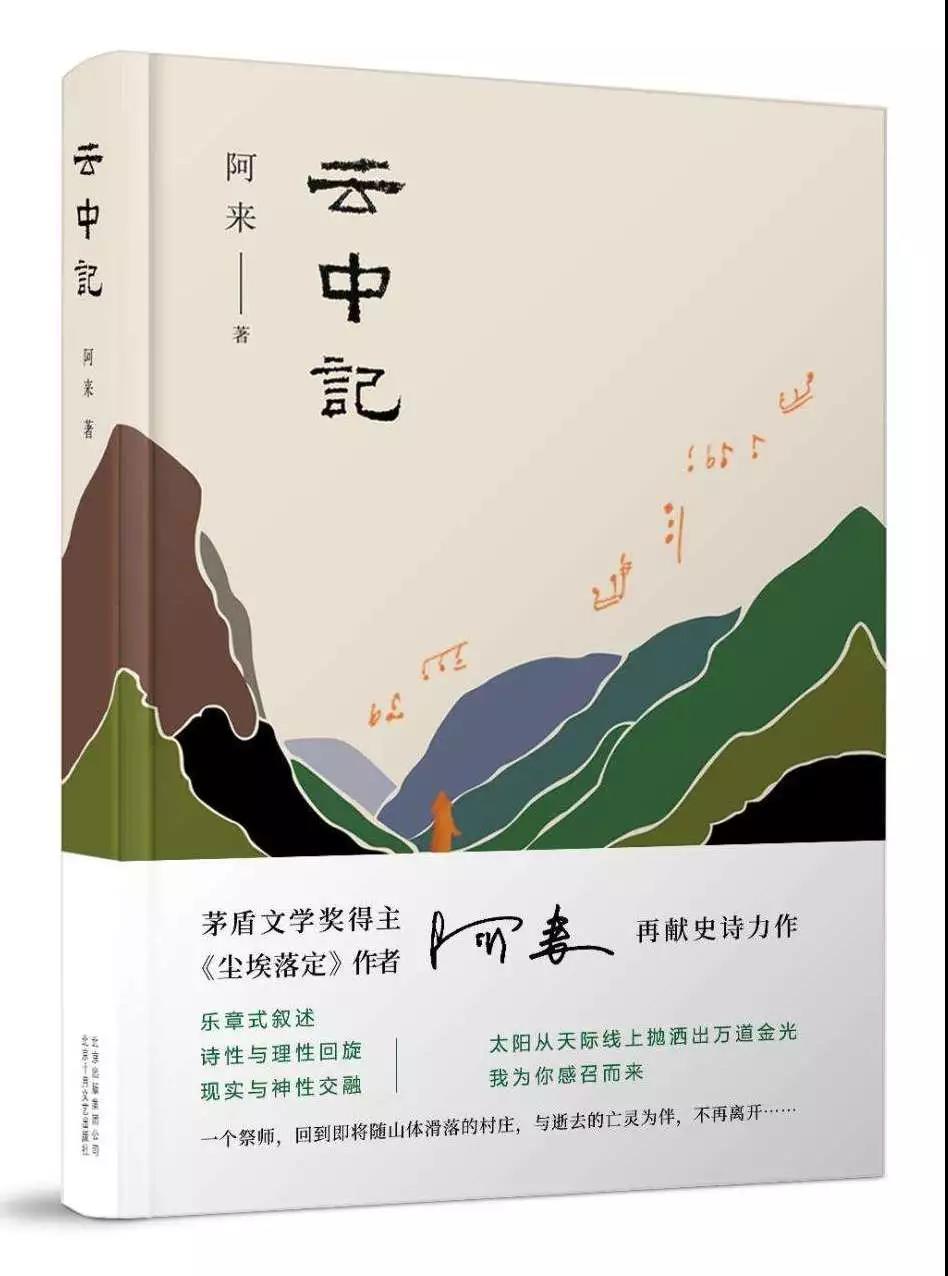
阿来新作《云中记》
2017年10月,著名作家阿来与十月文学院签约,成为“十月签约作家”
2019年1月,阿来长篇新作《云中记》由《十月》杂志首发
2019年4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云中记》单行本
2019年8月,《云中记》荣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访谈精编
“他们的受难就是我的受难”——关于《云中记》的访谈
◉ 十月签约作家 阿来◉ 十月特约评论家 行超

作家阿来
《云中记》的扉页上有这样几行字:“向莫扎特致敬//写作这本书时/我的心中总回想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某种意义上,《云中记》正是阿来写给512汶川地震中逝者们的一首安魂曲。十年之后再次回望,在曾经的巨痛即将被大众遗忘的时刻,阿来用自己极度克制的笔触、平静的讲述和深刻冷静的思考,写出了拥有《安魂曲》般力量和美感的《云中记》。
行超:《云中记》的写作开始于512大地震发生十年之后,这中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沉淀。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是您有意克制、不想被一时浓烈的情绪所裹挟?还是一种自然的失语状态,就像我们面对至亲的突然离开时仿佛丧失表达能力一样?
阿来:其实这两种原因都有。灾难发生的当时,我也觉得有很多话可以说,那种情境下,很多作家都提起笔来书写,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所观察到的现实。但是面对这样的写作,我马上产生一种警惕,难道文学就是简单地说出事实吗?难道现实主义就是简单地描绘自己所看到的吗?我觉得在这样重大的现实面前,文学应该写出更有价值的、更值得探索和挖掘的东西。但是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当时我没有想得很清楚。而且的确,如果选择当时立刻去写,我也很容易情绪失控,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当时出现的作品,其实都是失控的、没有节制的表达,你以为自己是在第一时间,在一个最好的状态中去书写的,但是最后发现所达到的不是你想要的效果。
行超:那么,是什么具体的契机让您最终提笔的?
阿来:我其实没有想过需要什么具体的契机。我知道这个题材、这个内容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也相信自己有一天肯定会去书写它。但是我的写作一向不会做什么具体的规划、准备,也从来不给自己规定什么时候要写什么。当时我正在写另一个长篇小说,突然有一天,我的脑海中一下涌现出一种情绪,出现了一个具体的形象,这些都与我当时正在写的长篇完全没有关系。但那个形象又是那么鲜明,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就是后来出现在小说中的祭师。于是,我停下自己手中正在写的另一个长篇,开始了《云中记》的写作。
对我来说,写作常常就是这样的情形。一件事情,如果我对它有兴趣,那么它就一定会存在在我心里,我不会着急去表达,而是先克制住表达和书写的冲动,因为我知道这种冲动有时候是虚假的,或者是短暂的。长篇小说的写作需要有漫长的时间、大量的经历投入,一时的感觉是不够的,你必须有充分的内心准备,不然一口气是没办法支撑自己写到底的。
行超:您的作品一直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前两年的“山珍三部曲”《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通过珍稀物种的现状反思了当代社会的商业逻辑。在生活中,您也是个非常热爱自然与生灵的“博物学家”。《云中记》写的是自然灾难,或者说自然对人的惩罚。通过这部作品,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什么新的理解?
阿来:刚才提到我刚开始没办法马上动手的原因,也是我当时没有想明白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死亡,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过去我们所看到的中外文学中的灾难书写,不管是战争灾难还是政治迫害,这些灾难的发生都有具体的原因和对象,我们习惯了对面有个敌人,有一种敌对的力量,这样我们才可以表达情绪,可以施以仇恨、批判。但自然灾难完全不同,台风、地震、火灾、水灾,这些都是大自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行,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要生活在大地上,并不是大地发出的邀请,而是人类自己的选择。我们总说“大地母亲”,大自然是我们永远没办法去仇恨的。我们的文学习惯了把所有问题设置出冲突双方,但在自然灾害这里,冲突的另一方是不存在的,你对面的大自然是没有情感的,它并不是施暴者,因此你也不能把它当作敌人,这个问题是我们此前的灾难文学所不曾面对的,也是写作时首先必须想清楚的。
比起“山珍三部曲”,《云中记》对自然与人的关系思考,其实触及的是更加本质性的关系。大自然为人的生存提供了庇护,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资源,但它也有情绪发作的时候,它一旦发作,人类就将面临灾难,而这时,人的宿命性就出现了。人必须在这个充满灾难的大地上生存,你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就必须承受可能发生的灾难,我们都别无选择。这是人类的宿命,也是悲剧性所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深刻意识到人类的无力、渺小,因此,爱护自然绝不是基于狭隘的环保主义,而是一种更根本的宿命论的认识。如果说《云中记》有一点贡献的话,我想就是处理和提供了对死亡、对自然这两个方面的新的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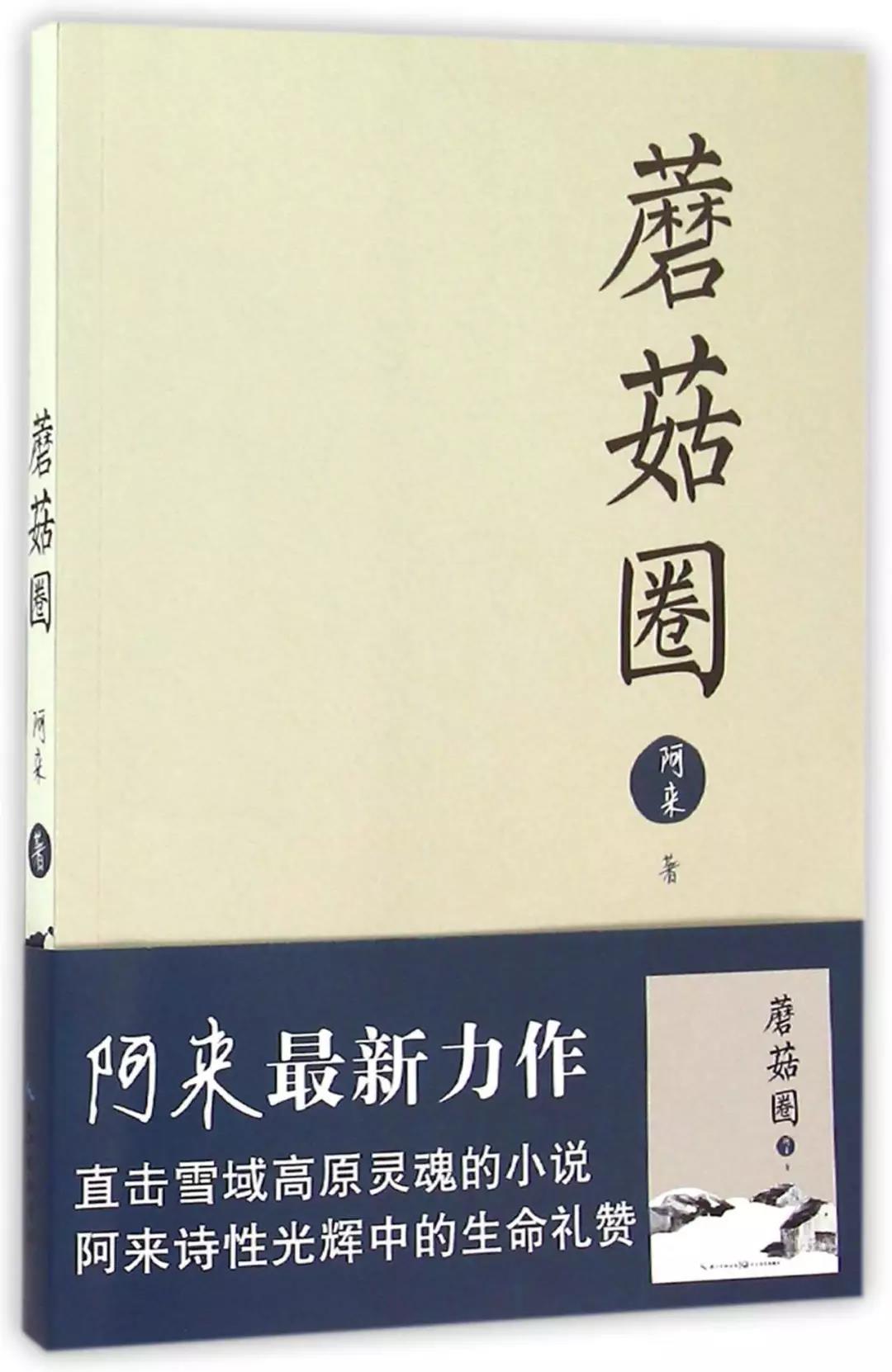
阿来作品《蘑菇圈》
行超:从《尘埃落定》到《机村史诗》,再到今天的《云中记》,可以看出,您对现代文明始终持有一种复杂的思考与审视。小说《云中记》写到灾后重建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尤其是后面几章,央金、祥巴等人本来是灾难的受害者,但他们后来的做法、行为更让人觉得痛心。您是怎么构思这部分内容的?
阿来:大地震发生后的这么多年里,我一直都关注着灾区的情况。小说中所写到的这些现象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都能找到影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我用文学的手法进行了改头换面而已。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这些现象,我还是基本秉持着“温柔敦厚”的态度,提出问题的同时也尽量理解他们吧。
对于这场大灾,我关心的不只是当时的灾区和灾民的情况,我更关心的是之后重建中的灾区。一场灾难带来了很多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这些伤亡和损失是无法逆转的,发生了就发生了,触景伤情很正常,但是悲天呼号本身并没有价值。更重要的是,在灾难发生之后,我们人的意志体现在哪里,发生了什么变化,之后我们是怎样对生活、对社会进行重建的,在我看来这比一时受灾的情况更重要。所以在《云中记》中,我想写这部分内容。
行超:就像云中村人所面临的现实一样,在现代化不可抗拒的大趋势面前,云中村这样的古老文明,或者说云中村人所信仰的精神和传统,在今天处于怎样的地位,该如何自处?
阿来:我并不认为所有旧的东西都应该保存下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轨迹,与时代脱节之后,消失就是必然的命运。人类文明几千年,这当中不断的进步,其实就是不断发现新的事物,同时不断与旧的事物告别。
我们现在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结,这里面其实有两个心理基础。一是我们提倡尊重传统、保护传统的大环境。这个环境是好的,但其中有问题需要辨析。在我看来,我们对传统的理解和保护,更重要的是领会其中的精神,地球空间有限,要不要保存那么多物质的东西,这个问题我还是存疑的。与其去保存那么多具体的物质,不如多读一点我们古代的经典著作,我们民族传统真正精神性的东西其实是记载在文字中的,而不仅是留存在某个老物件上。现代社会出现了拜物主义,很多“怀旧”行为,有时候其实只是对物质的迷恋,而不是对传统的尊重。现在很多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就是老物件、旧仪式,所谓“鉴宝”,最终关注的还是它的商品价值。事实上,我觉得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其中的精神,我们传承传统文化,并不是传承一件物品、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而应该是传承它真正的内在精神。
还有一个心理基础是,当代社会中的人们在面对新事物时内心有一种焦虑和不确定的、不安全的感觉。过去出现的新事物往往是可感可触的,火车、汽车,虽然是新的,但人们还可以把握。但是到现在,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很多新问题是大家完全无法把握的,比如我们热衷于讨论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等,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说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些新事物,人们一方面极度依赖,一方面又无法把握。在这种关系中,人类本身会产生焦虑,会时常有缺乏安全感的时刻,所以我们一边疾速发展,不停地出现新事物,另一方面又不停地“怀旧”“怀乡”,对旧事物总有一种迷恋。
行超:小说中阿巴对于传统的态度,其实也代表了您刚才所说的观点。这个人物身上有某种矛盾性,他开始以祭师的身份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训班时,好多东西都记不住,被大家嘲笑为“冒牌的半吊子”,但另一方面,在大灾发生之后,他却成为了对故土和已故乡亲最坚定的守护者,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您是如何定位并把握阿巴这个人物的?
阿来:阿巴这个人物身上是有普遍性的,在现实生活中,我见到的很多所谓传承人都有点“半吊子”。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明传统并不是很顺利地传承下来的,“文革”对传统文化形成了强力的阻断,很多传统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中被切断了。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对传统文化在内心的理解和认可其实并不彻底,很多人都是似懂非懂的。《云中记》中的阿巴就是这样,一开始他对于传统文化是什么其实并不是很清楚,但是灾难的发生唤醒了他,唤醒了他对传统的记忆、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也唤醒了他作为“传承人”的责任感。

阿来在《云中记》新书发布会上为读者签名
行超:对作家来说,“穿梭生死”的写作是很不容易的。《云中记》通过阿巴实现了这一点。阿巴是云中村人们与亡人沟通、与彼岸世界沟通的一座桥梁。与西方人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中一直缺乏“死亡教育”,对于死亡,我们好像除了恐惧之外一无所知。《云中记》中,阿巴“向死而生”,某种程度上他也教给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死亡。您在这部小说中想传达怎样的面对生死的态度?
阿来:阿巴这个人物的命运一开始我并没有明确的定位。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跟他一起经历,一起成长,到最后,他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思考了悟了生死,参透了其中的关系和秘密。所以面对自己最后的结局,阿巴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甚至进入了一种伟大的境界。
中国人对待灾难和对待死亡大多有三个阶段的感觉,首先是你说的恐惧,接着是受震动,然后就是遗忘。我觉得“死亡教育”应该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于正在面对死亡的人,如何能够平静坦然地接受死亡,接受这是人的必然命运;还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当你面对他人的死亡时应该思考什么,如何从别人的经历投射到自己,思考自己的生存和生命价值以及死对生的意义,这是对每一个个体的生者,对整个社会和国家而言都很重要的深层问题。
行超:十余年过去了,彼时语境中的很多喧嚣如今已经趋于宁静。就像您说的,我们好像已经进入了“遗忘”的阶段。小说《云中记》就像是一场对亡灵的告慰,告慰小说中的阿巴,更是告慰在那场灾难中受灾的灵魂。这次写作,对您个人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阿来:这样的遗忘我真的看过太多太多了。地震发生之后,我第一时间赶到汶川,此后又去过北川、映秀等地。在现场,我眼见着救灾人员、志愿者的热情一天天退却,遗忘开始发生。最开始的半个月时间内,大家都沉浸在那种巨大的悲痛中,救灾的热情也都很高涨。半个月过去之后,这种热情一天天地退却、递减,救灾的人们每一天都呈现完全不同的状态。不用说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余年,我亲身经历的遗忘的速度,是以天为单位计算的。
写作《云中记》,其实我并没有想去告慰什么人。在那场大地震中,受灾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是我自己熟悉的、身边的人,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人类都处于“生命共同体”之中,所以,他们的受难也是我的受难,他们的经历也是我的经历。因此,这次写作其实就是记录一段我与那些受难的人们、小说中的人们共同的经历,记录我们共同的沉痛的记忆。完成《云中记》的写作对我而言,首先是让自己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是我对自己那段经历、那种感受的一个交代,那段记忆我永远不会忘,但是写完之后我心里释然了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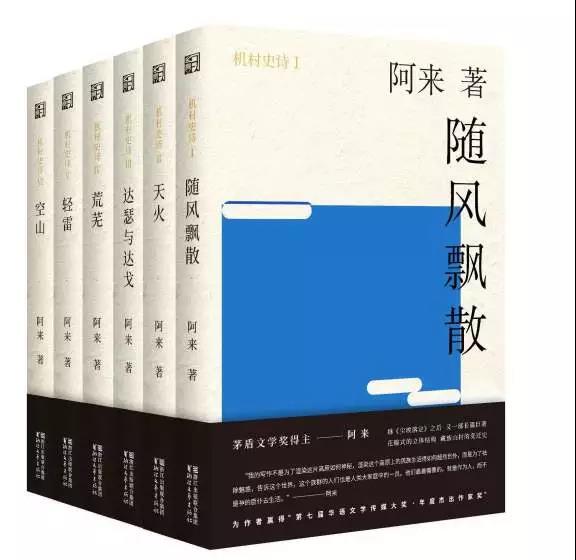
阿来作品《机村史诗》
《云中记》选读
第二章
第二天和第三天
阿巴进村去。
时间是盘算过的。2013年的5月9日。地震前三天。
他把自己打扮停当。翘鼻子的软皮靴,白氆氇长袍,山羊皮坎肩,熟牛皮的盔形帽子,上面插着血雉的彩羽。法鼓,法铃。铃还带着马身上的气息。当年把鼓从废墟下挖出来时,羊皮鼓面已经破了,他在移民村修复了它。当年把铃从废墟下挖出来时,铃也坏了。阿巴也在移民村修复了它。
阿巴吃了一张有些发酸的饼。他慢慢咀嚼,等着正在上升的太阳把村子照亮。
没有水,他从石缝中揪下来一些酸模草的茎,咀嚼,吮吸。酸酸的汁液充满了他的口腔。
太阳升起,把云中村照亮。
他对着村子,对着石碉,对着死去的老柏树,同时也是对着神山,磕了三个头,又磕了三个头。他听到自己身体里的关节嘎巴作响。
阿巴起身,穿过荒芜了的田野向着云中村走去。
以前,乡亲们珍惜这片肥沃平整的土地,路从平地边缘绕了好大一圈。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阿巴从荒芜了的田地中间直接穿过。
他摇铃击鼓穿过田野。
两匹马从远处望着他。
田野里的鸟惊飞起来。
石碉上的红嘴鸦惊飞起来,斜着身子盘旋,在风中振动着翅膀嘎嘎啼叫。
田野里还有自生自灭的稀疏的油菜、麦子和玉米。更多的是野草。甚至有柳树和村里人叫作筷子树的绣线菊在以前的麦地里生长起来。这些树很蠢,它们不该长到这块最终会消失的地方来。树应该站在山上,不应该跑到田地里来。他往前走,摇铃击鼓。他听到自己用祭师的声音和腔调在喊:回了!回来了!回来!
村子安安静静,残墙站在那里,柴垛子蹲在那里,不发出一点声响。
阿巴顺着废弃的水渠走向枯死的老柏树。他绕着树转着圈,他喊:回来了!回来。
……
来到了妹妹家。妹妹没有死在家里。妹妹在磨坊里被巨石砸在了地下。村里通电后,人们已经很少使用隔村三里地的水磨坊了。那天妹妹说,她要去把磨坊打扫干净,再过一个月,新麦子下来,她要让儿子吃到水磨坊磨出来的新麦面。妹妹喜欢说,可怜见的。她说,可怜见的,仁钦肯定想吃家里的新麦面了。可怜见的,新麦子的香气都被电磨盘吃光了。她去打扫磨坊就再没有回来,可怜见的。阿巴在妹妹房门前的石头台阶上坐了很久。石头被妹妹进进出出的脚磨得那么光滑。加上这些年的风雨,更使得它一尘不染。
阿巴说:好妹妹,我回来了呀!
门框上的残墙上有一个四方的洞。院门关着。妹妹煮了好吃的,在外上学的儿子来了信,妹妹就站在楼顶上向阿巴房子的方向喊:哥哥!阿巴!
阿巴就过来。院门关着。阿巴把手伸进这个洞,反手拨拉门闩,门就开了。
仁钦问过一个问题:门既然可以从外面打开,为什么还要从里面闩着?
妹妹用近乎崇拜的眼神看着儿子,转而又用近乎崇拜的眼神看着阿巴,对孩子说:你妈妈什么都不懂得,问你舅舅吧。
舅舅也不懂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说:老祖宗阿吾塔毗他们建村子时,就这样了。
阿巴把手伸进门洞,里面已经没有那根栎木做成的光滑门闩,也没有了那扇门。地震时,那门倒在了地上。仁钦带领大家抗震救灾的时候,把它刷黑,给开办了帐篷学校的志愿者做了黑板。
阿巴用一天时间拖着越来越没有力气的身子走遍了全村。
他把从移民村带回来表示念想的物件一样样放在一户户人家的废墟上。新家的照片。新朋友的照片。新生孩子的照片。其中两个孩子的照片,要放在四家人的废墟上。那是两个新组合的家庭。两个新生的孩子是四个人家的后人。
除了照片,还有一些旧东西。属于死人的东西。拿走时是要个念想。又担心死人用的时候,这些东西不在手边。一把牛角梳子。一个麂皮针线包,里面是锥子、顶针、大小不一的针、麻线、丝线、牛筋线。一件旧衣裳。一枚边缘泛紫的旧铜钱。一把钥匙。一朵褪色的红丝绒簪花。一盒头痛粉。一把小刀。半盒火柴……
……
他走到磨坊的引水口。湍急的溪水冲激出一个深潭。引水口就在潭边。两根粗大的杉木柱子中间,是可以升降的闸门。厚厚的闸门关着。因为泡在水中,闸门才没有腐烂。阿巴想提起闸门,但淤积的沙石把闸门下半部埋住了。
阿巴终于走到了巨石跟前。
他围着巨石转了一圈。除了引水到磨坊的木头水槽,磨坊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阿巴还记得,和云中村所有建筑一样,磨坊的矮墙是石头砌成的。门朝东开,北面一个窗户,南面一个窗户。顶子的几道横梁上,铺一层树枝,铺一层苔藓,再盖一层泥土。层顶上长满了瓦松和茅草。阿巴扶着巨石,走到磨坊门口的方向。岩石已经被太阳晒热了,有些烫手。他心头一热,轻轻地叫了一声:妹妹,我看你来了。
没有声音。只有溪水在几十米外飞珠溅玉,奔腾喧哗。
他把额头抵在岩石上,泪水流出眼眶,滑下脸腮。手摸着的岩石热乎乎的,额头抵着的岩石也热乎乎的。阿巴说:妹妹,这是你吗?这是你吗?
其实他知道,这只是太阳把岩石晒热了。
妹妹在世的时候,妹妹悲伤难受的时候,就会把手放在阿巴手里,让他握着。妹妹的手总是凉的。那冰凉本身就叫哥哥心伤。哥哥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哥哥自己就对生活中的不如意无可奈何。要是心肠不好的人伤了妹妹的心,哥哥对别人的坏心肠也无可奈何。要是妹妹使自己心伤,他也对妹妹的心无可奈何。他不说话,他就用自己手上的热气把妹妹的手暖和过来。仁钦在县城上中学那几年,他会对妹妹说:要不,我替你去看看仁钦吧。
妹妹就会落泪,说:仁钦听话,仁钦上进,就让他好好念书吧。
后来,仁钦去念大学了。
阿巴就不再说这样的话了。仁钦上学的地方太远。坐一天汽车去省城,再坐火车去外省的省城。阿巴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
阿巴平静一下自己。
草地有些潮湿。他铺一块毡垫,坐下。然后把褡裢打开。他在原来磨坊开门的方向,摆上了苹果和罐头。他说:这是仁钦给妈妈的。
他又摆上茶叶、盐和糌粑。他说:这是我带给你的。
他说:我想喝一口酒,你也用一点吧。他把碗里的酒浇在石头上,把剩下的留给自己。
……
阿巴注意到面前有一丛鸢尾。飘带一样的叶片,停在花萼上小鸟一样的花朵。开了几朵,没开的,也有几朵。年轻时的妹妹,喜欢簪鸢尾花在头上。但照片里的她头上没有簪着这样的蓝色花,花瓣上带着金色纹路的蓝色的鸢尾花。
阿巴喝了一口酒,继续说话:我来告诉你仁钦的事情吧。
这时,他听到了一点声音。像是蝴蝶起飞时扇了一下翅膀,像是一只小鸟从里向外啄破了蛋壳。一朵鸢尾突然绽放。
阿巴的热泪一下盈满了眼眶:是不是你听见了?你真的听见了吗?
花瓣还在继续舒展,包裹花朵的苞片落在了地上。
阿巴说:仁钦出息了,是瓦约乡的乡长了。我碰到云丹了,江边村的云丹,他说咱们家的仁钦是个好乡长。
又一朵鸢尾倏忽有声,开了。
阿巴哭了:我知道你听得见,我知道你听见了!妹妹你放心,我回来了,我回来陪你们了!我在这里陪着你们,你们这些先走的人。我把你的照片从仁钦那里带回来。我让他忘记你。我不要让他天天看见你。你也让他忘记你吧。
阿巴高兴起来。他想那两朵花应声而开不是偶然的。世界上有哪个人在说话时见过两朵花应声而开?他相信谁都没有过。也许云中村以前的某一任祭师见过。但现在的人没有谁见过。他觉得这就是鬼魂存在的证明。
如此看来,这个世界大概是有鬼魂的,他因此高兴起来。要真是这样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半吊子的阿巴了。
阿巴相信这是妹妹的鬼魂通过花和他说话。告诉哥哥,他的话她都听见了。
作家简介
阿来,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四川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机村史诗》(六部曲)《格萨尔王》《云中记》,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集《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以及中篇小说多部。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凭《机村史诗》(六部曲)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2018年,作品《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9年8月,长篇小说《云中记》荣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