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迪·史密斯,《白牙》和“多动症现实主义”

史密斯的母亲1969年从牙买加移民到英国,父亲是英国人。史密斯家几个孩子都有文艺才华,兄弟是饶舌歌手,她能歌善舞,大学时曾以演唱爵士为业,甚至一度想做专业爵士歌手。朱诺·迪亚斯是苦孩子,两个兄弟都坐牢;扎迪·史密斯却顺风顺水,在剑桥大学开始写作不久就找到文学经纪,《白牙》写成后轰动英国文坛,她立刻成为最受瞩目的新一代移民作家。
从奈保尔开始,英国文坛迎来拉什迪的《午夜之门》这样的巨著,进入2000年后扎迪·史密斯以处女作《白牙》接过“移民文学”这支火炬。奈保尔出生于1932年,与他相比,1975年出生的史密斯可以说是移民文学的第四代了。《白牙》杀青后获得该年度的Whitebread文学首发奖和《卫报》处女作奖等多项重要文学奖项。2002年她的第二部小说《签名商人》出版,写的是有中国血统的犹太商人,贩卖名人签名为生。2005年第三部小说《美》出版,故事设置在波士顿,某藤校艺术史系的两位非裔和拉丁裔教授的家庭冲突故事。这三部小说都是以多种族、多元文化的英美社会为背景的故事。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作品里的各种人物,英文经典小说里“男的,老的,白的,死的”传统已经被一个个双语的,饶舌的,听嘻哈音乐的非白种人取代。奈保尔靠奖学金在牛津大学留学时惨淡经营,对家乡贫困充满羞耻感,扎迪·史密斯生长于伦敦的中产家庭。时移事转,可见到90年代加勒比海地区的前殖民地移民已经是英国社会当仁不让的主流中产。两个作者人生对比,也是《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到《白牙》背后真实的英国社会财富和阶级的变迁。
扎迪·史密斯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五本小说,同时也写随笔专栏,随笔多次入选年度最佳选集,也是我的最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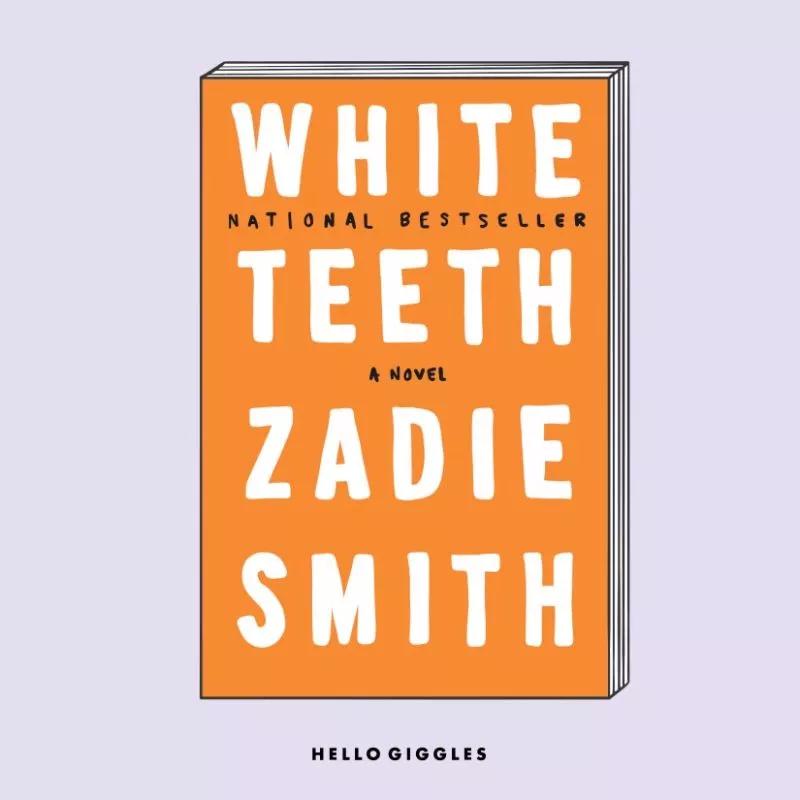
《白牙》写了两代伦敦居民,三家人。故事发生的地点从孟加拉国到伦敦又折返;小说时间跨度从二战开始,发展到基因工程流行的1992年——这是一部详尽的移民生活百科全书,令读者眼花缭乱:二战时的坦克兵阿奇·琼斯和孟加拉尔穆斯林移民伊克巴尔是一对好朋友。战后各自谋生转眼就到了中年,阿奇·琼斯不堪河东狮原配老婆的折磨,离婚后想自杀,被救下后在新年派对上偶遇牙买加美女,再结良缘。伊克巴尔战后在家乡结婚,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不久全家移民伦敦,在一家咖喱菜馆里打工当服务员。日子过得很闷,伊克巴尔把所有的错都怪到大英帝国头上,他酗酒,偷情,跟儿子的音乐老师约会被抓出丑都是英国社会的错。为了挽救下一代,保证他的宝贝儿子成长在道德风气良好的环境里,他决定把双胞胎送回孟加拉国抚养。哥哥听话孝顺,是标准的亚洲理科男,弟弟在街上混社会,小小年纪已经是个浑不吝,绝对不听老子的话。所以伊克巴尔只能把哥哥送回纯真道德的母国去。没想到待这两个男孩子长大成人,哥哥在孟加拉国“纯真环境”抚养下长成一个无神论科学家,弟弟长成一个热爱黑帮电影的正义青年。有感于像他这样的前殖民地移民在英国的二等公民的境遇,弟弟参加抗议拉什迪《撒旦的诗篇》示威游行,最后发展到加入原教旨主义右派兄弟会。这两家三个孩子,最后在伦敦北区的大学教授家里找到心灵的港湾。故事结尾,两代三家人的交锋,在1992年的除夕夜到达高潮……《白牙》的画风基本如此。
《白牙》在英国叫好又叫座,唯一的例外是评论家詹姆斯·伍德。2001年伍德在《新共和》杂志上撰文,把这种多民族多宗教,跨社会阶层,情节密集得处处开花,百科全书式的超级长篇小说比作“多动症患者跑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没有一分钟的静止,没有一分钟沉思默想,“不是魔幻现实主义,是歇斯底里现实主义”。詹姆斯·伍德是英国评论家中的重量级选手,即使不是文学“教父”,也是英国文学界敢说重话,说了重话让作家认真听的一个评论家。比如他公开评论奈保尔是人品极差趋迎富贵的渣男,是施害者和受伤者兼之。他评论保罗·奥斯特,直接用《保罗·奥斯特的浅薄》这样的题目。伍德不是简单尖刻的网红毒舌,每评论一部当代文学作品,他都在文学史上旁征博引,力求把作品放进文学史中去而不是简单地谈流行的文学套路。真话是文学批评的含金量。
批评移民文学中的歇斯底里叙述,伍德从英国社会小说中的狄更斯传统说起,把原罪归到唐·德里罗(Don Dellio)的长篇小说《地下世界》头上。拉什迪的《午夜之门》、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无尽的玩笑》、唐·德里罗的《白噪音》、罗伯托·波兰诺的《2666》、强讷森·弗兰岑的《纠正》都上了黑名单,连2007年出版的《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出版后都被追补一刀。
移民题材鸿篇巨制的小说,大量地没有节制地铺陈外部环境和人物关系,疏于探索人物性格的发展,人物内心状况基本没有。事无巨细,包罗万象的描写,已经到了令读者头晕的地步了,比如《白牙》中每一个人物都信了一门邪教,或者不是地震(比如《午夜之门》),就是核弹爆炸(《地下世界》),“人物一生孩子就生一对双胞胎,连狗都会说话”,“主人公还没有往前走一步,迷宫一样的环境,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描写已经占了四十多页”……可见真的把伍德搞烦了。用国内编辑的话,就是这些小说“编得太厉害了”。伍德的理想小说是契诃夫的短篇经典——留白,安静,连头带尾最多十页纸。小说,终极目标不是写得复杂,把读者侃晕,而是写得动人、好看这个简单的标准。
这篇评论发表以后,不久扎迪·史密斯写文回复。她基本接受评论家的观点,“歇斯底里现实主义”这个词话糙理不糙,下一本小说她一定关注人物内心。她唯一觉得不公正的是,《白牙》作为年轻作者的第一本小说,跟拉什迪和唐·德里罗这样文坛巨擘被一起痛殴,有以大欺小的嫌疑:“试想若没有《午夜之门》那还是当代英国文学吗?”——言下之意《午夜之门》出版的时候,评论家中没有一个人出来指责拉什迪歇斯底里。而我这个年轻作者出版第一本书,你就敢骂了?“作家只能写她能写的,而不是写她想写的”,留白,安静,好看,写得像契诃夫,这些对小说的高要求,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对于这种批评,同辈评论家的反应是,既然写作反映世界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中心理想,面对如今这样一个世界,多少小说能避开混乱、焦虑、多地点多宗教多民族的故事构架呢?而这样错综繁复的故事怎么都是有点歇斯底里的啊!
这段公案基本就到此为止。值得注意的是,《歇斯底里现实主义》这篇伍德没有把它收入评论集,没有让这句毁灭性的标签继续流传下去,随着时间流逝若不是专业研究者深挖的话,读书界不会记得那么清楚,可见伍德对年轻作家还是心慈手软。要知道,伍德每隔几年就汇集他在报纸杂志上的长篇评论,结集出版,他的书在市场上卖得非常好。(伍德的书在国内基本都有中译本。)
伍德和扎迪·史密斯对后殖民时代移民小说再次交锋,要等到2008年另外一部移民小说——约瑟夫·奥尼尔的《荷兰》横空出世并获得那年度的普利策奖。2001年纽约双子楼的恐怖袭击,改变了全球政治的图景,十年后世界开始新一轮难民迁徙的潮流。难民问题让移民文学和移民世界的争论再添热度,难民是暴力和恐怖下极端形式的移民。难民问题加上全球恐怖主义,以及与之对应的反移民的民粹保守思潮汹涌,这些进入21世纪后遍布全球的激烈的新现象,仿佛末日洪水!相比20世纪90年代伦敦东区移民社区的混乱,简直是小打小闹。
詹姆斯·伍德任《纽约客》杂志文学评论版的专业评论家已经超过十年。可以说当代英美出版的重要小说,都经历他的刀笔。他选择作品的标准在英美的评论家中可以说具有代表性——出版作品引起关注,评论家对作品评论。评论家若对一部小说保持沉默不置一评,说明小说不够出色,不值得评论家花时间和版面。至于小说家的年龄、性别、种族这些非文学以外的因素很难成为作品的加分项。这一点跟中国文坛的评论路径相去甚远。

詹姆斯·伍德
说了这么多,还是要回到本文的开头。本文写了英美的移民文学中风头最劲的两个年轻作家,他们被英美当代文学接受并肯定,并不因为他们的族裔和移民身份被排斥在外,这是毫无悬念的。同样,用“新海外华语作者”何袜皮的话:“虽然我人在美国,但我还是汉语写作,写的还是‘中国小说’。”
跟严峻的冷战时期比,海外华语文学以及其他的边缘/另类作品比如网络文学是不是能拿文学史家的通行证,实在不算太大的磨难。感谢我们生于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够水准的作品在市面上都可以与读者见面。这是我这个写小说的人也稍稍可以自我安慰的地方。按照新华语文学的标准——“这个专题的作家都是新世纪后抵达世界各地的,他们是全球化时代的新人,新青年。他们的写作也是真正的‘新’”。我这个年近五十,20世纪90年代初到达美国,近三四年来才开始写作的作者真不算是什么新人。年龄超标,除了投稿,我基本上沾不上任何文学人群的光,“80后”“90后”“新华语”都与我无关。但没有名目,也一样要写作。海外像我这样无法归类的作者,其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我们这群人,真正是何平老师归纳的“没有名目,一样写作;甚至没有写作,他们一样有其他的生活”。我们这群人人数不少,两袖清风,靠自己的另外职业谋生来养文学,凭着开店,做金融分析师,公司财务会计师,电脑系统程序员,房产中介,珠宝设计师等职业收入,在英语世界中坚持写了多年中文写作,若说以中国故事投市场所好,以这个理由拒绝其作品的价值,那么同样的理由可以刷掉国内的一大批作品,所有作品卖了IP改编成影视剧的都可以被质疑其文学价值。
海外华文孤岛式写作,不是没有问题。但不是何平老师说的“迎合市场讲中国故事”,也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语言孤岛对作家创造力的限制——文学语言和文学视野没有更新,停留在出国时期,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移民人群的“文化石化”,即奈保尔在《两个世界》里所概括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过着一种‘假装在印度’的生活,好像印度是一块随身携带的地毯,随时可以取下来铺到一块平地上……继续过一种渐渐褪色的印度生活。”把这段话中的“印度”换成“中国”完全成立。
“新海外华语文学”展览的作品可以看到写法上的尝试可能。但平心而论,并没有看到令人拍案叫绝的作品。就像伍德在同篇评论里说的:“自从现代主义出现后,优秀作者提供了对传统小说人物的戏仿写法和批评,但真正可以取而代之,行之有效的新写法并没有出现。”搅局是搅了,但搅局之后是空白。读者想读长篇巨制还只能是回到《劳燕》等,所见即所得,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have,读者没得选。这种存在即合理式的对“那几个海外作家”的作品集中关注,是一个自我生成的怪圈——你写出够出版水准的长篇作品,编辑喜欢,市场自然就关注。反之,没有作品,一切主义和理念都是空谈——这里说的作品是文学作品,不是理论构想,不是专栏文章,未完成作品也不是作品。没有作品,就怪不了读者不够关注甚至有意错过新华语作者。
文学评论家对作家作品的沉默,并不是容忍而是看不上,这一点中外皆然。所以,我期待何平老师对海外几大作家的当头棒喝,正面集中要害的文学批评,是海外作者真正被母国文学界接纳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