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恩先生》:波拉尼奥笔下那些被围困在时间中的漂泊者
来源:澎湃新闻 | Dzolan 2019年08月29日15:43
在短篇小说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波拉尼奥写了一个名为《圣西尼》的故事,关于漂泊在西班牙的“我”与作家圣西尼如何依靠参加小说比赛谋生计。熟悉波拉尼奥的读者会发现,这个故事其实来源于波拉尼奥本人的真实经历。

1977年,身怀革命与文学理想的波拉尼奥漂泊欧洲,游荡在巴塞罗那的海岸边,依靠打零工和写小说谋生。写于1981年或1982年的《佩恩先生》,就是这段骄傲又不幸的时期的产物之一(“我作为一个作家,从来也不像那时感到那么骄傲和不幸”),他将这部小说及其所获的奖项看作是:一头红皮毛水牛为生存而必须外出捕食而获的奖。

自然,这个说法中存在着自谦,以及为形势所困的意味,写小说首先是为了喂饱自己的肚子。到了90年代之后,这种对生存的需求开始扩大,为了养活家人,也为了能在死后给儿子留一笔遗产,波拉尼奥开始更勤奋地写小说,在生命的后十年,他留下了几百万字的小说。
如同对生存的需求成为波拉尼奥小说写作中与生俱来又难以摆脱的命数,在阅读《佩恩先生》后,你会发现他在后期小说里,那些侦探元素与迷宫般诡异的情节、历史与虚构的交织、在破碎的理想与现实中无法挣脱的主角,几乎以一种自发的方式出现在这部小说里。《佩恩先生》,它是波拉尼奥小说宇宙的开端,一个尚未完整但已经锋芒渐露的雏形。
小说的故事主线简单到几句话就能交代完。1938年的巴黎,名为皮埃尔·佩恩的“我”受雷诺夫人的委托去给一位名叫巴列霍的病人看病,途中“我”被两名西班牙人阻挠而放弃救助巴列霍,十多天后,我收到了巴列霍的死讯。
在小说中,当佩恩先生答应西班牙人放弃治疗巴列霍后,故事似乎变得与巴列霍无关了,波拉尼奥将重心放到了叙述者身上——“我”游走在空旷又多雨的巴黎,遭遇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人,制作鱼缸的双胞胎、夜总会守门人、曾共同学习催眠术的旧友;与此同时,“我”的精神世界也面临崩溃,幻觉和梦境来回纠缠着“我”。
“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些?巴列霍的死又意味着什么?当小说结尾时,这些谜题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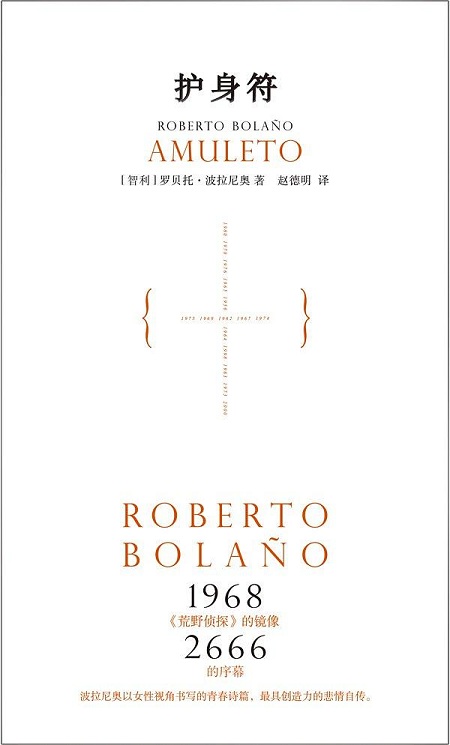
波拉尼奥从不忌惮用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为故事的原型。《护身符》中的墨西哥镇压事件,《2666》里的华雷斯谋杀案,包括以化名或真实姓名出现在小说中的拉美作家们。在《佩恩先生》的作者手记里,波拉尼奥就向我们表明:巴列霍的死以及佩恩先生本人是真实存在过的。言下之意也是,要想得知小说的真相,得从历史中寻找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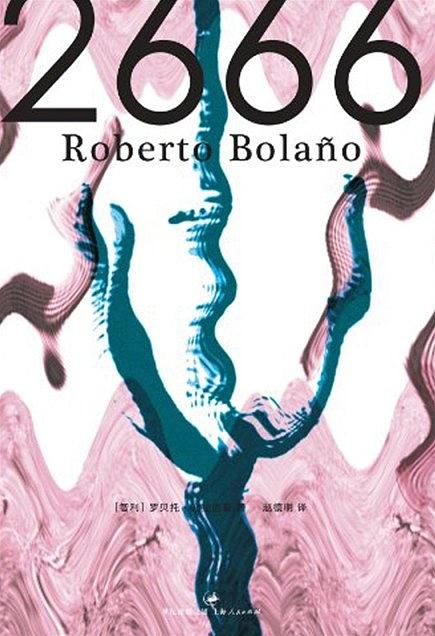
小说中的巴列霍先生原型来自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1892年出生,1920年因为思想激进被捕,1927年流亡欧洲,1930年在西班牙内战中投入反法西斯战争。1938年,巴列霍在巴黎的一个下雨天辞世,死后逐渐被看作是比聂鲁达更伟大的西班牙语诗人。
在时间上,小说对巴列霍之死的描述与历史吻合,区别在于,现实中大多数医生认为巴列霍是被饿死的,小说中的巴列霍则是患上了一种打嗝的怪病,被关在一家有着圆形楼梯、宛如迷宫的医院里。在佩恩先生跟随雷诺夫人探望巴列霍之后,两名西班牙人给了佩恩先生一笔钱,让他忘记、不要参与巴列霍的事情。

罗贝托·波拉尼奥
当历史部分与小说虚构的部分结合起来时,佩恩先生、巴列霍、西班牙人之间看似没有因果的关联有了答案:1938年,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参与内战并站在反法西斯阵营的巴列霍遭到迫害,佩恩先生在无意中参与其中,被身为法西斯者的西班牙人阻挠,巴列霍最终被迫害致死。
一个打嗝而死的人,一场无形的政治阴谋,被莫名卷入的参与者,波拉尼奥对巴列霍之死的再现正是他小说中常见的叙事谜团,因果关系被抹去,混乱又破碎,连接荒诞情节的是不可名状的恐惧。在波拉尼奥的另一部小说《智利之夜》中,名为卡纳莱斯的女作家在自己家主办一个著名的文学派对,一方面帮助自己笼络资源,一方面又默许身为秘密警察的丈夫把来往作家关在隧道里审讯。当真相揭晓时,往往又呈现出超越表象的恐惧,也带有阴谋论的意味。
回到小说中的第二个问题,“我”——佩恩先生——为什么会在脱身巴列霍的事之后遭遇这些?在交代佩恩先生光怪陆离的遭遇同时,小说也由“我”逐渐说出了自己的过往经历。
皮埃尔·佩恩,二十一岁的时候参加过凡尔登战役(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耗时最长的战役),双肺被烧坏后奇迹般生存下来,靠着残疾人的微薄补助生活。小说中“我”有过这样一段自述:“也许为了向满不在乎地把我置于九死一生境地的社会表示拒绝,我放弃了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青年人的人生有用的一切,而致力于神秘学......”在研究神秘学期间,佩恩结识了名为特泽夫和普勒默尔—博杜的好友,三人时常待在比他们年长的里韦特先生家中。
眼下,1938年,佩恩与好友分散,独自一人依靠催眠为业,西班牙内战正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无论是佩恩背负旧的战争创伤,活在新的战争阴影下的状态,还是他的遭遇——其中有一段写佩恩跟随三个印刷工人在巴黎午夜游荡,穿梭于舞厅和酒吧,在一个半地下赌场遇见名为“皇后与屠夫”的色情表演,最后独自在无人的库房中醒来——人物的经历和情节安排都让人想起法国作家乔治·巴塔耶的《天空之蓝》,一部讲述西班牙内战期间,绝望的青年托普曼为了逃避战争带来的动荡,终日将自己沉浸在酒色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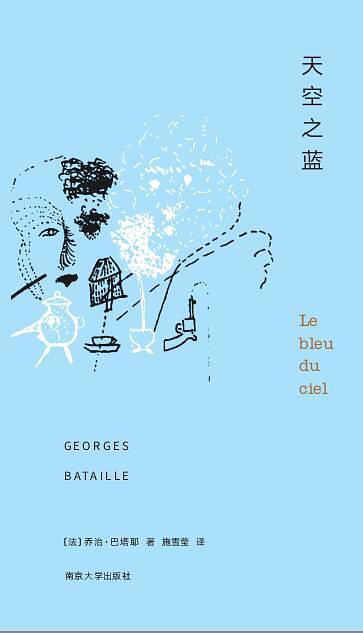
与托普曼类似,佩恩也面临着战争阴影下如何与现实相处的问题。一方面,他喜欢雷诺夫人,也渴望拯救巴列霍,即便是收了西班牙人的贿赂后,他也尝试着进入迷宫一般的医院寻找这位病人。在他那些古怪的梦境和遭遇中,巴列霍的幻象也时常纠缠着他:“那个人影又打嗝了.......那个人在那里假装巴列霍的打嗝声。”他的行为和潜意识都在努力和这个现实产生一些有益的连结,但这些尝试又总是变得徒劳,巴列霍未能存活,雷诺夫人消失之后带着新任丈夫回来。
与此同时,佩恩似乎意识到造成他与现实之间的隔阂是因为他的过去。作为一战的幸存者,他对这即将再次燃起战火的世界失去了原本应有的责任和价值,他断绝了和里韦特先生的关系,因为他意识到他们都是眼前这个“地狱”的旁观者,远离里韦特就是在与过去的自己划清界限;当他遇到曾经的好友、现在的法西斯主义者普勒默尔—博杜时,他愤怒地将酒泼在对方脸上,也可以看作是他试图挽回自己的价值——还能在战争中找到自己的立场,即便这个举动显得无助和幼稚。
摆脱过去,在现实中找到新的自我,佩恩失败了,他重新回到了自己眼中的正轨:纯粹而简单的绝望与情绪低落期交替出现。“困在时间中。”他没有了过去,也失去了现实,成为当下的漂泊者。而如同历史中的巴列霍之死无法被改写,佩恩的失败几乎是小说必然的结果,并持续牵引出波拉尼奥小说里最常见也最重要的母题之一——被践踏和埋没的理想混杂着对现实的不安,将主人公永远地围困在其中,直至死亡。
在小说的最后,波拉尼奥通过另一个叙述者的口吻,以人物小传的方式(后来波拉尼奥以这种方式创作了《美洲纳粹文学》)讲述了小说中人物们的经历,皮埃尔·佩恩在二战结束后的1949年,累死在工作中:“直到有一天他的肺脏受不了,累死了。他死在我的怀里,在多雷夫人夜总会的老板办公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