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的“此在”与……“站在人这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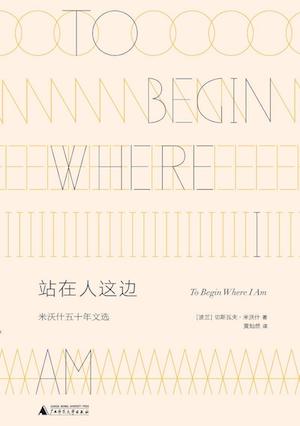
《站在人这边:米沃什五十年文选》,[波]切斯瓦夫·米沃什著,黄灿然译
国内许多读者对波兰著名诗人与散文家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1911—2004)的作品早已熟悉,我印象很深的则是十几年前读《米沃什词典》(西川、北塔译,三联书店,2004年)的体验——在这部个人回忆录中,几乎每一个条目都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历史的一条注释,关于那些人物、事件和著作,他的许多记忆、感受与思想在今天看来更有现实意义。例如对苏联地下历史学家安德列依·阿玛瑞克(AMLRIK)的介绍和论述,无论是他对权力真相的分析洞察还是对未来的预言,都很有思考的价值;更令人心悸的是,米沃什说阿玛瑞克有“一种对于如此悲惨、如此残酷的生活方式的恐惧转化为要求某种历史报复的呐喊”。(21页)米沃什在该书最后的“跋”中说,他的二十世纪是由一些他认识或听说过的面孔和声音所构成的,他们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必须让他们免于被遗忘,要让他们回到生者之中。(304页)同时,我们在这部《词典》中已经接触到一个问题:究竟如何看待米沃什的写作主题中的政治性与反抗性?在介绍《基谢尔日记,1968—1980》的时候,米沃什谈到他自己与他所敬佩的波兰知识分子基谢莱夫斯基(“基谢尔”是他的笔名)的区别:“我没有让自己政治化。置身于西方……我用几本书履行了我的义务,但随后我告诫自己:‘够了’,便再未继续往前走。……因为我意识到了另一重召唤。”(148页)西川在为这部书写的“译者导言”中说,米沃什的写作主题肯定少不了对专制制度的谴责,但如果我们仅是这样来看他就会“简化了一位复杂而深刻的诗人”。他认为米沃什深知自己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写作,在把一切噩梦化为写作资源的同时与噩梦本身保持距离,“米沃什的历史经验和他对神学、哲学的兴趣都要求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关照历史和人生”。(10页)从面对政治到超越政治,这是涉及关于二十世纪的历史记忆与人的状况的根本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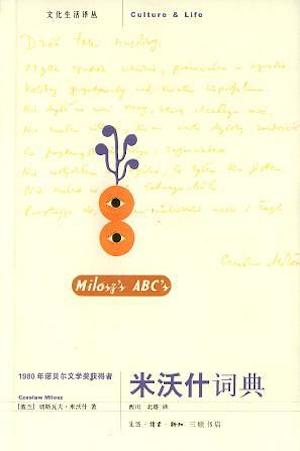
《米沃什词典》
十多年过去了,关于米沃什的阅读感受不仅没有淡忘,反而由于最近“文学纪念碑”推出米沃什的几本文集而更加强化,同时也深感当年读《词典》的时候产生的问题仍需继续深入思考。这部《站在人这边:米沃什五十年文选》(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辑录了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代表性随笔。它们横跨五十年,旨在体现米沃什非同寻常的主题广度以及他所掌握的体裁和风格的多样性”。第一部分“我这些客人”从“我是谁”开始,在回忆中记叙和评价了那些曾经对米沃什的人生与精神世界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第二部分“站在人这边”更多呈现的是在极具深度的宗教思考和哲学思考中的米沃什,是了解他所感受到的“另一重召唤”的重要文本;第三部分“反对不能理解的诗歌”,辑录米沃什关于诗歌的责任的重要文章;最后一部分“在不断的惊奇中”,可以看作是全书的结语,收入摘自他的《笔记本》的一些片断,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开放和自由的阅读角度,以重温一直以来支配米沃什写作的诸多主题。毫无疑问,这部“五十年文选”比以往米沃什的其他文集有更为宽阔的阅读视野,所涵括的人物素描、风景散记、哲学随笔、社会观察、政治评论、文学分析、辩论文章等多样体裁和风格更为全面地呈现出作者多样化的修辞策略和叙述技巧。
这部英文版选集的两位编者在“导言”中指出,米沃什的全部写作集中于少数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历史的意义;邪恶和受苦的存在;一切生命的短暂;科学世界观的崛起和宗教想象力的衰落。同时也为读者勾勒了米沃什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势:由某些特定经验触发的早期作品是个人的和充满激情的;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因双重流亡和重新定义自我的需要而保持距离感和客观性;在八九十年代则不再紧密地联系某个特定经验,而是更多的是对人、历史、文化和宗教的总体反思。米沃什的全部写作与他的生活经验和他面对现实的态度紧密相连,他经历了二战、纳粹、冷战、流亡等二十世纪的痛苦生活,这些经验使他对历史与现实极为敏感,使他始终保持参与现实中的精神斗争的激情。对于我们而言,从米沃什的写作中更能体会到的是,离开了我们的生活经验与我们无法脱离的现实,“我们”其实就并不存在。而所谓的“经验”与“现实”都是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在这里我想到的是这部书的原书名“To Begin Where I Am”,直译是“从我在的地方开始”。中译本舍弃了它,选择了第二部分的题目“站在人这边”(“On the Side of Man”)作为书名,有得也有失。依我们对米沃什的基本立场的认识,尤其是各种因素的积蓄,“站在人这边”是一种坚定的、最后的精神宣示,是一面无法再妥协的旗帜。但是,书中米沃什的正文第一篇“我的意图”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此。这三个字包含了可以说的一切——你以这三个字开始,又回到这三个字”。(1页)接下来说他的写作要传达的是对“在此”的无比惊奇,文章最后一句是“我在此——而每一个人也都在某个‘此’的位置上——我们唯一可做的事,是试图彼此沟通”。(3页)可以看出“我在此”在米沃什心目中的重要意义,原英文版编者以此作为书名当然是有所考虑的。说到底,米沃什的“此在”观念与“站在人这边”的立场当然没有矛盾,中译书名之得耶失耶,真是见仁见智。
与上面谈到的米沃什的政治性与反抗性问题紧密相关的是,两位编者在“导言”中指出:“米沃什的反抗不仅针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也针对西方自由主义,后者被证明在面对极权主义邪恶时是安于现状和在精神上空洞无物的。”这里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批判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那么尖锐和准确,这是由米沃什的“此在”所决定的写作针对性,他自己在文章中也多次谈到无论是苏联体制或美国体制都不喜欢。关于这两种体制,他突出的是“恐惧”这个特征:不是害怕政治警察,就是害怕贫穷,两者都是“基于恐惧的社会”。(《米沃什词典》,195页)但是,米沃什并没有停留在对邪恶的厌恶和拒绝的层面上,他“超越拒绝,并且不顾困难,把他的希望寄托在那一丁点儿人性尊严上,因为他相信这人性尊严存在于我们每人身上,并在不同时代被冠以不同名称:‘理性、神灵、常识、绝对律令、道德本能。’”(《站在人这边》“导言”)这是需要在这部文选中认真阅读和探讨的问题。
我认为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上,包括波兰在内的所谓“中欧经验”起码包含有三个方面的独特性与重要意义:一是所有的思想主要来自于承受历史上两种极权政治的暴力统治,是“在两者可怖的交替中存活着”(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语)的思想产物;二是思想与行为选择紧密相连,个人良知是在暴力专制下对责任与牺牲所作选择的内在驱动力,这些选择是对思想的最好检验;三是其价值与意义超出纯粹的政治性与反抗性的论域与局限,使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精神使命具有普遍性价值——这些价值的基本核心是“自由”与“尊严”,与之紧密相连的是受苦与牺牲。关于“良知”、“自由”、“尊严”,从正面来评价这些“中欧经验”的论述很多,但米沃什在《道德家阿尔法》中让我们看到一个反面的渐变过程,虽然带有某种“了解之同情”,恐怕比正面的自由主义“说教”更能触动人性中的幽暗。作家阿尔法拥有才华和野心,是米沃什的至友。在波兰人反抗纳粹的最后的悲剧性斗争结束之后,他很快找到并认同了可以实现他的才华与野心的“历史的必然性”及其力量,他及时创作出新的作品、自我检查、加入组织,该做的都做了。米沃什对这种过程的描述非常精准:“如今,波兰的作家们有点像处女——热切而胆怯。他们最初的公开声明都是谨慎而煞费苦心地掂量过的。不过,重要的仍然不是他们说什么。新政府需要他们的名字来证明它得到整个文化精英界的支持。……能够在弥合这鸿沟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是那些以自由派人士甚至保守派人士闻名的著名作家。阿尔法满足每一个要求。他的文章出现在一份政府文学周报的头版;那是一篇论人道主义的文章。我还记得,他在谈到一个道德准则,也即那场革命带来了对人的尊敬。”(143页)无论如何感到志得意满,阿尔法无法逃避个人的道德危机,但是他成功地使自身的人格发生相应的改变;“他渴望获得认可的过程中,他简化他的画像,……一个妥协导致另一个妥协和第三个妥协,直到最后,尽管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但它们已经与活生生的人的血肉没有任何关系了。”(151页)他只能以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光环陶醉自己,摒却内心的那个阻止自己下落的声音——米沃什怀疑地说:“很有可能,他并不知道那个声音。”(同上)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米沃什并不认为自己适合评判阿尔法,因为“我本人也走过同一条看似不可避免的道路”。他也承认自己带上了面具,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如果你在你心里保存对善的爱,你会被原谅。”(165页)米沃什回想起来,在同样的环境中,人与人的命运的区别往往是由于那些很微细然而很真实的差异:“也许我们命运的不同,在于我们参观华沙废墟或目光穿过窗口望向囚犯时,我们的反应的些许差别。”(150页)是的,我相信在人的天性中总有一些差异可以决定人的世俗命运和精神倾向。应该顺带指出的是,米沃什在这篇文章中对阿尔法在战后新作的评论相当深刻,那是对被规训的文学的变化过程的精彩的文本分析,虽然是很简短的。那么,在那种“历史的必然性”及其力量的碾压下,谁能幸免于道德危机?如何才能真真正正、毫无保留地说真话呢?米沃什以西蒙娜·薇依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世上,只有沦落至遭受最低贱的羞辱,远低于乞讨生活的羞辱的人,不仅没有社会地位而且被大家视为失去基本人性尊严、失去理性——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讲真话。所有其他人都撒谎。”(268页)话说得很残酷,但恐怕很真实——在这样的境况中,人还有什么因害怕而不敢说的真话呢?
最后,让我们还是回到作为诗人的米沃什吧。米沃什敏感于哪怕是最简单的事物、最单一的景色中所蕴藏的复杂性与预感,他甚至能够从别人诗歌里对最简单事物的吟唱中感受到同样的敏感与惊讶。比如,巴西诗人卡洛斯·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有一首短诗《在道路中间》:“在道路中间有一块石头 / 有一块石头在道路中间 / 有一块石头 / 在道路中间有一块石头。/ 在我这疲惫的视网膜的一生中 / 我将永不会忘记这次事件。/ 我将不会忘记在道路中间 / 有一块石头 / 有一块石头在道路中间 / 在道路中间有一块石头。”米沃什的评述是:“当一样事物被真正地看见,专心地看见,它便永远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惊异,尽管它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415页)他继而认为这个例子说明“被观察到的事物能被文字捕捉到的是多么少,因为很简单,语言是以观念来运作的。……德鲁蒙德·德·安德拉德这首诗很出色地描写与物体相遇的瞬间,但是它难以令人满意,说句实话,就如同任何旨在把感官知识转化成文字的企图那样,只能多多少少令人满意。”(416页)这是在人与事物之间最纯粹的相遇,语言文字只能描述在这种相遇的瞬间中产生的印象,但是出色的诗人能够感受并捕捉这种瞬间相遇中的现象学意义,能够在最为简单的物像、景色中看到存在的全部力量与复杂性。米沃什自己就是这样的诗人,因此他才能平静地说出“而在街上,一辆 / 坦克驶过,还有一辆有轨电车 / 在叮叮当当作响,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华沙,一九四一)这样的诗句,却让某些读者想到了曾经经历过的最沉重的时刻,这让我们相信米沃什不断强调的关于诗歌的存在意义——尽力捕捉可以感觉到的真相,使之成为见证历史、参与时代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