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与巴金的书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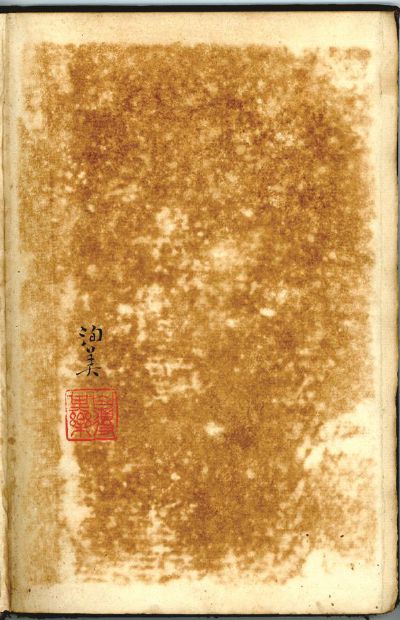
《死去的人》一九三一年版英文本扉页上的巴金签名和环衬上邵洵美的签名
1926年5月,诗人梁宗岱在巴黎送给邵洵美一本卢梭的《忏悔录》,书的环衬页上,有梁宗岱的题词:“洵美由英归国,道经巴黎,以此持赠,并藉以寄我火热的相思于祖国也。宗岱一九二六,五,二一法京。”抗战时期,这本书在重庆为巴金所得,并一直珍藏,晚年捐给上海图书馆。一本书,三位中国现代作家,这也算是一段饶有兴趣的佳话。
巴金与邵洵美的书缘并未尽于此,他还买过另外一本邵洵美的藏书。那是劳伦斯的中篇小说 《死去的人》(THE MAN WHO DIED),一本细条的十六开精装书,毛边本,伦敦MARTIN SECKER有限公司1931年出版。正文前有标注:此版本限印2000册,仅在英国和美国发行。另有说明:这个小说最初的标题是 《逃亡的公鸡》,现在的题目是作者死前不久决定的。八十八年过去了,这本书已经有些陈旧,墨绿色的布面已经失去它最初的颜色,但是封面正中烫金的一只展翅的水鸟的标志仍然金色饱满。书的前环衬靠近订口处有邵洵美以浓墨工整地签下的“洵美”二字,下面钤一方闲章,印文是“自得其乐”。这清楚地表明,此书原本为邵洵美藏书。书的扉页上有一个用钢笔书写的大大的“金”字,这是巴金藏书中的习见签名。它什么时候归巴金所有呢?在封三处,有一枚“外文旧书门市部”小条章,上面标着售价1元。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是旧书店、外文书店的常客,此书应当购于那时。
这不是邵洵美的普通藏书,他还为它写过书评。劳伦斯,是邵洵美颇为关注的一个作家,1934年,他撰文《读劳伦斯小说——复郁达夫先生》,文中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前后曾读过五次”,并藏有劳伦斯私印初版本和后来出版的廉价普及本。他还透露:“我在前年的秋天,曾译了他的一部中篇故事《逃走了的雄鸡》……”(《读劳伦斯小说——复郁达夫先生》,陈子善编《洵美文存》第22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它正是这本《死去的人》。1931年10月,邵洵美在《新月》第3卷第10号上发表书评,认为劳伦斯要表达的是:“耶稣不应当为了想贯彻自己的思想而便要他的肉体牺牲了应有的享受以经历不应有的痛苦。”(《〈逃走了的雄鸡〉》,《洵美文存》第215页)从相关文字看,邵洵美在1932年已经译完这部小说。1934年《美术》杂志第1卷第1期还曾刊出过画家张光宇为此书设计的封面,画面上是一个像邵洵美模样的人,赤着脚,捧着一只公鸡。不知道什么原因,此书当时没有出版单行本,直到1938年才在《纯文艺》杂志上发表,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也仅仅是刊出的两期,不过六七千字篇幅。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够有幸欣赏到邵氏译文的全篇。我还注意:在《新月》月刊上写书评,邵洵美依据的并非是后来巴金藏的这本书,而是题为The Escaped Cock这个本子,是巴黎Black Sun Press出版的,也就是说,此书,他至少有两个版本。一本喜爱的书拥有多个版本,这也是巴金的习惯。
巴金与邵洵美的另外一桩书缘,是邵洵美创办的第一出版社为巴金出版了《巴金自传》。这是“自传丛书”的一本,邵洵美听了胡适鼓动,认为“中国缺乏传记文学”,便起意出版“自传丛书”,这套书实际出版了沈从文、张资平、庐隐、巴金和许钦文的五种,邵洵美为《巴金自传》写出版介绍是这样:
巴金先生的作品,充满了人间的苦闷和哀愁,但有一贯的对人间的爱的感情流注着。他这一种对于人间的爱,对于真理的热情,是怎样孕育产生的呢?先生为四川世家子,自来上层阶级,每多革命前锋,因他们才能真知灼见自己一类的罪恶,而同情于被压迫者。因为厌恶自己,人生途中便到处都是悲哀,又因为同情于他人,所以有爱的流贯。一切文章作品,都和作者的环境有很深关系的。《巴金自传》读过之后,你便能真个了解巴金的人和作品了。这不仅是广告的文词,但有真正的广告价值,也应得是真正的广告。(原载1934年11月3日《人言周刊》第1卷38期,现收《洵美文存》第298页)
巴金对这本书并不满意。很重要的原因是书名由《断片的回忆》被改成《巴金自传》。估计编者是为了统一丛书中各本的书名,也是为了招徕读者才这么做的。偏偏巴金他向来不喜欢做名人,更不大喜欢名人的做派。还有些细微的原因,“我不满意它,因为除了错字多、售价贵以外,它还比我的原稿少一章,那是被审查会删去了的。”(《〈忆〉后记》,《巴金全集》第12卷第4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此书售价是大洋六角,我查了一下后来出版的《忆》,内容比此书几乎多一倍,平装三角,精装四角五分,虽然《巴金自传》纸张要好一些,相比之下还是贵了些。删去的文章是《信仰与活动》,也是书中意义非凡的一篇,作者都不高兴自己的书残缺不全。1936年,改名《忆》,增补了几篇文章,巴金在自己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了此书的新版,这也是以后通行的版本。而以《巴金自传》为名的这本,仅印一版,倒成了稀罕版本。
这是巴金与邵洵美的“隔空”交往,在1930年代,他们同在上海,是否有过面对面的接触呢?1936年2月出版的《六艺》杂志中有一幅鲁少飞画的《文坛茶话图》,上面“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尝君邵洵美”,邵洵美请客不是稀奇事,他能否请座中诸人才是一个问题。退一步讲,即便是在画家设计的虚拟场景中,巴金和鲁迅也是站在离邵氏很远的另一端。巴金和邵洵美,显然不在一个朋友圈内,不过,他们的朋友圈中却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如此说来,两个人能否相遇呢?我只能说有这个机会,可是我还没有找到具体证据。近年来陆续发表的傅彦长日记中,对三十年代上海文人的交游情况记载甚多,其中涉及邵洵美之处很多,谈到巴金的也有。可是,关于两个人碰面,只有一次疑似的记载。那是1932年7月17日日记:“到新雅、中社、海青,遇王礼锡、徐仲年、钟独清、荣玉立、邵洵美、谢寿康、徐悲鸿、陈抱一、汪亚尘、陈春随、华林、田汉、李宝泉、关紫兰、火雪明、巴金、索非、徐调孚、曾仲鸣、吴曙天、钱君匋、顾均正、孙福熙、章衣萍、周乐山等。”(《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1期)那一天,傅彦长是去了三个地方遇到这些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分别在三个地方,而非同一处。他的日记中,记载过巴金的一次请客:“到界路中国银行、安乐园、南京影戏院、新雅(晚餐,巴金请,列席者林微音、叶秋原、李青崖)、大华跳舞厅 (林、叶两人同往)。”(1933年3月6日日记,《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5期)这里有好几位都同邵洵美来往很多,但是巴金请客名单中偏偏没有邵洵美。或许可以判断,两个人即便平日里有来往,也算不上比较密切的朋友。不过,邵洵美在文章中曾提到巴金和他编辑的图书。谈文学批评时,他说:“譬如茅盾或是巴金的一部小说,作者的抱负一定非凡,但是经批评家一说它是在要暴露某一阶级的罪状,或是在要显示某一阶级的功劳时,它的意义便确定了,便有了限止了,它便死了。”(《伟大的晦涩》, 《一个人的谈话》第15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7月版)谈到沈从文的《八骏图》,邵洵美说,此书是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这书装潢很幽雅,尺寸也可爱,足见编辑丛书的巴金先生的趣味”(《不朽的故事》,《一个人的谈话》第115页)。
1963年,巴金与邵洵美倒是因为书又有了一次来往。当年8月2日,巴金在日记中记: “邵洵美来信借书。”(《巴金全集》第25卷第278页)我未能找到这封信,从当年8月20日巴金日记再记中大致可以了解此信的内容:“复邵洵美信,说我没有Loeb’s,clasics希腊、拉丁名著英文对照本。”(《巴金全集》第25卷第
285页)不知道邵洵美要借的是“洛布古典丛书”中的哪几种,这套书是美国人詹姆斯·洛布(James Loeb)主持印行的,他组织英美的古典学专家将希腊、罗马文化原典译成英文,为了体现准确性,这套书采取的是希腊、拉丁语原文与英文左右页相互对照的方式,而且每卷都有专家的导读和详尽的注释,这正是做翻译需要的版本。邵洵美借书,也是那段时间做翻译参考。此时的邵洵美没有公职,只有译书为生,1958年,他遭受不明冤狱,身陷囹圄,直到1962年4月才无罪释放。他的夫人盛佩玉曾写信向女儿描述刚出狱的邵洵美的状况:“他进去前胖胖的,出来骨瘦如柴,头发雪白,佝偻着身躯,缩得小小的,一动就喘……”家徒四壁,邵洵美环顾四周之后说,“都是身外之物,身外之物,没有了,不足惜。”幸好儿子为他保留了百来本书,邵洵美看到一直使用的那本英文辞典Webster Dictionary,十分高兴,说:“太好了!太好了!这是宝贝,有这本就行。”(转引自邵绡红《天生的诗人——我的爸爸邵洵美》第370页)
在有关方面的照顾下,邵洵美为出版社译书,出版社每月预支定额的稿费,维持生活,那时做翻译工作,邵洵美最苦恼的就是找资料书。他曾公开抱怨过:“翻译这部诗剧,还有一个极大的困难,这也同时是翻译一切外国古典文学所存在的困难。那便是参考材料问题。我国各处图书馆所保存的关于外国古典文学的书籍,大部分不过是供给学校教材的应用;私人的收藏,又是各人凭着各人的爱好,零零碎碎,没有系统。”(《〈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译者序》,《洵美文存》第415页)邵洵美写信向巴金借书,这说明,他确实急需,否则不会向来往并不密切、且身份和地位已经有很大差异的巴金求助。当然,也不排除他们两人还是有相当的来往,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这也与巴金的一个“缺点”有关,他常常是做了的事情也不说,也从不会去炫耀或宣扬什么,哪怕他帮助了别人。
这么说,是因为在邵洵美去世后,巴金还真的为他的事情帮过一点忙。1979年8月5日,巴金日记中记道:“邵洵美夫人和一个小儿子来访,说要写信给周扬,请我转交。”(《巴金全集》第26卷第357页)当月15日日记又记:“邵洵美夫人和儿子送信来。”并在16日日记中备注:“寄罗荪信(附邵夫人信)。”(同上,第359页)这是盛佩玉为丈夫的平反和落实政策而奔走,求助巴金帮忙。一年多之后,1980年12月8日日记中还记:“邵洵美夫人来。”(同上,第434页)巴金是通过在中国作协任职的孔罗荪转信给周扬,现存巴金给罗荪的书信中有三封书信谈及此事,但是日期是1982年,距盛佩玉第一次拜访巴金已经过去三年,看来此事的解决绝非一日之功,恐怕盛佩玉写了不止一封信。罗荪在1982年2月26日给巴金的信中回复了初步的结果:“您的来信和附来邵洵美夫人的信都已收到。她给周扬、夏衍同志的信,我也已分别送去,周扬同志表示,他将给上海陈国栋、胡立教两位同志写信请给予协助,并将原信也附去,这样或可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有点情况我当另外写信给陈茵眉,再请她过些日子与市委联系一下,我想胡立教同志或可能直接同她联系。”(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7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版)转去的信显然起到了作用,邵洵美在1985年终获平反。盛佩玉、邵绡红的书里提到夏衍和周扬为邵洵美帮忙的事情,不曾提过巴金。从这些资料看,巴金也在背后为老朋友尽了一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