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茂元《唐诗选》再版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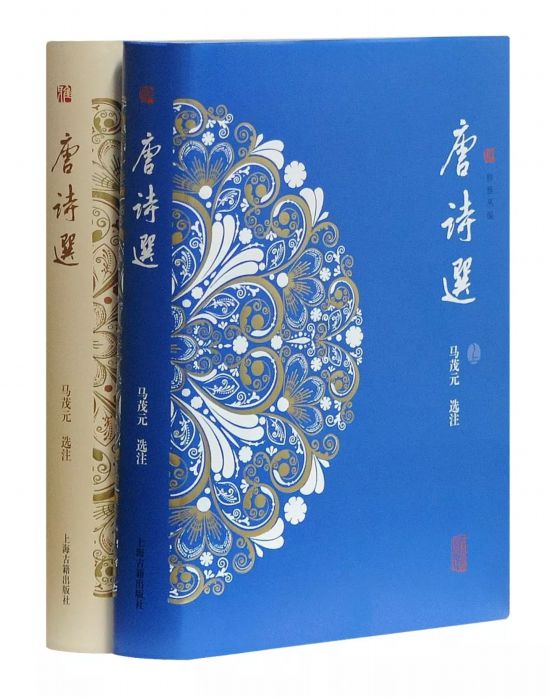
我小的时候,对中国古代诗歌有浓厚的兴趣,一度达到痴迷的地步。觉得诗歌跟别的文体不一样,音韵铿锵,朗朗上口。那时候凡目所及的诗歌皆能成诵。可惜穷乡僻壤,得书太难。每看到一首新诗,都高兴得如醉如痴,比如在亲戚家看到墙上挂的画里有一首诗,都要先背下来,回家写到自己抄诗的本子上。那个时候我对诗歌的渴求,就像饿急了的人,凡是能吃的东西,都会不加选择地塞进嘴里。后来有个朋友说太精妙的诗歌不适合给孩子读,这种论调实在太奢侈了。当然,如果那时候我手中能有一本马茂元的《唐诗选》该多好啊!
马茂元《唐诗选》选录诗人一百二十六家、诗作近六百首,数量适中,所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除大家名家外,为再现唐诗的整体风貌,也兼及小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唐诗的艺术特征和发展脉络,是建国后第一部《唐诗选》,也是最受欢迎的唐诗选本之一。全书有马茂元先生的诗学观一以贯之,所以更具系统性,可作一部唐诗史来读。既是普及读物,又有很高的学术性。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订重版,重排重校,改正了原书的少量舛误和部分注音错误,收入《粹雅丛编》中。大字疏排,适当留白,与大唐舂容缓雅的气度相副,也让读者获得最佳的阅读享受。这本书从普及方面讲,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就可以读懂;而从学术方面讲,即使是中文系的教授博导读了,也同样有收获。马先生的语言通俗易懂自带光芒令人愉悦:
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可说是达到完全成熟的境地了。无论题材、式样、语言和风格,无论初唐、盛唐、中唐或晚唐,都使人们读了好像进入百花争艳的园圃一样,深深激起了一种“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愉快和喜悦。这许多诗人,在思想和艺术的修养与造诣上,各不相同;成就的大小,也相差很远。可是,他们都富有新鲜活泼的创造精神。李东阳曾说:“唐人诗不言法,诗法多出于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怀麓堂诗话》)这话用以否定宋诗,虽不免过激;但“唐人诗不言法”,却是事实。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正如马克思所说:“就使一滴露珠,照映在太阳光里,也呈现无限多样的色彩。”(《关于普鲁士最新审查条例的备忘录》)唐代诗歌之所以如此吸引人们的爱好,乃是无数多样色彩的露珠,在时代精神的太阳光里所放射出来的总体的光辉。
具有深厚学术修养的大家,写起普及性的文章来,那种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像手持千钧棒而能舞动自如毫不费力,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比如诗人张祜的名字,早有张祐之讹,因为祜、祐字形相近,与字承吉之义也相通,无法用名、字相关来判定真伪。但是马先生引《尧山堂外纪》载张祜轶事一则,云祜子曾作冬瓜堰官,有人讥其任此漕渠小职,祜解嘲曰:“冬瓜合出祜子。”以祜谐瓠音,冬瓜和瓠子都是葫芦科的植物。据此,知作祐者误。可谓一语解纷。又如妇孺皆知的李绅《悯农》一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餐字,马先生注音为sūn。注释:“熟食的通称,这里指饭。通飧。”这可能跟一般人印象中不一样,但真的不是注错了。大家读cān好多年了,确定要读sūn吗?也许是的。这里“盘中餐”的用法跟杜甫诗“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中的“盘飧”相同,都是指盘子里熟的食物。就像我们经常背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样,正确的版本其实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晋文公出亡,箕郑挈壶餐而从。”王先慎集解:“餐,《御览》八百五十引作飧,四百二十六、二百六十六引作飧。”《三国志•魏志•和洽传》:“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引此文作“飧”。胡三省注曰:“飧,苏昆翻,熟食曰飧。”这可以证明餐、飧是通的,二字字形经常可以互换。《汉语大词典》里面也有餐读sūn这个义项。
又比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坳字马先生注音为āo,而现代汉语里坳读音为ào,无āo这个读音。孰是孰非呢?按,此处当然应该读āo。因为这首古风开头五句押的是平声韵(到第六句才换仄韵),而号、茅、郊、梢、坳在韵脚,当然读平声。
另一首陆龟蒙的《白莲》:“素蘤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这诗咏白莲,若即若离地从空际着笔,写出了花的淡雅清幽的意态之美,同时也流露出作者乱世隐居的孤高寂寞的情怀。蘤字一般认为是花的异体字,但是马先生注读作wěi,“素蘤,犹言素质”。首先,从意思上说后面是“此花”,为了避重,前面也不可能是“素花”;其次根据格律诗的规则,“素蘤”的“蘤”处,应该是个仄声字,所以蘤字不会是huā(花)。按,《唐韵》蘤字为韦委切。《玉篇》释蘤为“花荣也”,平水韵里把蘤归为上声四纸韵,只有《字诂》里说蘤是古花字(蘤同花,的确是最常见的义项)。可见马先生注的是确凿无疑的,此处蘤既不读huā,更不能简化成花字。
此种细节,最能见茂元先生深厚的旧学根柢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例子不胜枚举。正如赵昌平先生在序里所说:“每论及一义,即随机应发,旁征博引,真有口若悬河,花烂映发之感。”据昌平先生说,茂元先生能背诵的唐诗过万首,“观千剑然后识器”。大量记诵基础上的出色的感发能力,将马先生天赋中对文本的感悟力,磨炼得越益敏锐。这是马先生唐诗研究的个性特征,也是他最为雄厚的“资本”。这本《唐诗选》是马先生选取最脍炙人口的唐诗,再加以最精到的注释,至于每篇后所附之评语,则是昌平先生亲承茂元先生遗意,投入很大精力完成的,书出版时,昌平先生退逊而不署名,又撰唐五代诗概述附后。本书是两代唐诗学者的学术结晶,也是老辈学统和道德的继承发扬。读者一书在手,就像漫步在春天的大花园里,“花烂映发”各种花烂漫开放,令人目不暇给,身心怡悦。这种读书收获的乐趣,真的像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所说的“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