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现代人,但怀揣的还是古老的心灵”——刘亮程谈新作《捎话》

刘亮程(丁杨/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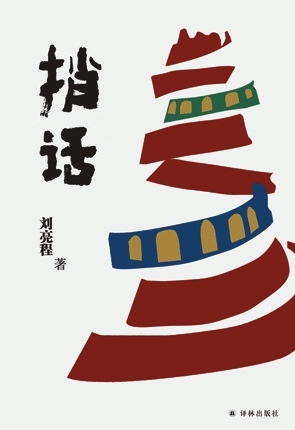
《捎话》,刘亮程著,译林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58.00元
“在这本书中,人的‘捎话’只是线索,更多的是动物与其他生命、鬼魂的话语。所有这些声音被一个小说家通过一部小说带到了今天。”岁末的北京夜晚寒风凛冽,从乌鲁木齐赶来的作家刘亮程在王府井大街言几又书店一角的暖黄柔和灯光下,面对几十个读者说:“当千年前的众声喧哗被今天的人们听到,它就依然是今天的声音。历史并没有过去,历史中那些声音也没有完全湮灭,当我们把它唤醒,它依然可以刺痛今天的人,被今天的耳朵听到,被今天的心灵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说家——‘捎话人’的职责。”语速不紧不慢的他表情从容而略带神秘,这段即兴表达和他的文字有异曲同工的气质。他提到的这本书是前不久出版的新作《捎话》,那个“捎话人”,就是他自己。
“捎话”一词在互联网普及、移动社交方式多元的今天显得复古且略带乡土气,不过,刘亮程以此为关键词在新作中讲述了一个建立在“万物有灵”观念上的故事——毗沙国与西邻黑勒国因诸多纠纷而冲突频仍,几十年的战争令两国百姓难以交往,甚至书信隔绝。于是“捎话人”这个民间职业悄然兴起,书中主人公库即为精通多种语言的“捎话人”,另一位主人公是通晓人言的小母驴谢,从毗沙到黑勒,情节由此展开。作者将故事发生的历史年代与地域范畴虚化,但从诗意、精炼、隐喻重重又带有超现实意味的文本讲述中能够对应和印证,令时空背景清晰起来。这部作品的语言非常有特色,想象力充沛,对一些抽象和难以量化的事物有着跨越感官的呈现。这些天马行空又沉郁哲思的文字赋予“捎话”这个词以信息传递、情感交流乃至心灵沟通、信仰流传的多重含义。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刘亮程并不讳言通过写作《捎话》对那段千年前关乎信仰的历史有所思考,对触及人类心灵之痛的沧桑变故亦有感慨,进而,对信仰、死亡等一言难尽又无可回避的命题进行文学虚构上的阐释,“我以前的作品,大多在个人经验范围内写作,《捎话》进入纯虚构。一个作家要有虚构世界的能力”。这是他在《捎话》“附录”访谈中的表达,“捎话的本意是沟通。贯穿小说的也是不断的和解与沟通。只是有些话,注定要穿过嘈杂今生,捎给自己不知道的来世。那或许就是信仰了”。
中华读书报:《捎话》的版权页上标着“长篇小说”,读起来却有些散文感,也像是民间传说或成人童话,还有强烈的寓言感。您自己怎么定位这部作品?
刘亮程:这是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小说中还存在一些散文的痕迹,但从叙述方式到整个文本结构都是小说式的。
整部小说写了有四年吧。记得2014年的时候,我的QQ头像上标着“2014《捎话》”,之前一些年QQ头像上都写着“《凿空》”,我是以此纪年啊。之所以《捎话》写了这么久,是我很长时间内想不清楚应该以什么方式去写。这是一部有着隐约背景的“历史小说”,但写的又完全不是历史。懂历史的人看这篇小说会想到,书中的故事来自发生在公元一千年前后西域那场长达百年的宗教战争。我一直在读跟那段历史有关的文献,可是那段历史留下来的史料很少,还有一些民间传说、诗歌、传记。我是想把“改宗”这个历史事件写到小说中,那是心灵之变。一种延续了数十代的精神信仰,要改换成另一种的时候,人们会作何反应?这就是我写《捎话》的一个动因。
我们所经历的现实社会很平静,尽管也有那么多文学作品去叙述历史中的种种运动。那些文学作品所讲述的社会动荡、战乱,看似残酷,但对肉身的屠戮和抹杀毕竟只是皮肉之痛,我更想尝试用写作去接近心灵之痛、灵魂之痛。
中华读书报:也就是说,写《捎话》的动因已有,故事的历史背景和一些文字素材也是存在的,但用什么方式呈现需要反复斟酌。
刘亮程:其实历史背景和素材也说不上什么存在,因为无法直面那段历史。有时候,书写历史也是回避历史的一种方式,写历史并不是真正要揭露历史。但是,历史深处的痛会一直通过时间传递给我,我就要把这种心灵之痛写出来。
我最初的设想和动笔后的写作情况截然不同。一开始连书名都不是《捎话》,而是《偶像》。那是一个偶像时代,神的偶像出现在寺院和每个家庭的角角落落,每个人心中都有许许多多挥之不去的偶像。我们现在把偶像低矮化、市民化、娱乐化,所以我就是想通过写作找到心中原初的偶像。
中华读书报:写作过程顺利吗?
刘亮程:整个写作过程中,我总是想好了再去写。最后完成的《捎话》,是从一头驴开始写。第一章,就是从驴的视角写一段,以人的视角写一段,第二章整个都是驴的视角,写到第三章的时候,驴的视角和人的视角混杂在一起。确定了毛驴这个角色,找到用毛驴的视角来叙事,就给我的写作开了方便之门。从驴的视角看,人世间的惨烈也变轻了。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驴车上的龟兹》《凿空》等许多作品里都写到了驴,到了《捎话》里驴干脆成了主角。为什么您对这种动物情有独钟?
刘亮程:因为我写的那些地区跟驴有关系。在新疆的游牧区域基本上都是马的天下,而像塔里木盆地区域,那里绿洲上居住的农民主要接触的是毛驴。驴可以帮人干活,很好养活,也能跟人交流,有意思。有些动物,像牛,可以出力,能耕地拉犁,但是没意思,跟人不怎么交流。
中华读书报:于是您用了拟人化的写法,用驴的视角看书里的世界。
刘亮程:不能简单地用拟人化去理解书中的那头毛驴。它就是它,就是那样看世界的。我写它的时候从来不认为它是在替人着想,它在想我所想,想它所想。
中华读书报:这样用驴的视角来叙事,以及有历史根据但叙事中又淡化历史感,这些处理给您提供了叙事的自由和便利?
刘亮程:是的。我觉得,即使是写一部看似有历史背景的小说,有时也要避开历史对作品的打扰。历史既是你的参照,也需要你把它推远。这部小说是在写我从那段千年前的历史中感受到的心灵之痛,有这点痛的存在,那段历史就可以被放得很远。有这点痛,就可以去创造一个自己的历史空间,把这个痛安置进去,让这部小说完成。好的“历史小说”应该孤悬于历史之外,作为单独的文学存在。
中华读书报:从《虚土》《凿空》到《捎话》,印象中您的前两部长篇哪怕是现实题材也有很多超现实的处理。但《捎话》这部长篇从形式上是在超现实的路上走得最远的。
刘亮程:应该说这是我这种写作体系体现得最完整的一部作品。从《一个人的村庄》开始,到《虚土》《凿空》《在新疆》,我这种书写人、动物、万物的方式其实一直如此。只不过在这部作品中,我把这么多年积累的这个体系完整呈现出来,就是人与万物同构共居,建立起生命或灵魂体系。这本书中所建构的世界的层面,从地上到天上,声音的层次、构造,还有那种人和其他事物相互交流的关系,这种设定都是以前作品中偶尔会有的。
像毛驴这个角色,跟随我的写作很多年了,以前我的作品中也出现过。只不过以前它只是偶尔出现的角色,但在这本书中它成了事件的主要叙述者。我也给了它更多的权利,在《捎话》中小毛驴可以听到、“看到”人们听不到看不到的那些灵魂的声音以及声音的形状。这样我就把世界分成了现世世界和灵魂世界,把看见那个灵魂世界的任务由毛驴去完成。这个说法在民间也是有基础的,民间一直认为驴眼睛能看见鬼。这部小说试图完整建立起这样一个体系,其中有我对民间传说的印象,但没有照搬任何民间传说,我是全部把它消化、组装在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
中华读书报:您一再提到贯穿《捎话》其中的“痛”,以及这部作品中关于黑暗和死亡等主题的叙写,都以诗意的语言,平和的姿态去写。这是您笔下的痛和死亡有别于很多其他文学书写的地方。
刘亮程:这部作品中所写的这段故事是发生在千年之前的,千年之前的死亡放到现在看都是永生,不管是怎么死的。这是我们隔着千年的时间回看死亡的一种态度,千年来,所有的生都归于土归于灵魂。我远远地去写,就有这种超然感。作为作家,以文学对死亡的写法,是要给死亡找个隐身之处。这可能是每个作家都想用写作去实现的,但要遵循现实主义的讲故事方式,从生到死,把故事讲完就完了。可是,在我们的民间文化中,在作家的想象和创造中,也许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死亡,这种死亡像生一样漫长,甚至比生更久长。关于“死亡”的写作是写作这本书时最吸引我的地方。作家,不可能不去思考死亡。
中华读书报:书中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句子,比如“人不知道驴为啥不住地叫,但驴懂得人为啥不住地念经”,还有“驴说,人真是个好牲口啊”,这样的句子承载了一些隐喻。整本书写下来,包含着很多您对生死、精神世界以及对千年前那段历史的看法和寄托吧?
刘亮程:首先,我在写作中不会主动去写隐喻,隐喻是一种我写作时经常会忘记的修辞方式。我也不认为我写到的那些事件,或者写到毛驴的部分,就是隐喻。驴写成那样,那就是我心中驴的样子,并不是有意拟人化。
我们的文学欣赏习惯总会觉得,哦,那是不是拟人化。其实你要把这种欣赏文学的习惯忘记,就会觉得,那头驴就是一头普通的驴,并不是超乎我们平常经验的拟人化的驴,它是一位心怀万物有灵理念的作家笔下呈现出来的一头驴,也是在大地上拉着驴车、载着人、帮人干活、吃着粗草料的普普通通的毛驴。只不过这头驴的心灵从来没人关注过,谁会在乎家里那头毛驴怎么想事情。
中华读书报:这么写,首先您自己是信服的。
刘亮程:是啊。我希望读者读到最后也仍然只是把它当成一头毛驴。我写了这头有神性的毛驴,是因为我坚信驴是有神性的。我也希望通过阅读,让这头有神性的毛驴回到人间的毛驴群中,被大家重新认识,这也是我对一头驴的交待。本来就是这样的。
中华读书报:您对语言的准确、精炼、诗意等等是很看重的,在写《捎话》的过程中,怎么令小说的语言达到您自己的要求?
刘亮程:一般来说,语言的润色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就基本完成的,但写完全部之后再反复看、修改也肯定是必要的。看的过程中会做一些调整,这个过程主要是做减法,把多余的字和词都删掉,其实也相当于做加法,当我把一个句子中多余的字删掉的话,这个句子中也增加了一些东西——干扰句子的字词去掉后,句子增加了韧性。
中华读书报:昨天您在北京的那场新书分享会上说到,对你来说不存在选择写作主题的问题,这些年来您的写作最大主题就是新疆。这是你生活和写作的地方,是你最熟悉的地方,类似的情况在一些中外作家中也存在,所谓文学母题和写作原乡的话题,对此您怎么看?
刘亮程:每个作家都有不一样的追求,有些作家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更多地呈现这个世界,讲更多故事。我的写作从一开始到现在,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构筑完成我的语言体系、意象体系,通过这些完成我的那个文学世界。除此之外,我不愿在别的地方多费笔墨浪费时光。
中华读书报:总的来看,您的写作还是比较有规划性的。
刘亮程:我写得很慢,一天能写一千字就非常多了。不过我每天都写,在飞机上、在路上也会写,即使不写小说也会写别的,往往几个东西一块写。即使这样,我仍然写得不算多。写那么多干什么呢?
中华读书报:昨天的分享会上,您还有个说法让我印象深刻。您说《一个人的村庄》是当年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回忆乡村生活写出来的,那时离开了故乡,反而故乡的一切都清晰起来。这是否意味着这种非虚构写作需要和写作对象有一定的时空距离才好?
刘亮程:不止是需要这样的时空距离,或许是必需的。作家无论写什么,都有必要拉开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去审视要写的东西。你曾经身在其中,等你写的时候已经站在远处,站在远处的时候你才具备写作者应有的眼光、广度和深度。
中华读书报:《捎话》和您上一部长篇《凿空》隔了八年,您说自己现在的写作速度比年轻时快。听说您已经在写下一部长篇了,进展如何?
刘亮程:新作正在写,可能2019年会写完,是以《江格尔》(流传于新疆、内蒙等地的蒙古族英雄史诗)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这几年我一直在读《江格尔》,边读边想,这部史诗诞生的那个时代,人类是如何想象这个世界的。读着读着又感到不过瘾,觉得古人的想象力是有模式的,总是想到某种程度就想不下去了。那好,我就在古人想不下去的地方继续往前想,在史诗的尽头进行无边无际的想象。
其实《捎话》主要写“死亡”,正在写的这部小说是关于“时间”的,写得非常顺利,因为这部作品比《捎话》天真,这里的天真更适合我。通过这部小说的书写,解决了困惑我多年、难以用文字去呈现“时间”的问题。“死亡”和“时间”都是作家要面对、思考和呈现的,如何把“时间”具象是书写“时间”的难度所在。你哪怕写完一整个朝代,都未必呈现出一点点时间。时间不止意味着历史纪年,也不止是人从小长到大、生老病死,那时间到底是什么?看似一个哲学问题,有赖作家去探寻。我看到有评论家说,《一个人的村庄》是在写时间。我想说,就是在写时间啊。那些细小的时间、经过村庄的细小事物被我捕捉到了,也可以说我把时间逮住了。
中华读书报:和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相比,您的写作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文本给人的感觉,都突出一个“慢”字,或许这样的写作刚好把飞速变化的时代中来不及带走的有价值的东西用文字记录了下来。
刘亮程:作家在呈现这个时代之变的时候,也同时在观照人类心灵中哪些东西没有变。变只是一个社会的表象,具体到人类心灵的核心是不是在变,就需要作家去考证了,我一直在关注和书写不变的东西。
在大家都接受新生事物的背景下,我相信人的心灵还是古老的。一群现代人,穿着时代的艳服,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以及外表的变化,但怀揣的还是古老的心灵。那个心灵可能是唐代的,也可能是宋代的,它没有跟我们的身体走到现代,没有急于到达今天,而是慢悠悠地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