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改革文学的扛旗者

在中国当代文学塑造的人物长廊中,“乔厂长”——乔光朴无疑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小说人物之一。1979年,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当年第7期上发表。一时间,小说中这位主动要求到濒临破产的重型电机厂担任厂长、并以铁腕手段推行改革的乔光朴厂长,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蒋子龙回忆说,当时甚至“有人贴出大标语欢迎我的‘乔厂长’到他们那里去‘上任’”。可见,乔厂长这个人物形象的出现是多么恰逢其时,寄托了当时多少人变革现实的热切期待。在通行的当代文学史叙述中,“文革”结束之后,以追求城市和农村现代化为主旨的文学类型被归为“改革文学”,而乔厂长则堪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蒋子龙也就顺其自然地被视为“改革文学”的扛旗者。继1979年发表《乔厂长上任记》之后,他笔耕不辍,1980到1982年间井喷式地创作了《乔厂长后传》(《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新港》1980年第5期)、《开拓者》(《十月》1980年第6期)、《狼酒》(《中国青年报》1980年9月20日)与《拜年》(《人民文学》1982年第3期)等一系列工业题材小说,生动而全面地记录了改革初期工业生产领域的变革历程。
对现代大工业有着特殊兴趣与深刻观察的蒋子龙,不是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作家。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子弟,也曾是参与绘制祖国领海蓝图的海军士兵,更是一名曾经长期奋斗在生产一线的车间工人。事实上,直至在文坛上“功成名就”以后的1982年,他才被调入天津市作协,成为一名职业作家。2010年,业已69岁的蒋子龙回顾道:“我现在常常集‘三老’于一身:‘老工人’、‘老兵’、‘老作家’。唯‘老作家’担不起,我以为作家能称‘老’,不是光靠熬岁数,成就最重要。‘老兵’则可以认领——1960年的兵,还不算老吗?至于‘老工人’,领之泰然,且欣欣然。”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老工人”,这并非只是自谦的缘故,而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认同。由此我们也便明了,为何蒋子龙总是喜欢自称为“工人作家”。在晚年的自述中,他没有认领“改革文学”扛旗者的尊号,而是不断强调工厂生活才是他写作工业题材小说的活水之源。纵观蒋子龙的创作生涯,不难发现正是有赖于极为丰富的工厂生活经验,他手中的笔才能够紧紧地追随时代脉动而起舞。
“工人作家”的养成
1941年,蒋子龙出生于河北沧州豆店村。童年的他看得最早和最多的“文艺节目”,就是听村里的“能人”讲神鬼妖怪的故事。在那声波构筑的另一个世界里,他滋生了对文学的最初兴趣。后来他又迷上了京剧和河北梆子,每到过年和庙会就跟着剧团跑,很多戏词儿都能背下来。到了小学四年级,初通“识文断字”的他,便迫不及待地做起了“念故事的人”。夜灯初上,他便趴在炕上给村民念故事。《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济公传》等,都是他书场上的读物。12岁进沧州城,14岁赴天津卫。一个农村子弟在天津念起了中学,多多少少会受到一点歧视。1958年初,一向成绩优异的他在“整团运动”中成了全校重点“帮助对象”,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原因是他有着“想当作家”的名利思想。突然遭此“莫须有”的罪名,生性倔强的蒋子龙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恶气,他开始发了狠劲地写稿子,想要真的发几篇文章给批判者瞧瞧。可惜他投出的稿件全都如泥牛入海,对文学的首轮冲击宣告“惨败”。很快,他就从中学顺利毕业,并死心塌地地进入了天津铸锻中心技术学校学习,他对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和操作技术同样有着强烈的兴趣。从技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天津铸锻中心厂(后更名为“天津重型机器厂”)工作。此时的他把成为大工匠(即八级工)作为人生目标。只不过生活里不能没有小说,每天不管多忙多累,蒋子龙都必须要翻上几页书。
1960年,就在工厂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蒋子龙应征入伍,穿上了海军军装,并考取了海军测绘训练学校,光荣地加入到新中国领海绘制的事业中。按照他的话说,人生走到这儿,“从农村到城市,由城市进工厂,从工厂到部队,经过三级跳把工农兵全干过来了”。无巧不成书的是,在部队期间,蒋子龙与文学的缘分居然更进了一步。当时的部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蒋子龙被认为是最会“摇笔杆子的人”,话剧、相声、快板、歌词,无所不写,包打天下。这时的他把制图当作自己的本职工作,文艺创作不过是“不务正业”。但当他亲眼目睹一位农村社员因为他写的诗而感动落泪时,他被深深地震撼了,开始重新看待手中的笔,更加敬重文学的力量。他和年幼时那个浸泡在“闲书”中的自己,再度相遇了。经过长期练笔和不懈努力,他的小说处女作《新站长》终于在1965年的《甘肃文艺》发表。这篇小说源于真人真事,讲述了一位气象站站长在战时状态下不敢预报天气,不想承担责任,进而延误战机的故事。把真事化为故事,仿佛有什么力量在推着蒋子龙往下写:“一打算写小说,我认识的其他一些性格突出的人物也全在我脑子里活起来了,仿佛是催着我快给他们登记,叫着喊着要出生。” 从这篇作品开始,蒋子龙的创作模式已经很明确了,那便是生活“逼”着他去写下最真实的观察和思考。
也就是在1965年,蒋子龙复员转业,重回天津重型机器厂。不久,“文革”爆发,他退回车间,从工人一步步升为生产组长、工长、车间主任。在此期间,他陆续发表了《三个起重工》《弧光灿烂》《压力》《春雷》等作品,逐渐成长为一个小有名气的工人业余作者。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进一步深化。同年10月底,第一机械部在天津召开工业学大庆会议,落实中央钢铁座谈会(1975年5月8日-10日)的工作精神,目的是“抓革命、促生产”。蒋子龙作为天津重型机器厂的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令他眼界大开,许多知名大厂的老干部和老厂长齐聚一堂,令他产生了“一种久违的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敬佩”,被各地工厂领导“抓生产”的事迹深深打动。他回忆道:“我当时正被大会上的一些人物所感染,经历了近十年“文革”的压抑和单调,这种从骨子里被感染的经验是很新鲜的,身上产生了一股热力。” 正当此时,复刊在即的《人民文学》稿源缺乏,编辑许以、向前专程赶来天津,找到了正在开会的工人业余作者蒋子龙,约他为《人民文学》写稿。双方一拍即合,蒋子龙的“热力”终于有了发光发热的机会。他在会议期间(此会开至11月初),便一气呵成写下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小说中的机电局长霍大道是以出席会议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厂长冯文斌与另一位会上认识的南京汽车厂副厂长为原型。《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在《人民文学》复刊后的首期,即1976年的第1期上,而且作为复刊后推出的重磅之作,被刊登在十分显眼的位置。事后看来,正是这次机缘巧合的约稿,彻底改变了蒋子龙的文学生涯和人生命运。

1978年秋,蒋子龙在天津重型机器厂门口留影
笔尖上的改革风云
在文学“国刊”上发表作品,既让蒋子龙名声大噪,同时也把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走向峰巅还是坠入谷底,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从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编印的简报来看,《机电局长的一天》(以下简称《一天》)发表初期,好评不断。据当时《人民文学》的编辑周明回忆,叶圣陶、张光年、陈荒煤等老同志都很喜欢这篇小说。但1976年前后的政治风向瞬息万变,暗流涌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又异常密切。《一天》发表不久以后,全国便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到了1976年3月,编辑部简报上的读者来信便有一半都认为《一天》存在严重错误。原因是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霍大道不是“革命小将”和“新生力量”,竟然是一个“瘦小干枯的病老头”,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没有体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被冠上了“宣扬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等帽子。3月15日,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召开了一次创作会议,蒋子龙到场参会。于会泳在18日的报告中指出,有些“坏小说”影响很大,倾向不对,作者应当勇于认识错误,主动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于会泳不点名批评的正是在座的蒋子龙。这次会上还决定让蒋子龙在《人民文学》上作公开检查。同时,为了遵照“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指示,蒋子龙还被安排参与了话剧《红松堡》创作组,并写出了反对走资派的小说《铁锨传》。《人民文学》编辑部计划把《铁锨传》和蒋子龙的检查放到1976年的第4期一起发表。蒋子龙心不甘情不愿,写出来的检查始终不“合格”,后来几经修改,终于没耽误在第4期与《铁锨传》共同刊出。
未曾料到,因印刷厂机器故障和地震的影响,第4期延期了半个月才出刊。就在这短短半个月里,事情又出了岔子。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中编发了《一天》所引起的社会政治反向,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因此,批判《一天》的调门就越来越高,力度也越来越强,《人民文学》编辑部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不过,伴随着“文革”走向尾声,对于《一天》的批判也盛极而衰,逐渐不了了之。历史和蒋子龙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文革”结束后,《一天》虽不是“大毒草”了,但他为了“戴罪立功”发表的《铁锨传》又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为此天津市委还成立了“蒋子龙专案组”。他回顾这段心惊肉跳的历史时,只能自嘲道:“为一位业余作者单成立一个专案组,在全国大概只是我有这份福气。”
这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自然让蒋子龙刻骨铭心。很长时间以来,他下定决心与文学告别,一门心思当他的车间主任。1979年春天,他因病躺倒在医院里,手术的疼痛期尚未过去,《人民文学》的编辑王扶就冒雨前来慰问。王扶到访,首先是为《一天》的批判事件致歉,而更为重要的目的则是想要“收拾旧山河”,再次向蒋子龙约稿!蒋子龙已经两年多没有动过笔,憋了一肚子的话,对工厂的现实问题有着太多太多的见解和看法。他压抑了许久的心再次颤动了,当时他的专案组还没有撤销,他就躺在病床上构思新小说了,摩拳擦掌想要通过小说干预现实生活。后来躺也躺不住了,就申请提前出院,利用几天休假时间便写下了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此时的时局早已与他发表《一天》的1976年大有不同:“文革”正式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也已召开完毕,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过,人们在具体事情上的判断和认识还不完全一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之后,便收获了两极分化的评价:一方面,天津文学界对它猛烈批判,9到10月间,《天津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批判文章,总的观点是认为这篇小说正面描写了“文革”造反派郗望北,因而是反对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另一方面,北京的《文艺报》与《人民文学》编辑部则对这篇小说大加赞赏。时任《文艺报》编辑的刘锡诚便奉主编冯牧之名,写下了《乔光朴是一个典型》,此文被刊发在《文艺报》“第四次文代会专号”上。刘锡诚在该文中指出乔光朴是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的闯将。其他支持者也有着类似的观点,纷纷把乔光朴标举为“具有时代精神的先锋人物”(冯牧)、“四化的带头人”(宗杰)、“新时期的英雄形象”(金梅),等等。那么,为何北京方面会对这篇小说推崇备至呢?原来,“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中的哀怨情绪弥漫,暴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多,“向前看”的积极的作品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文艺界特别希望能够出现反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文艺作品,特别需要能够配合人民群众恢复生产迫切心理的文艺作品。如此看来,《乔厂长上任记》的出现非常及时,开辟出追求四个现代化的崭新创作主题,犹如“迎着春天里吹来的一股冷风而绽蕾怒放的鲜花”(宗杰)。最终,乔厂长被树立为四化建设中的头号“新人”,成为新时期的英雄形象。
争议背后的“真意”
除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和《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的很多其他小说发表后也都曾引发争议。比如1980年发表的《开拓者》中虚构了一位D副总理,激怒了不少人。再比如1984年发表的《燕赵悲歌》、1985年发表的《阴差阳错》等作品也都曾招致或大或小的风波。这就给我们造成一个印象,蒋子龙始终站在改革的潮头,是时代中的风云作家。正如蒋子龙自述,他的文学是“入世”的文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并不代表随波逐流或是盲目地追求轰动效应。当时代的喧响散去,留下来的是蒋子龙对于那个特定时代的观察与思考。“争议”之外,尚存“真意”。
以他的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为例。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够被铭刻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中,除去“时势造英雄”的幸运,其中更为内在的原因是,小说凭借若干典型人物形象呈现出不同社会群体在时代转型中的位置、心态、选择与行动方式,提供了一幅转型期的工厂“群像图”。进而言之,《乔厂长上任记》不是“改革纪实”,不是事后被拿来论证改革正确性的论据,而是以文学的方式探讨了改革初期现代大工业内部组织管理方式的调整及其带来的人心震荡,诚实而真挚地描摹出改革的动力与困境所在。
在“改革文学”中,还有一部重要的作品——柯云路的《三千万》。这部小说以老干部丁猛对经济指标“三千万”的核算作为故事主轴,塑造了一位具有责任感与开拓精神的老干部形象。乍看之下,《三千万》与《乔厂长上任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蒋子龙却曾坦率地指出他们之间的不同:
我跟《三千万》的作者柯云路同志说过:《三千万》这篇小说很好,但“三千万”的数字没有感情……最好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把“三千万”作为副线,不要把人物的感情、纠葛都拴在“三千万”上……我写乔厂长,乔厂长改革的成败与否,不影响乔厂长的感情,因为他的感情纠葛在他周围的人,包括上级、战友、对立面以及同他有过一段关系现在结成夫妻的人。而不在于他上任以后是否改变厂子的面貌。
需要说明的是,蒋子龙的小说里同样也充满了对数字和效率的崇拜,这是当时人们的共同意识。在这点上,他与柯云路没有什么不同。1978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里就写道:“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速度和效率成为了绝对的时代关键词。不过蒋子龙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他能够看到创造这些数字背后的人们。他不是要写一个老干部出山后便“势如破竹”、“马到成功”的故事,而是要把老干部放回到工厂特定的关系场域中,以老干部的活动为主轴,描写改革所带来的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人与物关系的更新。具体到《乔厂长上任记》,以乔厂长为中心,串联起一组人物,如此一来,改革故事便被他写顺了、写活了。蒋子龙回忆说,《乔厂长上任记》里的人物是“跳到他脑子里”的,这些人物都有着现实中的“模特儿”——
第一个到他脑子里报到的是冀申。冀申所代表的是极善揣度政治风向、精于经营人际关系网络的某些老干部形象。他们只会用突击会战的方式抓生产,而不会“用经济的方式管理经济”。谈到公事,满嘴“研究研究”,论起私事,则神通广大。蒋子龙概括这类人的特征是“只会做官,不会做事”,他们彼此之间已经织成了一个庞大的蜘蛛网,这张网是他们用权力、地位和欲望织成的。蒋子龙用心刻画冀申这个人物,就是想要说明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克服冀申们的阻碍。
第二个来报到的人物是石敢。石敢所代表的是因为“文革”而丧失革命热情的那类干部。他们曾经真诚地信仰革命,满腔热情,九死不悔。但在历次政治斗争中,他们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灰心丧气了。蒋子龙为石敢设计了一个细节,那就是他在“文革”受批判时,咬掉了半截舌头,成了口齿不清的“半哑巴”。空头议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石敢需要被乔厂长这样的开拓者引导,重新焕发对四化的热情。
乔光朴是第三个逐渐清晰起来的人物形象。他虽然跟冀申一样,同样都是复出的老干部,但他敢于冲破原有的权力关系网络,有魄力、肯实干,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他身上有着明显的优点,也有着看似冷酷,不近人情,不擅于处理对外关系等缺点。乔光朴的爱人童贞,是一位高级技术专家,其中寄托了当时对于知识分子和先进技术的重视。
除此之外,蒋子龙还大胆地描写出曾是造反派头头的郗望北这个人物。当时各个工厂里都有大量“文革”期间提拔上来的“火箭”干部,如果把他们全部否定,势必将对生产造成很大影响,并且加剧工厂内部的分裂。蒋子龙以很强的责任心,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郗望北这类干部经过正确的引导,也可以为四化做贡献。
总之,《乔厂长上任记》的篇幅虽短,但通过这几类极具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勾勒出了当时工厂生活的总体图景,较为深入地描绘了各个群体的心境与处境(相对来说,里面的工人形象比较模糊)。小说中乔厂长所面对的各种问题,诸如怎样处理人情与科学管理的关系、怎样面对冀申这样的官场“老油条”、怎样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关系,等等,都是改革过程中面临的真问题。透过这些真问题,蒋子龙最想写出的是“人和经济社会的关系”,最想走进的是现代化生产条件下人的精神世界。正如蒋子龙所说:“创作的根须在生活里扎得越深,就越能细致感受时代动荡给人民带来了哪些社会的、伦理的、道德的、心灵的、外在的变化。” 《乔厂长上任记》既是立场鲜明的、刚强有力的,同时也是复杂的、纠缠的、暗流奔涌的。小说结尾处,乔厂长的成就感、孤独感、迷茫感交织在一起,未来的改革将走向何处,他的心里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蒋子龙的文学终于成为了真正的“入世”文学,它没有刻意渲染出一个成功学意义上的“神话”,而是“克尽本分”地做生活的观察者。同时他又借由文学的超越性,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思考与总结。
总之,蒋子龙的作品之所以会一次次地搅动风波,恰恰是因为它们刺激到了现实的痛处,触碰到某些人的现实利益,并深度投入到对于现实进路的择取中。今天翻开这些作品,争议的声音早已远去,但其中对于时代和人的真切描摹,依然与我们当下身处的这个现代化、科技化、整个社会都越来越工厂化的世界密切相关,一脉相承。“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借由文学的世界回顾“所来径”,最为困难同时也最为关键的便是透过文字所叙述的表象,抵达背后的“真意”。
改革故事的B面
蒋子龙最为人熟悉的工业题材作品,大多是以工厂领导作为主人公。许多改革文学作品,也都是以领导的视角展开故事的。这非常好理解,在转型关头,当然特别需要有魄力、有创新精神的带头人出现。现代大工厂的领导人物,是“组织生产”的枢纽,许多复杂的矛盾往往体现在他们身上。因此,从写作的角度来看,写好领导人物,往往可以“提契全盘”,正如我们上文分析的《乔厂长上任记》那样。蒋子龙工业题材作品的突出贡献也在于,他十分自觉地描绘了一批具有开拓精神的领导干部形象,努力回应现代化对作家提出的挑战,竭尽全力地去描绘现代大工业的组织方式及其孕育的新人、新道德、新观念与新美学。虽然他并没有做得尽善尽美,但有了这样的创作自觉,使得他的工业题材作品在同时代同类型的创作中拔得头筹。
如果说领导者视角构成了我们最为熟悉的改革故事,那么改革故事还有它的另一面,亦即普通劳动者视角中的改革故事。普通劳动者在社会转型期的命运,同样是改革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时代,劳动者当家作主被视为国之根本。那么在转型年代,劳动者的命运将何去何从?他们还有机会参与重大决策,还有自我管理的空间吗?他们的个人命运、情感历程又将发生哪些变化呢?那些曾经有效的经验与传统又将被怎样处理呢?不夸张地说,没有故事的另一面,改革故事将是极其模糊的。因为领导者只有在与普通劳动者的互动中,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工作模式。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与《乔厂长上任记》几乎同一时间,蒋子龙还发表了另外一篇短篇小说《晚年》(《新港》1979年第8期)。当然,《晚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远远不及《乔厂长上任记》。如果说《乔厂长上任记》讲的是“老厂长的出山”,那么《晚年》讲的就是“老工人的退休”。一进一退,映照成趣。具体来说,《晚年》讲述了毛泽东时代的优秀工人张玉田晚年不被青年工人和车间领导理解,直至被迫退休的故事。张玉田对于手艺的精益求精,对于工作近乎苛求的认真负责,对于工厂唇齿相依的深厚感情,在转型时代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他的儿子为了继承父亲的工作,甚至不惜以“堕落”相要挟。张玉田的离厂,已成定局。他的退休,更是一代人退场的隐喻。退休之后,他生了一个月的病。小说里写道:
张玉田得的是什么病呢?医生说是气血亏,要静养,多吃补药。老人自己心里可明白,他不是气血亏,而是精神亏,思想空了。希望是人的精神支柱,没有希望了还怎么活下去?对于他既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只有属于老年的过去。这些天,他躺在床上就靠回忆自己过去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来安慰自己。但这种安慰连五分钟也维持不了,又变成了深深的自责:“我为什么五年不写申请,为什么五八年不写申请?要是那时候写申请不是早批下来了。我总说时间还有的是,离死还远着呐。现在可好,稀里糊涂退休了,退休离死只差一步了。我和共产党生死与共,摽着膀子干了三十多年,最后还得挂个白牌牌去见毛主席、周总理……”
工厂不仅是张玉田的工作场所,也是他付出过青春与热血的地方。三十年兢兢业业的工作,让他收获了尊严、价值和精神支柱。当他得知曾经的徒弟、如今的车间书记田福喜以为他迟迟不肯退休,是担心退休工资比上班工资低时,张玉田感到受了侮辱,觉得自己被小看了。他退休后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入党。他不明白自己没能入党是因为田福喜忌惮他的资历,担心自己在仕途升迁中遇到对手,而是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距离党员的标准还很远。张玉田后来因为偶然遇见工厂党委张书记,并受到张书记的褒扬,田福喜才忙不迭地批转他入党。当田福喜盘算着如何防止张书记和张玉田的关系进一步亲密时,张玉田却在入党的当晚彻夜难眠:
这一晚上,张玉田失眠了,但这不是由于愁苦和憋闷;而是一幕一幕地回顾过去,他严肃认真地检查了自己的一生。
第二天早晨起来,老伴发现他的枕头湿了一片。
时代不同了。田福喜作为工厂的基层领导,所有的工作只对上级负责,并且只知道苦心经营个人前途;张玉田作为他的师傅却自始至终地爱党、爱厂,不断地自我批评与反思,以期达到党所要求的个人状态。前者为“私”,后者为“公”;前者心中只有“事”,后者眼中总关“情”。但后者却成了“落伍者”和“老古董”,被十分轻易地贬低、否定乃至抛弃了。总之,张玉田式工作状态、精神状态与生命状态的消逝,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当新旧时代更迭时,前一时代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是需要仔细辨析、认真守护的。当文学史牢牢地记住《乔厂长上任记》的时候,也应当为《晚年》这样的作品留下一席之地。因为它记录了普通劳动者,甚至是那些“落伍”的劳动者的宝贵品质,他们的宝贵品质本应是推进改革的积极力量。
这就是文学的价值所在。它不是抽象地论证改革的光辉与正确,而是打开了更为丰富的面向,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关注不同阶层的群体,从表象深入精神,从事件沉到心灵。论说至此,我们也就有可能理解蒋子龙对于“改革文学”扛旗者的美誉,为何总是颇多推辞。他总是强调,他在写作的时候,绝对没有“改革”这样的框子引导他。而且城市工业改革全面推行的时候,他有意地将写作对象从工厂转移到了其他领域,停止了工业题材的创作,从曾经带给他名气和荣耀的创作领地急流勇退。在他看来,“写改革”是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是极为复杂全面的事业,无法预测和把握。他只是凭借着对生活的积累和观察,依靠创作上的直觉写下了日后被命名为“改革文学”的作品。他被正式调入天津市作协工作后,不再与心爱的工厂“日夜厮守”,工业题材的创作也就自然而然地终止了。幸耶?悲耶?
如今,已经年过70的蒋子龙早已过了创作的巅峰时期。他认为自己的创作历程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从1979年到1983年是第一阶段。这期间以工业题材为主,情感基调是忧、思、愤,自觉地用文学承担起现实的责任。他把真诚视为创作的生命,并总结道:“尽管这真诚有点沉重,有时锋芒直露,对前途倒并未丧失信心,甚至对有些人物还投以理想的光焰。就这样,形成了这一阶段我的创作基调,或者说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风格了,并有意强化这一风格,追求沉凝、厚重。跟文学较劲,努力想驾驭文学。” 第二阶段是1984年至1989年,他逐渐感到自己不应当被工业题材局限,决心冲破工业题材的束缚,情感基调变得深沉、冷静,开始走向更广阔的现实生活。1990年以后,他更是随心所欲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不再想着驾驭文学,而是“舒展自如地被文学驾驭”。虽然此时的他早已不再是那个烜赫一时的话题人物,但他反倒认为自己的文学在最自由的时刻,才真正走向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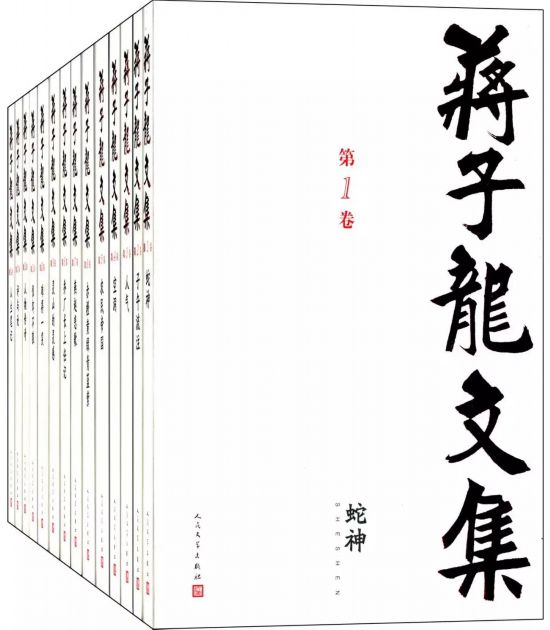
《蒋子龙文集》十四卷本
2013年,《蒋子龙文集》十四卷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位曾经挺立在改革潮头的“工人作家”,既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收获了自己更为完整的文学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