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2018年第6期|何平vs糖匪:好故事可以抵御恶
何平(文学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小说的题目按你说的改成《无定西行记》了。无论是原来的题目,还是现在的题目都有一个“西”,在你自己小说的预期中“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指?还是因为先有了彼得堡,所以确定了“西”的方位?
糖匪(作家):日出东升,日落西降。从东到西的空间变化,不自觉就带上了以微小生命为基本单位的时间刻度。这是一个讲几代人在逆熵世界里做无用功的故事。我想不出西之外更好的方位。实际上也没怎么想。彼得堡的地名是在确定方向后才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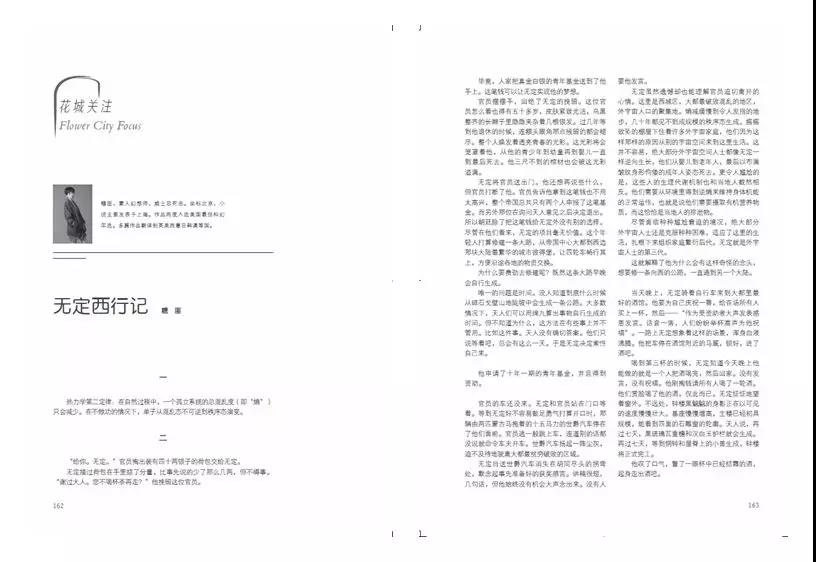
何平:还和“西”相关,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你是怎么想象“西”的?我不知道你小说的“西”和一些我们熟悉的文化原型是否有关系,比如“西天”,比如“西域”,比如近现代以来的“西方”?也许我是过度阐释,你只是灵光一闪,然后就有了“西行”的“西”了。
糖匪:灵光一闪,也是因为一直浸淫在关于西方的想象里才会有的吧。西方,一直是作为异世界存在在东方文明的想象里。作为佛教文化的起源地,或者欧洲文明世界,当然还有亡者国度。无定他们去的是欧洲文明世界,不过这个故事里的逆熵设定,东方世界反而更现代。还有无定他们不是前往西方世界“取得”什么。他们的目的明确,只是经过,然后返回。修建大路是否成功最后也是折返到他们自身。“西”的地理意义消解了,同时和其他故事不同,它也不是作为某个精神象征激励行者前行。“西”只是一个中点,一个驿站。西行才是故事的终点。
何平:但是从地理空间和自然风景上看,无定经行处确实是我们说“西”所能联想到的,比如森林、戈壁、沙漠,等等。
糖匪:实际上,这条从大都到彼得堡的路线不完全是想象产物,包括故事里其他的一些地质特征也有依据。可以称为一种玩世不恭的考据癖吧。写故事前我会花点时间查相关资料,一部分弃之不用,用的那些会被打得很细碎,吃进去消化了再吐出来,放到故事里。
何平:当下小说不同类型的作者他们各自被关注范围好像有一个无形的边界,比如你,一般而言是被视作一个科幻小说家,你写星际旅行、人工智能、虫洞,包括这篇小说好像有一个科幻的外壳,比如熵和逆熵形成的外宇宙空间人士和当地人的不同代谢机制以及生命方向,但我觉得你的小说不一定要当科幻小说来读,或者说你的想象并不完全依靠“科幻”之“科”,而是你自身的源发的想象力,是一种已有文学类型暂时很难规定的幻想文学,至于你这种幻想文学向哪个方向走,我现在很难做一个肯定的判断。
糖匪:在你我的这个宇宙里,按热力学第二定律,随时间,孤立系统熵不会减少。这个问题关系着时间的流向,到生命的生理代谢,宇宙的起源,也关系着你的热咖啡为什么会变冷这样的小问题。而我设想的平行宇宙里,熵正好相反。What if,是写科幻小说的重要乐趣之一。重新创造了一个世界,从动力学到生理代谢到时间还有投掷骰子的概率,都相应改变。最重要的,是人和社会在这样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动机、生存方式所发生的改变。到了这一条,读者不需要了解热力学定律,不需要get到之前的趣味与恶趣味,他是可以直接理解的。“在一个什么都自动完成的世界里无定是个笨蛋。”就这样可以了。这样,他就可以和无定一起上路西行。
对小说分类,不是作者的工作。分类有利于传播营销推广,现代文明社会里需要将信息扁平化便于最大限度地传播扩散,也可以帮助有类型期待的读者更快找到他们想要的内容。我非常理解它的作用。但这不是我的工作,所以,就这样吧。
何平:你曾经和我说过:“有时候觉得当代文学正变得越来越有形式感,在这种形式感里丧失掉最原初的那点生命力。”我觉得科幻文学现在就面临着你说的这种危机。
糖匪:这几年我看科幻小说比较少了。坦白说,我十多年前就对大事记、传奇类的科幻故事失去了兴趣。这样的故事,比起文字,有更适合的媒介。比如电影,动漫,甚至游戏。像菲利普·迪克、巴拉德、克拉克、西弗尔伯格,包括特德姜这样的科幻作家,他们小说核心、独特的意趣和世界观,都是无法影视化再现的。只有文字可以。不排除好的导演影视他们的作品,但这就是另一部作品了。至于文学形式化,很大原因是因为感受力的丧失。姿态变得重要起来。
何平:《无定西行记》开头言之凿凿地说:“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念头,想要修一条向西的公路,一直通到另一个大陆。”但到了小说的最后,当无定三代和彼得罗三代快抵达他们祖辈的出发之地,你却又说:“为什么一定要造一条路,既然它迟早会出现。”小说叙述的过程成为洞悉生命虚无的过程,所以,你说这篇小说写的是“丧”,“就是想写一个很丧的故事,不仅仅是无能为力,更是,无所作为”。
糖匪:无定一代其实也知道的。在这个逆熵世界里,他们是唯一熵增分子,增加世界的混乱度。到底是自己先造起大路,还是让大路先自行生成?无定没法确认这个。但是他还是在出发前拟了成功回来后的演讲稿。这份演讲稿传了三代。每一代都对此念念不忘。虽然是自己创造出的人物,但还是忍不住觉得他们挺可爱。
何平:如果文学批评的误读和过度阐释有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那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无论是西天取经,还是通西域,以及向西方学习,“西”作为一个想象的异邦是瑰丽的、神奇的,也是一种激活的力量,但“无定西行记”经过三代努力最后却是“丧”。
糖匪:想了很久,最后决定用三代来丧。尤其是到了第三代,没有太考虑失败的可能,由他来直面这样的现实,像个残酷的玩笑。不过想象一下那个逆熵世界,组成物质世界的每一粒原子都在变得越来越有秩序,人类什么也不用做。这种时候,用三代人的生命去无用功了一下。这种丧是不是也挺瑰丽的。
何平:去年有一个时候“丧”文化被广泛地讨论,“丧”也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口头禅。在我看,“丧”其实可以是一个内涵特别丰富的词,读你的小说集《看见鲸鱼座的人》,我总感觉到你是从各个方向给“丧”赋义,你小说的孤独感、虚无感、荒寒感无处不在地弥漫着“丧”。
糖匪:你是第一个这么说我的人,有一种一下子被人喊出真名的感觉。虽然明了,却不沾染;虽然恐惧,仍旧前进——我的丧大概就是如此,战战兢兢前行在一条没太可能的路上,偶尔停下来赤脚吃个瓜。全球在变暖,世界在崩坏,可是眼前的瓜还是甜的,太阳还是暖的,要笑啊。
何平:你应该是特别迷恋讲故事的人,讲童话一般清澈干净的故事,甚至你的几个小说都用“讲故事”做了小说叙事的核心,比如《黄色故事》《蒲蒲》,比如长篇小说《无名盛宴》一开始的《马戏团》。
糖匪:好故事可以抵御恶。一个世界,如果只需要中心思想或者只向往高潮,不仅可悲,而且危险。人类最早的艺术形式,无论绘画还是音乐,还有口耳相传的故事,其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小宇宙。到了文字出现的时代,诗歌和故事都是在传达一种无法言明又必须言说的内容。在我心目中,诗歌更高洁纯粹,有些难以够及。我喜欢现在这样灰扑扑地坐在路边讲故事的样子。

糖匪,素人幻想师,威士忌死忠。坐标北京,小说主要发表于上海。作品两度入选美国最佳科幻年选。多篇作品翻译到英美西意日韩澳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