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金庸作品浮想札记三则
金庸的两种读法
原来整整三十年前,香港女作家黄碧云谈过金庸作品。咳,应该说是骂,不是谈。
她论《书剑恩仇录》,说“陈家洛悲壮的‘牺牲’儿女情亦是庸俗的‘男儿’、‘英雄’感性。也因为这段恋情的陈腔滥调,加上才子的文章,恋情使大众很安心,成为佳话。因为现实从来没有这样简单”。她又说,“《书剑》亦暴露了作者/读者的‘大汉’心态,整体故事的前提是‘反清复明’,‘汉’是‘忠’的,而‘满’是奸的。这种忠奸分明的种族观,不过是幼稚狂热的狭隘爱国主义”。她再说,“《书剑》亦是封建伦理观的拥护者,君臣之义,父母之恩,手足之情,全然受到推崇……我无法明白小说人物及观众竟可以接受这样的人生秩序……金庸小说鼓吹的封建意识,重视传统对个人的压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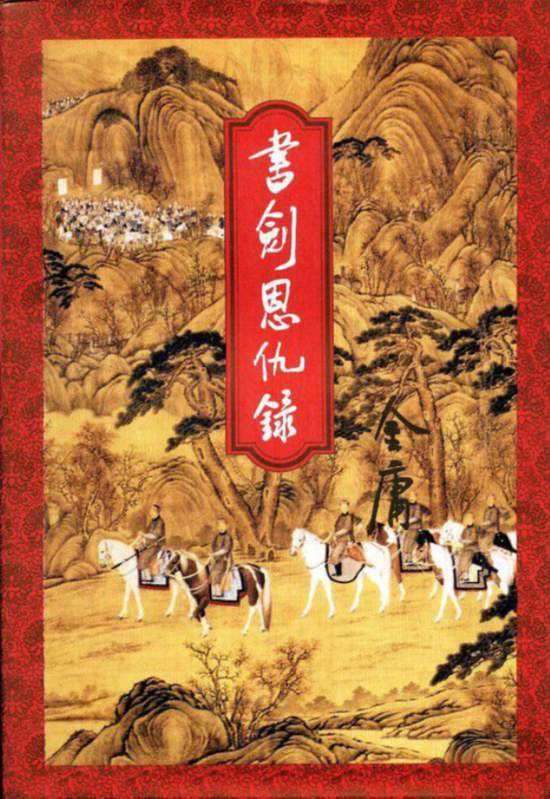
《书剑恩仇录》书封
她说这点,说那点,黄碧云是如此的不悦与不爽。
我不知道黄碧云其后有无改变想法,只记得当时阅后打从心底冒起连串问号:真的吗?真的如此简单便可打动一代又一代的华文读者?《书剑》的故事,以至金庸作品的其他故事,真的可用如此忠奸分明的逻辑分析到底、一棒打尽?当金庸写满汉和君臣和父母和手足和男女,真的想说的就是这些?而就算作者本来想说这些,读到读者眼里,真的只会跟随作者之愿而拍掌叫好?抑或,读者另有“阅读快感”之源,并正跟黄碧云眼中所见的彻底颠倒?
至少我是这样的。
在我的遥远经验里,读金庸,最有趣味在于他用丰富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加上用中文写中文(而非唐兀的欧化语句),把我带进各式各样的“两难困局”里面对严峻的抉择。满汉也好,君臣也罢,父母手足男女亦是,“和谐”从来不易,常有冲突,以大传统、大道统、大道德之名,把个人迫进取舍的死角,而真正在角落的围困里,个人必须在万分焦虑与挣扎的状态下质问自己:你要怎样选?你到底敢不敢选?而无论怎样选,你敢说自己选得对?
由这角度看,“我的金庸”呈现的,非如黄碧云所说的“幼稚”和“狭隘”,而刚相反,他是透过主角的焦虑和挣扎而对大传统、大道统、大道德多有反讽。
“两难困局”是真实的,却又是虚假的。在历史情景下,困局处处,人间不易,但当书中人在作抉择之际或之后,往往领悟困局之为困局只不过因为你接受它、认同它,若能登高望远甚至远离江湖,困局即与你无涉无干。
金庸故事之撼动华人,这或是本旨。
金庸自己的说法
黄碧云卅年前撰文谈《书剑恩仇录》,指故事说的无非是“忠孝节义”的大纲领,“所有人物只以此独一无二的标准来衡量善恶,孝者义者忠,忤者逆者奸,鼓吹的是‘封建意识’并‘重视传统对个人的压迫’”。
或许是吧。但又不见得全然是。毕竟《书剑》以至其他金庸作品皆以历史为叙事背景,封建时代的封建意识,在那背景下几乎已是必然,但说作者用意或作品效果在于“鼓吹”或“重视”,倒易低估了作者的复杂心意和读者的主动认知。
作者想写的是什么?

金庸 资料图
金庸自己说过了:“我希望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和平友好,互相帮忙,重视正义和是非,反对损人利己,注重信义,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轻视争权夺利、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
如此复杂的价值观,显然不是“忠孝节义”所可网罗,即使勉强笼统地归纳到这四个字的大招牌下,其中亦有不少裂缝和褶皱,甚至常有冲突和矛盾,而亦正是冲突和矛盾驱动了情节张力,并引发阅读过程里的快感和愉悦,把读者迫到某个处境,不断叩问自己,何时应该顺从,又何时应该违拗。甚至某些金庸作品,会在“忠孝节义”的脉络下,用或明或暗的方式反讽、反思忠孝节义的存在合理性和荒谬性,暴露了忠孝节义的处处裂缝,以及其他的可能出路。

《鹿鼎记》剧照
金庸作品人物丰富,有铁杆愚忠者,有被迫忠诚者,有不屑逃离者,有私心伪装者,有飘然远引者,似难被忠孝节义的大帽子一网打尽。压轴的《鹿鼎记》是最佳范例,青楼之子韦小宝,以及他的江湖朋友,以及他的朝廷联盟,以至皇帝大人,各占其位以谋其私,忠孝节义并非不重要,但往往只是用来谋私的论述工具,生存固然不易,谋私却亦要讲策略,忠孝节义至此如同只供玩弄的“游戏语言”,忠者忤者皆没有认真对待。但金庸倒未停笔于策略层面,否则便变成商战或谍战戏了,他反而写出了在各式策略下面的挣扎和抉择,一味效忠的小说闷死人,一味反抗的小说亦甚幼稚,真正动人的是在忠与忤之间的摇摆和怀疑,以及此间的情和爱和义和报和仇。“舍身取义”、“鱼与熊掌”、“忠孝难全”……向来是困扰华人的传统价值两难困局,金庸作品用这困局精采呈现,打动了几代华人读者,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当然,尚有在这一切之上的天意和宿命,人在其下,常有万般无奈。所以金庸作品于曲折之馀另有一股淡淡的悲剧感,不过常受论者忽略罢了。

1959年5月20日,《明报》创刊号封面。
金庸和他的同代人
传来金庸先生病逝消息的刹那,脑海首先浮现的脸容是匡叔。同代人,重量级,殿堂经典,世代传奇,在生命大限以前像排队一样轮次风流云散,虽说早有长久的心理准备,排到队伍后头的人难免仍感落寞。并且愈来愈落寞。走了一个,又走了一个,江湖急寥落,弦声渐息,散席的瞬间是最苍凉的瞬间,总得重新调整适应。
未几在网上见到访谈,倪叔说:“剩下我一个了,哈哈哈!” 笑声依旧爽朗,但我猜,里面未尝没有悲怆。
之后我又想起胡菊人先生。远在加拿大,闻说健康状况时有起伏,不知道现下可好?他比金庸年轻九岁,曾经主理《明报月刊》,是查先生的左右手,1981年转到《中报》担任总编辑,金庸跟他长谈挽留,却亦明白他的大志,给他忠告,新老板绝非可靠之人,万事提防,若有差池,大可回归原地。胡菊人离职前,金庸在酒楼替他饯行,赠其劳力士金表,识英雄重英雄,是文艺江湖的一幕动人景象。
《中报》果然短命到无人相信,胡菊人干脆自立门户,与陆铿合办《百姓》半月刊,闻说胡老总曾为此借酒消愁,一夜之间头发尽白。《中报》成立时亦有《中报月刊》,为了对抗《明报》和《明报月刊》的舆论阵地而来,胡菊人在政治旋涡里欲做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折翼败走。转眼三四十年,昔之老板与老友离开了,自己亦饱受疾病之苦,异国寒冬,回首前尘,唯望胡老总别因情绪挫败而端起早已放下的酒杯。
之后我再想起梁小中先生。五年前逝世于温哥华,笔名“石人”,四十年代已在中国大陆做编辑,其后来港,又编又写,更曾办报,但三回皆失败告终。文青时代的我,曾经有缘在饭桌旁听梁先生说故事,他曾在金庸手下工作,报馆风云,小道八卦,他所勾勒的老板侧影让我听得津津入味。我还记得那顿午饭临近结束,梁先生执起毛巾抹一下嘴角,提醒我道:“世侄,我用一支笔写文章养活了一家大小,几个仔女,供书教学,看起来风光,其实写得几乎眼盲。如果有其他出路,你最好别做写稿佬了。多读点书,稿纸以外的世界大得很。”
多年后我弄了个blog,取名“稿纸以外”,根源于此。
那年头啊,真像一个文字的蛮荒世界。勇者前来闯荡,风正萧萧,一支笔是一把剑,虎啸龙吟,各有招式各有位置。江湖已老,汉子凋零,唯有文字长存,终究代表著笔墨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