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诗集《预言》出版小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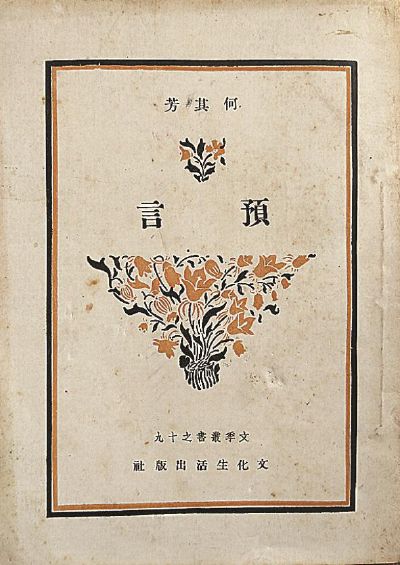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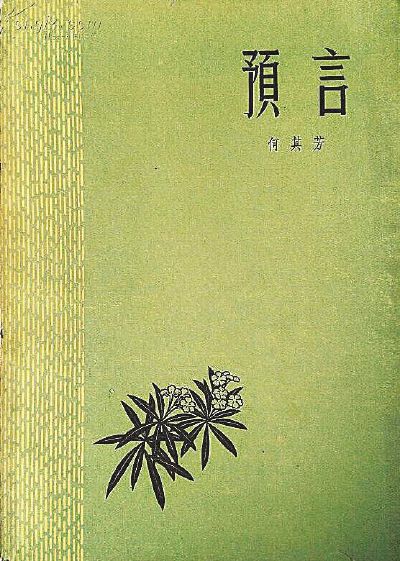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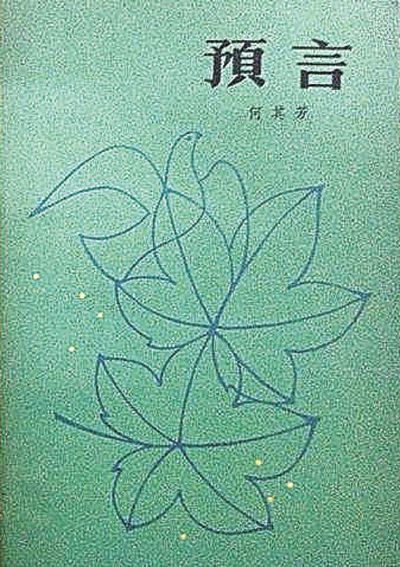
青年时期的何其芳及其诗集《预言》初版本、1957年与1982年版书影。
何其芳1931年开始发表诗作,早期诗作先后编入《汉园集》(1936)、《刻意集》(1938)。《汉园集》是他与卞之琳、李广田三人的诗合集,其中何其芳的《燕泥集》收诗作16首。《刻意集》是诗与散文合集,收入“不曾收进《汉园集》的诗”18首。
何其芳第一本诗集《预言》是自选集,收入《燕泥集》《刻意集》中的大部分诗作。其中,《燕泥集》的诗删 1首留15首,《刻意集》的诗删4首留14首,再加上写于1936至1937年的5首,共34首。全书分三卷,1945年2月作为“文季丛书之十九”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编选始于1939年
何其芳1956年在《写诗的经过》一文中说:“我的第一个诗集《预言》是这样编成的:那时原稿都不在手边,全部是凭记忆把它们默写了出来。凡是不能全篇默写出来的诗都没有收入。”“那时”指在冀中的时候。
沙汀后来回忆说:初到冀中时,“为了排遣,一有空他(何其芳)就埋头抄写他抗战前所作的诗歌。字迹又小又极工整。这个手抄本我曾经一一拜读,尽管它们的内容同当时的环境很不相称,但我多么欣赏其中那篇《风沙日》啊”(《〈何其芳选集〉题记》)。这个“手抄本”就是那时开始编选的《预言》。
1940年 12月,诗文集《刻意集》第二版已出版一年,身在延安鲁艺的何其芳 “一直”“没有见到这本书”,但他“想起了它”。为“使这本书显得单纯一些,调和一些”,他决定对《刻意集》作些改编。18日,他在延安鲁艺作的 《刻意集》“三版序”中说:“感谢出版人和这种丛刊的编者,他们允许我有一个改编的机会!……我要把那些诗和那两篇关于诗的文章从这本书里抽了出来,它们(除了一些我要根本删掉的不好的诗)将出现于我的第一个诗集 《预言》里面。”文中所说“那些诗”是“卷四”的 18首诗,何其芳删去 4首“不好的诗”,其余14首编入《预言》。这样,仅《刻意集》初版本和再版本收入诗作,后面的版本均未收。
何其芳改定《刻意集》,诗集《预言》已差不多编成,这与他在第二个诗集《夜歌》(诗文社1945年版)的“后记”中所说相符:“我的第一个诗集即工作社预告的《预言》。那是1931年到 1937年写的……把那些古老的东西编成一个集子已经是四年以前的事了,那时的动机也不过一是为了自己保存陈迹,二是为了爱好我的作品者了解我的思想发展,总之没有什么更充分的理由。”“后记”作于1944年10月11日,还提及《预言》最初是在工作社出版的。
“工作社版”并未“出世”
“工作社”,是何其芳妹夫方敬1942年秋冬在桂林创办的小型出版社。取名“工作社”,缘于何其芳、卞之琳、方敬等 1938年 3月在成都创办的《工作》半月刊。
工作社“开张”后出的第一本书是何其芳的散文集 《还乡记》。该书1939年由良友公司出版时,因 “出版者在战乱中失去了一部分原稿,并且将书名误印作《还乡日记》”,工作社于 1943年2月出版了再版本,书名改为《还乡记》。在该书预告的“工作社新书”中,就有何其芳的《预言》。
诗集《预言》是方敬准备为何其芳出版的第二本书。他回忆说:“1944年夏天这本书已排好打成纸型,准备付印。但战局骤紧,日寇长驱直入,桂林沦陷前,我们仓卒疏散,这本诗集当然也就不能出世了。”(《关于〈预言〉》)何其芳在《夜歌》“后记”中也说到这件事:“后来工作社打算印,而且不久以前已经在桂林付排了,打好了纸型。但是,战时的变化是很多的,现在当然无法出世了。这也没有什么,于人于己都不是值得惋惜的事。”
由于工作社预告过《预言》的出版,所以有些文献误认为《预言》是由桂林工作社正式出版的。比如,《桂林文史资料》(第四十七辑)介绍“方敬”时,说工作社出版的“工作文学丛书”中有“《预言》(诗集,何其芳著,1942年出版)”;《桂林抗战文艺辞典》明确为“1944年桂林工作社出版”;《桂林抗战文学史》中,《预言》的注为“1944年桂林工作社”,并说“这部诗集……在桂林诗坛上也还是引人瞩目的”。其实,是“无中生有”。
曾改书名为《云》
工作社预告时,书名取自诗集中第一首诗的篇名《预言》。但在工作社 “无法出世了”的情况下,何其芳对书名另有想法。他在《夜歌》“后记”中说:“将来若万一又有机会印出来,我想给它另外取个名字,叫做《云》。因为那些诗差不多都是飘在空中的东西,也因为《云》是那里面的最后一篇。”事实上,何其芳确曾把书名改为《云》,因为他请老友卞之琳为《云》写过一篇序。序文说:
这 《云》是其芳的第一个诗集,他的第一部分称集的诗作,原是《燕泥集》,可是《燕泥集》并未出刊单行本,而只是由我编入《汉园集》一度行世。
现在那本小书也就成了陈迹了,陈迹里却分别借了一点根或者芽分别长了新草木——其中之一就是其芳的这本《云》。
而《云》本身也就只是一个芽了,若同时提起其芳未来的发展,这些诗也的确“预言”了一些未来的东西,与其说是思想上勿宁说是艺术上的成就。现在其芳已经怕人家以为还是这样子写诗,而愿意人家知道他已经有了第二个诗集《夜歌》那样的诗,可是《云》也有其本身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之所以能成《云》者也就在于这里见出的认真的精神和严肃的态度,即便表面上有时候带点颓废式玩世色彩的一往情深,并然炫目或怵目而是醒目或摄目的丰富的想象,叫字句随意象一齐像浮雕似的突起来的本领……
作者自己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对前一期的作品有所不满意是当然的,正如其芳现在就已经开始不太满意《夜歌》了,不过是作者在某一时期内的满意不满意判断而已,从另一点说,正因为作者一定不会再写这样的东西了,倒更是弥觉可珍,因为它们还是艺术品,这种奇怪的东西。
显然,何其芳告诉卞之琳,他的第一本诗集叫《云》,第二本诗集也已编好,叫《夜歌》。“其芳的第一个诗集却没有叫《云》,这篇序当然也就没有用上。”方敬解释说。不过,“这篇序也还是可以当作《预言》的序看,虽然书名不同,虽然没有印在诗集上。”那么,是谁把《云》改回《预言》呢?
1944年4月,何其芳奉命第一次来到重庆,1945年1月回延安。笔者推测,1944年桂林沦陷,《预言》无法“出世”,何其芳就把书稿交给也在重庆的巴金。也许是巴金建议他把书名改回的,他自己非常珍爱《预言》,也就同意了。《预言》于1945年2月出版,在时间上是相合的。不过,初印本出现一个小 “差错”:目录编有“序”,书中却未见序文。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交给巴金的书稿,书名是《云》,目录编有“序”。由于改了书名,抽去了为《云》而作的卞序,却未将目录中的“序”字删去。后来的再版本、三版本,目录就不再见“序”字了。而卞之琳的“序文”,1945年方敬在贵阳主编 《大刚报》文艺副刊《阵地》时,曾发表在副刊上,因而留存了下来。
关于版本
关于《预言》的版本,孙玉石在《论何其芳三十年代的诗》一文中说:“《预言》很快于第二年得以再版。不久,何其芳在给巴金的一封信中,还商量能否‘重印’,以‘留作一点纪念’。这个愿望后来实现了。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第三版。何其芳逝世后,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了第四版。”文中说到《预言》的几个版本,但有误记。
《预言》初版于 1945年 2月,再版于1946年11月,第三版是1949年1月,均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因此,“孙文”所说的1957年版应为第四版。
“孙文”说到给巴金的信,写于1952年1月9日,现录于下:
有一点小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有时还有人向我要 《预言》看。因此,我最近抽空把它改编了一下,主要是删去了那些有悲观色彩的东西。我一共删去了十四首,还留下了二十首。按原来的版式计算,一共还有五十四面(不包括目录),这实在是一个很薄的小册子了。现在想和你商量一下,是否文化生活出版社或平明出版社愿意重印它?如愿意重印,请通知我,定当寄上。如果你觉得无重印必要,或者估计无销路,书店有顾虑,都望不客气地告诉我。重印这个小册子,实在近于翻古董了。改编的动机实在起于有人向我要,而现在书摊上找不到。另外,我抗战以前写的东西全部不足存,这二十首诗或者可以留作一点纪念,这也是一个促成我改编它的想法。
其实,早在1950年3月2日,何其芳给巴金写信就提到“再印”《预言》事:“《预言》似乎悲观消极的色彩还没有前两本(指《画梦录》和《刻意集》)书厉害,如还有人要看,我想倒是也可以再印的(当然,如果根本没有人买,也就算了)。再印时请通知我一声,我也校勘一下。”两年后再次致信巴金,说的仍是重印《预言》事,但这次何其芳不想只是简单的重印,而是认真作了“改编”:“删去了那些有悲观色彩的东西。”具体说来,“一共删去了十四首,还留下了二十首”。他的“想法”是,为了给自己,也是给他人“留作一点纪念”。但不知何故,这个改编本始终未见出版。不过,既已改编完成,可称之为“未刊版”,只是至今不知留下的是哪20首诗作,否则应是研究何其芳的一则重要史料。
1957年 9月,《预言》终由新文艺出版社重印,但不是“孙文”中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艺社重印的《预言》,前有简短的“内容提要”,说“这次重印,由作者删去一首,补入一首,仍为三十四首”。删去的是《墙》,补入的是《昔年》。其实篇名也有变化,《季候病》改为《秋天(一)》,原来的《秋天》也就改成了《秋天(二)》。1977年何其芳逝世,《预言》于 1982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次重印,注明原“新文艺版”。巧的是,这两个版的封面设计者都是装饰画大家章西厓,时间上却相隔了25年。1955年 5月,他“涉嫌”“胡风分子”莫名入狱一年余,“1957年版”封面是他刚出狱后所作;在“文革”中,他又被打成“坏分子”,“1982年版”封面则是他 1984年真正“平反”前的设计。
另外,有“名家名作原版库”版,还有与《画梦录》或与《夜歌》合编的。《何其芳选集》《中国新诗库·何其芳卷》收入了部分诗作,《何其芳全集》以新文艺版为底本,把删去的《墙》重新收入,共收35首。
何其芳因 《汉园集》被誉为“汉园三诗人”,因散文集 《画梦录》(1937)而获大公报文艺奖,诗集《预言》则是全面反映他抗战之前诗歌创作的范本。这些奔赴延安以前的作品,“什么也不为,只是为了抒写自己,抒写自己的幻想、感觉、情感”。1938年去了延安,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自己说:“在四二年春天以后,我就没有再写诗了。”因为“有许多比写诗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由此,一个被称为“何其芳现象”的文学史现象,至今仍被学界所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