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书写大学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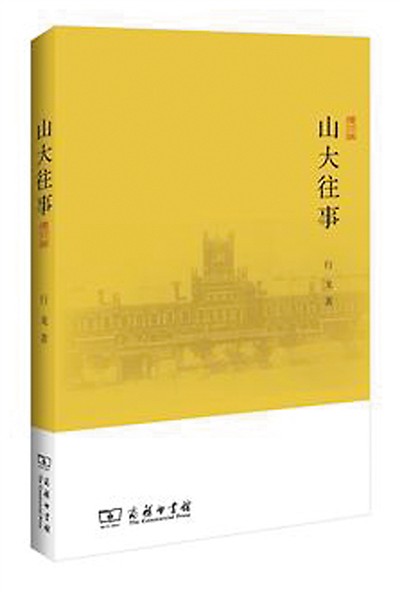
行龙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往事”是历史传承的一种特例,而“往事体”已构成文学书写的重要方式,校史写作更是当代文坛一种不曾被学理总结却硕果累累的往事书写领域。除却大量“简历”式校史修撰,校史写作的思想性、抒情性甚至“故事性”更加引人注目,如陈平原的《老北大的故事》、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孔庆东的《47楼207》,乃至今年丁帆的专栏《先生素描》。
《山大往事》(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一部钩沉山西大学百年历史风云的非虚构作品,作者行龙是一位历史学者。当此追昔缅怀视角盛行之际,又值古今抒情驳杂之时,行龙的书写确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关于往事写作的启示。按照柯林伍德的观点,历史书写是记忆的一种特例,那么,历史的变迁更渗透出了历史书写者的情怀和历史记录传统的赓续。
对母校的情感,是知识分子内心建构的一种基本情怀。以这所学校人的往事写学校,进而以学校屹立于山河。于是,人在此间确立了历史和现实的位置,获得一种通感的力量。《山大往事》最让人难忘的就在于一种山河的直呈,令人经常可以领略出结构中的凛然之气。
行龙善用插入历史文件的方式书写往事,恰到好处地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如《中西合璧、好事多磨》一节中插入《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李提摩太向李鸿章递交的此份章程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一个“罚”字尽显话语政治,而“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更充满了潜台词,把历史的诡谲和张力展现无遗。
山西大学百年牌坊两侧,树立着晚清山西巡抚岑春煊和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塑像,在师生眼中,这一中一西两位历史人物是山西大学的创始人。然而读罢《山大往事》,我们才知道如今笑容可掬共立于夏花冬雪中的两个人,当年却“貌合神离”。原来在李鸿章赞同开办学堂之后,岑春煊以民穷财尽为由对开办大学堂表示异议,后经李提摩太叠次催促,才派洋务局候补知县周之骧前往上海商谈。周之骧出语直击要害,办学耗银并不能称为“罚款”,而且西学与教会不能干预学校,李提摩太则坚持西人主持校务。经过一番拉锯谈判,开办山西大学堂的章程才初步拟定。然而在谈判一年之后,李提摩太又一次见识了山西人的“狡猾”——岑春煊早已将晋阳书院和令德书院合并为山西大学堂,李提摩太陷入到了长达两个月的“归并办理”交涉当中。行龙在山西大学创办的历史书写中“不虚美不隐恶”,充分打开了历史的张力。
“五四”运动前后,山大师生不但走上并州街头呼应,更于1920年创办《新共和》杂志,提倡“研究学术、宣传文化”,反对将大学办成“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思想开放”之风与北京大学不相上下。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山西大学暂时停办。《三原复课日:1939年12月23日》一节插入《阵中日报》报道和校长徐士瑚讲话,呈现了两年复校的周折历史过程,“学校在此八年的漂泊无定中”,“斗室讲学,颇有绛帐遗风”。1940年5月15日《阵中日报》对复课的报道并没有想象中的“激情洋溢、鼓舞人心”,而是一面历数办学经费困难,一面报道学生的苦学作风。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徐校长对三原复课也没有表功立意,而是总结发扬出“精研苦学”的奋斗精神。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这两个已被“过度阐释”的时段,行龙的直呈书写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地方性视域中的历史记忆给我们带来重新发现的感动;另一方面,从山西的视角反思历史,恰可为许多书写的“迷梦”祛魅。长期以来,历史知识的有效性已过多建立在感官的权威之上,就像马尔克斯所说,感官记忆总是会逐渐剩余美化了的沉淀,而真正的史学是努力寻找一切可能隐藏有自己答案的东西。
1947年11月29日,国立山西大学教授会召开全体教授大会,这次“教授治校”的成果却是“一致决议集体请假一周”。在风雨如晦、天地玄黄之机,行龙以“名垂校史”作了总结,因为教授们虽然集体请假,却并没有疏于辅导学生功课,而仅为了以鲜明的态度融入“反饥饿”运动。我们注意到,行龙所叙述的“人世”既没有泛英雄主义的情怀,也没有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尴尬。于平铺直叙之中,作者专注于历史情景的复原。“温和的斗争”非但总结了一次运动的特点,更涵盖了人世之于山河的力度。如果说,往事即使有实证和直呈,其组织也必然有着历史滤镜的效果。那么,我想行龙的这幅滤镜并非怀旧、光影恬淡的,而更接近于铅色颗粒、层次这些黑白摄影的效果。山西大学成立于1902年,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之一,而今却成为“最著名四非高校”,以历史的铅色透视如今立言、立名的挫败,恐怕就不能再盲目抱怨“春不到此间”了。
俆士瑚这位山西大学的老校长,在《山大往事》中的形象尤为鲜明。俆校长原任阎锡山英文秘书,但毅然“弃官从文”,在炮火中复校,战乱中呕心沥血,惨淡之中刻苦经营。1949年7月1日他乘坐专车赴京终于实现“将分散的山大完整交给人民”的心愿,之后主动选择功成身退,晚年更译著超过百万字。行龙的“人世”紧紧扣着历史中人的境遇,他笔下的“主人公品质”无疑经过了一颗泰然之心的涤荡。
《山大往事》通过一双“考证之眼”,文本达到的却是力学之美的平衡。这种平衡表现在“往事体”中的“人世”“山河”与“我在”三个方面的表达。除了“山河”与“人世”,往事体文章中至关重要的收束,我将其命名为“我在”。
在《山大往事》中,行龙时有直接的抒情。例如在写到山西大学堂译书院曾经的贡献,而今百年山大并没有一家出版社的时候,行龙直言:“笔端至此,能不令人浩叹!”书中所发议论也不在少数,例如“学生人数之少,师生比例如此相近,与当今之现状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了。”等。
“我在”如何穿行于“山河”与“人世”之间,这的确是往事体文章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想,在行龙的意识里潜在一种书写历史即书写诗的观念,但在古今对照之间,他又自觉形成了一番宏阔反思和细致借鉴。其实,《山大往事》中不时流露出一种诗意,而行龙所需继续生发的可能就是如何让“我在”行云流水又不着痕迹地照影于历史直呈之中。如何融史于情?为文又如何让抒情呈现成一种言说的模式?无论如何,一个平衡典雅的文本当是审美的愿景。
(作者为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