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VS杨辉|究天人之际:历史、自然和人 ——关于《山本》


杨 辉 先从题目谈起。在后记中,您开宗明义地写道:《山本》意为“山的本来”,是“写山的一本书”。这山就是秦岭。而“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关于它的故事,自然也可以被读解为中国故事,其中包含着的寓意,也自然指向中国。不知您是如何动念写作这样一本关于“山”的作品的?
贾平凹 有话说,生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血地”。我是商洛人,商洛在秦岭之中,写惯了商洛,扩而大之,必然要写到秦岭。六十岁后,生命和经历都有了一定的资本。你才可能认识秦岭,看待秦岭的表情自然与以前不一样。其实,秦岭也就是我眼中的人间烟火所在。
杨 辉 《山本》所写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秦岭的故事和传说。这些故事虽流传已久,但因无人整理,往往散逸在各处,不成系统。在写作之前,您作过材料上的准备吗?
贾平凹 不是为了写《山本》而去做材料准备,是获得了许多材料后才萌生了写《山本》的想法。那些材料来源于各种渠道,记录者和讲述者因角度不同,非常杂乱,但能感觉到它的价值和有趣,一下子刺激了我。犹如一块石头丢进水潭,水面上涟漪绽射,我才知道我心中早有涟漪。于是像怀孕一样,胎形慢慢生长。在胎形生长之期,我才有意识去做更多的材料的收集,比如各地方武装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各类枭雄的生与死,那时的风物习俗以及人的吃住衣行。等到《山本》的人事开始鲜活,我都相信这一切一切全是真实的事情,就开始把它摹写下来。
杨 辉 在后记中,您提到2015年开始构思《山本》时,面对这一时段的历史材料,一时不知以何种方式切入。“历史如何归于文学”,仍是您思考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在《老生》后记中您也曾提及。从《老生》到《山本》,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有何变化?
贾平凹 身在庐山难以识得庐山真面目,任何事情,回过头来,或跳出来,或往前朝后看,就不至于被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性的东西影响。历史也是这样。当一段历史摆在那里,如何变成小说?我指的是远期的历史,这可以看看《三国演义》、《水浒传》是怎样产生的。它是说书人说出来的,经过一代一代的说书人以自己的理解说出来,历史变成了一种故事在流播,最后再有人整编成册。其实我们写现实题材的小说,何尝不又是一种近期的历史?所以不必强调历史的远期与近期,那只是写作小说的材料,小说的完成就宣布那是历史了,这如同用布裁做衣服,我们说穿了件衣服,而不说穿了件布。
杨 辉 有论者认为,如果仅从“民间写史”或历史的新的叙述的角度理解《山本》,可能会形成对《山本》丰富意义的“窄化”。因为“民间”或者“野史”往往被放置在“正史”的对立面,但显然《山本》呈现的“历史”要更为复杂。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贾平凹 解读小说是有不同的角度,有的小说可能结构简单些,从一二个角度就能说清。或许《山本》要复杂些,“正史”、“野史”说到底还是历史,而小说,还是那句大家都知道的话,是民族的秘史。这个秘史,不是简单地从“野史”和“正史”对立的角度说,而是说它还包含着更复杂的生活的信息。比如人的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自然风物,以及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这些历史顾及不到的细节。它们可能呈现出历史更为复杂的状态。
杨 辉 《山本》故事的基础是1920-1930年代发生在秦岭及其周边的历史事件,但在写作中您并没有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观念中对历史进行处理。如您在后记中以破碎的瓷片比喻当时的总体性的历史状况,《山本》写的是一种“前历史”的状态,即在历史叙述未定之时的混乱、无序。因此,在《山本》中,一种混同的、非逻辑的故事从容展开。各种力量基于不同目的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你方唱罢我登场。这种状态,其实是对历史的“未定”状态的“还原”。即还原到历史发生最为原初的现场。在这里,历史可以生发出多种解释的可能。不知您在写作过程中,对此是如何考虑的?
贾平凹 正因为这样,我要模糊许多东西。我在后记中写道:“这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不是写战争的书。”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杨 辉 您在《山本》后记中谈到,在四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承接过“中国的古典”“苏俄的现实主义”“欧美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以及“建国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但“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凹,这个贾平凹就是贾平凹,不是李平凹或张平凹”。这种创作风格的转变,在《山本》中是如何表现的?
贾平凹 这是指这几十年来中国作家的承接问题,有的承接的是“苏俄现实主义”,有的承接的是“欧美的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有的承接的是“建国后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有的承接的是“中国的古典传统”,各种侧重点的承接,使几十年来中国的小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我主张承接要宽泛广大,尤其在当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作家写作,都是要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写作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都是竭力把“特殊性”变为“普遍性”,而遇到了更多的标准,从“普遍性”又回到“特殊性”,再竭力从“特殊性”变成“普遍性”,如此循环往复,方能大成。
杨 辉 陆菊人从纸坊沟带来的三分胭脂地引发了涡镇如此惊心动魄的世事,但“吉穴”却未如传说中的那样灵验。这样的处理,让人联想到《美穴地》。柳子言踏了一辈子吉穴,最后为自己精心堪舆的却是一处假穴。他的儿子后来并未做成大官,只能在戏台上扮演。在《山本》中,纸坊沟的这一处吉穴以及其之于井宗秀、井宗丞的意义一再被提及,但最终,兄弟二人均未成为最后的赢家。这样处理,不知有何深意?
贾平凹 小说里的任何情况处理,尤其结尾,多义性最好,由读者各自去理解。《山本》中的胭脂地吉穴,是一个由头,起着鼓动井宗秀和陆菊人的希望和雄心的作用,但世事无常,人生荒唐,才导致了最后人与镇的毁灭。
杨 辉 《山本》大量的笔墨,是在写历史事件发生之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他们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着四季转换而演绎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您在历史的宏大叙述之外,详细铺陈日常生活细节用意何在?
贾平凹 人生就是日子的堆集,所谓的大事件也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写日常生活就看人是怎么活着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人类之所以能延绵下来,就是因为有神,有爱。
杨 辉 在《山本》的结尾处,涡镇几乎被炮弹炸成废墟。“陆菊人说:这是有多少炮弹啊,全都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一堆尘土了?陈先生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陆菊人看着陈先生,陈先生的身后,屋院之后,城墙之后,远处的山峰峦叠嶂,一尽着黛青”。人事与自然,最终融为一体。这样的结局,似乎别有深意存焉?
贾平凹 在这个天地间,植物、动物与人是共生的。《山本》中每每在人事纠葛时,植物、动物就犹如一面镜子,呈现着影响,而有互相参照的意思。
杨 辉 《老生》以《山海经》为参照,超越就二十世纪论二十世纪的历史的狭窄视域,而有更为宽阔的历史参照。而以千年的历史兴废为总体性的视域,则关于二十世纪历史与人事变迁便有全然不同的理解。《山本》故事所涉,虽为1920-1930年代发生于秦岭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可避免地与该时段宏大的历史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但《山本》显然意图跳出既定的历史视域,而有更为宏阔的眼光,也试图表达一种独特的思考。
贾平凹 大地的伟大,在于它的藏污纳垢却万物更生,秦岭里那么多的战乱,灾害,杀戮,仇恨,秦岭却依然莽莽苍苍,山高水长,人应该怎样活着,社会应该怎样秩序着,这永远让人自省和浩叹。
杨 辉 在《老生》一个世纪的叙述中,四个故事指涉之时代虽不相同,但历史及世道人心根本性之运行逻辑并无变化。“眼看他起高楼,眼看它楼塌了”,此消彼长,此起彼伏,如是循环不已。《古炉》亦是如此,“春”、“夏”、“秋”、“冬”四时转换与人事转换互为表里。夜霸槽的“破坏”行为,与支书朱大柜年轻时并无二致。孙郁甚至发现,在夜霸槽和阿Q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征的当然是历史的延续性,或者历史的同义反复。而在《山本》中,井宗秀与不同时期身处不同阵营的阮天保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并不关涉到民族大义,而是个人利害恩怨的翻版。阮天保投诚之后,其行事与井宗丞似乎也并无二致。其他如逛山、五雷的各种势力,其运行逻辑似乎也并无不同。如是处理,不知有何深意?
贾平凹 天地间自有道存在, 不管千变万化,总有永远不变的东西。恋爱中找对象,其实找的是自己,别人的死亡,其实是自己的一部分死亡,孩子的任何毛病其实都是自己的毛病。光照过去,必然会折射过来,等等等等。古人讲,月落仍在,又讲,太阳下无新鲜事。我们曾经的这样的观念,那样的观念,时间一过,全会作废,事实仍在。历史是泥淖,其中翻腾的就是人性。
杨 辉 《老生》出版之后,您曾提及,面对历史,要写出“大荒”的境界。此种境界,颇近于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亦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所指陈之“超越了家国、民族、阶级甚至历史的界限,属于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大宇宙”,且“又超越功利、道德和人造的种种理念”的“宇宙境界”相伯仲。请问这种境界在《山本》中如何体现?
贾平凹 我只是有这种意识和向往,但我能力有限,我们或许能成为“飞天”,但我们在世上吃的东西太杂太多太笨了,飞不起来,这是我们和社会的可悲处。
杨 辉 如果不在“五四”以降的启蒙思想视域中看《山本》,而是从中国古典思想及审美方式论,便可以发觉《山本》所敞开的世界,包含古典思想意义上的“天”、“地”、“人”三个层次的。不仅如此,儒、道、释三家思想及其在混乱的世道中的表现也有涉及。比如陆菊人、井宗秀、井宗丞们,自然有类似儒家的精进一面;130庙和宽展师父则无疑体现着佛禅的意趣;陈先生所融汇各种民间智慧,但其核心仍属道家。它包含着各色人等及其所代表的各种文化,也便有更多复杂的意蕴。意义既然维度多端,也就有了多样的可解性。
贾平凹 这要看各人怎样理解。我觉得只要言之有理,都是可以的。照我的意思,你要观照这个地方,起码你要有一些特别的眼光和特别的理解。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就有着中华文化的东西隐含其中,有各种人文结构,有它流传已久的各种生活观念,来维系着社会的正常的运转。有破缺,自然也有自我修复。就精神层面而言,有宗教,也有种种民间信仰。有政治的线索,经济的线索和文化的线索。基本上将这几条线索把握住,就抓住了基本的东西。就总体而言,一个时代是由各种力量来制衡的。为什么我说《山本》不是在写某一个单一的方面,就是说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构成的总体上看,上一代人是如何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从什么样的状态过来的?是基于哪种土壤?哪种思维?哪种环境?从哪样的状态走过来的?小说写政治、经济、文化,但却不是搞一些概念化、宣言式的东西。比如说,你去读《红楼梦》。它到底给了你什么教益?这是比较复杂的东西。但咱们现在习惯在一本书里表达一种观念,也从这一种观念出发来解释它。追问这本书揭示了什么,批判了什么。为什么有人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好多人在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这种名著的时候,都是在吸收怎么活人的道理,而不是想解释目前社会上发生了什么问题。这种思路都是很局限,很短时间段的、很狭窄的视野。观念过一段时间就没有用了,但是发生的那一套事情还在。梁山上的那一套故事永远在流传,关于梁山的曾有的解释,却已经发生变化。读小说,有些人只是看热闹,有一些人却是在看一些生活的智慧。小说是小说,它和一般的用概念性的东西解释世界,还是存在着差别的。
杨 辉 从“五四”以来,小说在处理故事时,大多数已经习惯于将视野局限到人和社会,人和人的关系。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视野却并不如此狭窄。写作者们往往将历史人事放置到和自然同一的大的环境里,来考量种种关系。自1980年代初有心接续中国古典思想传统以来,您就在尝试敞开更为宽广的小说世界。如从这个角度理解,则《山本》的意义会因之丰富。
贾平凹 “五四”以来的很多作品都是写人和社会,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比如写之前的社会如何是吃人的社会,因此要民主,要自由。这些当然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只关注这些,就把小说局限到了一个狭窄的视域中。我估计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小说,都是把民间说书人,舞台上上演的英雄故事,把这些写下来。它并不一定有更多的别的含义,没有说要推翻朝廷,背叛朝廷的意思。它并不重视所谓的倾向。《红楼梦》我估计也是这样。曹雪芹就是把经过的事情写了出来,不一定给它赋予了多少意义。但我们后来在分析的时候,便要说这是反映了清王朝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实际上他只是写了曾经的繁华,追忆曾经的故事。原来最早是世情小说,从世情的角度写。后来还有《海上花列传》,也是作者看到《红楼梦》出来以后,感到还有这样的语言,于是用上海话来写的。王国维用中国的传统思维,还套用了西方的一些思想。当然,现在叔本华的观念还在流行。在他之前,没有人用那样的观念来看《红楼梦》。我以前看过《红楼梦》同时期的很多风情小说,黄色的内容多得很。有些纯粹就是在写乱七八糟的故事,在胡编乱造。那些作品应该属于当时的地摊文学。大家只是为了热闹,为了赚钱而写。《红楼梦》则不同,它写的不仅仅是这些,所以就保留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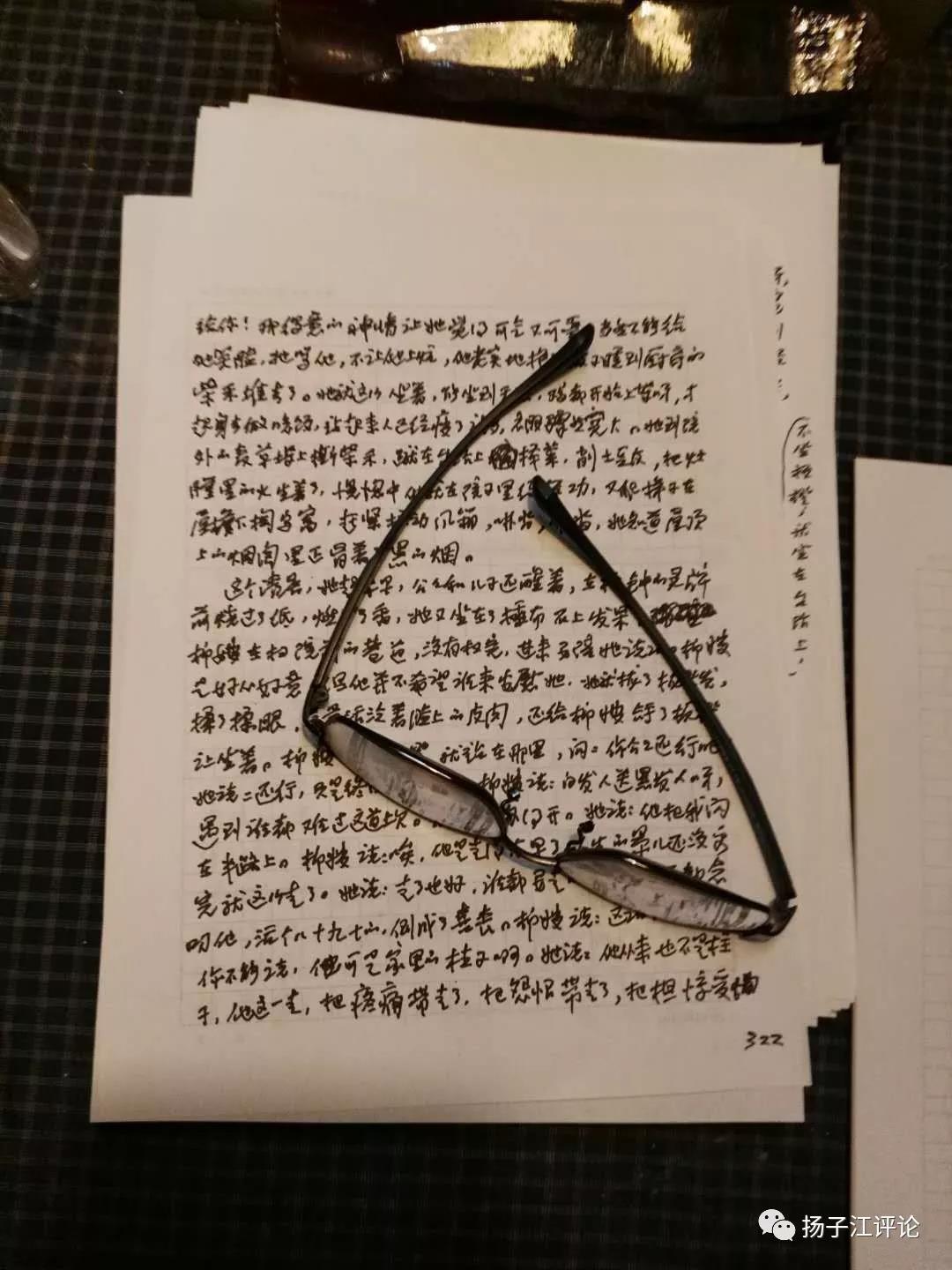
《山本》手稿
杨 辉 所以说到底还是小说观念的问题。有何样的观念,便有与之相应的小说作法以及评判的标准。
贾平凹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社会对小说观念影响很大。它以种种力量强迫着去改变某些东西。最后就落得与小说的初衷原来越远。你要是不忘初心,要追问小说最初是怎么出来的,就会发现不同时期观念的差别。现在我有时还在想,关于走路,人天生就是会走路的。但是你如果要说怎么走路,先伸出左手再迈右脚,再收回左脚和右手。这样来教的话,谁都不会走路了。小说也是这样子,它是必然发生的,就像吃饱了要打嗝一样。反正是很自然的产物。但是咱们受的教育,咱们说的写作过程,社会对你的要求,你慢慢地就放松并开始变化了。社会的力量的影响是很大的。
杨 辉 在混乱的世道中,涡镇出了井宗秀、井宗丞,也出了阮天保。他们在混乱的世道中与世道一同混乱着。未见出井宗秀、井宗丞有更为宏大的抱负,阮天保行事也以个人利害为准则。他们杀伐决断,并无常规,彼此均分享着暴力与血腥的历史逻辑。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乱世中的“英雄”。但涡镇出了井宗秀,却并未得到生活的平安,反而在乱世中愈陷愈深,终止于沦为一片废墟。因此,陈先生以为,啥时没英雄,世道就好了。这似乎有道家“绝圣弃智”的意思。不知陈先生的这一说法有何深意?
贾平凹 你已经替陈先生解释了。
杨 辉 如您所说,井宗秀和井宗丞皆有原型。但原型人物的本事(史实),却与虚拟世界中的人物并不能一一对应。不知井氏昆仲与其原型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别?这样处理有何用意?
贾平凹 现在一些读者有兴趣考证井宗秀和井宗丞的原型,其实是不必的。井宗秀和井宗丞是有原型,但仅仅是攫取了原型极小极小的一些事,而最大的是通过那些历史人物了解那一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一系列的社会情况,可以说以原型出发,综合了众多,最后与原型面目全非。
杨 辉 原型人物的本事在具体进入作品的时候,您是如何处理的?
贾平凹 拿井宗秀的原型井岳秀来说。我其实是只是用了一点关于他的材料。比如他晚上在别人家门上挂马鞭,这家人就得把女人送到他那里。但这个材料在用到写井宗秀时,已经有一些变化。将井宗秀处理成因受伤而导致的“无能”,就是改变之一。包括关于他的死亡,有几种说法。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些说法孰是孰非,已经难以辨认。我是专门采访过三个当事人的后人。一个就是当年去抓杀害井勿幕的凶手的那个人的后人。后来他给我说了井岳秀之死有好几种版本,有的说是配枪走火弹中胸部而亡。有的人说其实是被人暗杀,但是说不出凶手是谁。事情发生后,有人跑到后院了,发现树底下有几片叶子。凶手就在树上蹲着呢,然后把他揪下来……。剥皮的事情,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写完了。关于这件事情说的有很多次,太暴力了。里面有一个情节是井岳秀把杀害他弟的凶手剥了皮,用皮做了个马鞍。他们后来巡逻的时候,他骑一匹马,旁边另一匹马马鞍上放着他弟的照片。他坐在人皮做的马鞍上面巡逻,是有这样一个事情。但小说处理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变化。
杨 辉 关于井岳秀之死,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判定真伪。就说是当时根本不是配枪走火。井岳秀被打死之后,当时马上就来了一个卫兵,叫井继先。井继先来了以后,发现配枪枪机就没有打开。然后就发现了您刚才提到的那个细节,树底下有落叶,还有房上的几片瓦被人踩落了。而追随井岳秀多年的解春卿根据当时的大的形势判断,暗杀行为的幕后主使有可能是蒋介石。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却不知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如实上报肯定不行,因为当时在双十二事变前,因各种原因比较敏感。井府于是给于右任打电话商议此事。于右任建议以被共产党暗杀上报为好。“一可取悦蒋介石,崧生(井岳秀)受表彰,二可保亲属和子弟的安全”①。这样处理,就等于把这个问题完全转化了。
贾平凹 这些都是民间的传说,可靠与否难以辨识。还有说旬邑游击队,陕南游击队,把人点天灯。天气大多冷得很,把人衣服剥下来后再杀了。《山本》中写到的游击队的重要事件,没有一处不是有依据的。还有在树林子里迷路那一段,那是陕北的刘志丹的家属的回忆。据说就是他逃难的时候的经历。他在树林子里跑了,迷失了方向……类似这样的细节,都是乱七八糟凑起来的。你看有好多个传说,都是关于安吴寡妇,就是周莹的,《那年花开月正月》中的主角。我没看这个剧,但用了一些关于这个人的民间传说。比如说她是金蛤蟆变的,她从路上走过去,确实有很多人在她走过的地方挖金子,当然是什么也挖不到,但仍然有人相信这个传说。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她在院子里登高台,以便于管理。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周莹当时弄这个茶叶,我就用了这部分材料。但《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好像没有用这个材料。还有民间传说因为周莹是金蛤蟆变的,所以腰长腿短,能行得很。那些关于掌柜的贪污,周莹驯服的事,也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在具体了解的过程中,会遇到方方面面的材料。如果全都用的话,肯定是写不下。我看过的材料,有的是回忆录,有的是革命史。革命史基本上都是你回忆一段,他回忆一段,里面会提到各种杂事。还有那个夜线子,是在彬县和旬邑活动的土匪,也是真实的事。
杨 辉 有论者认为,要写二三十年代的历史,尤其是已经有“定论”的历史,是会有一些困难。他们从根本上不认同关于历史的个人书写,认为这是对历史的“想象”性书写。这种思路,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贾平凹 他这个思维是这样的。我想的是当时的历史发不发生。如果站在一个高的地方看待这个,其实就是发生过的事情。但怎样描述,各人的说法或许不一。因为有人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应当如何如何。在这个问题上,的确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在写作过程中,是把这些都避开了,闭口不谈这个问题,也避开这种思维方式。我之前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长期以来,中国文学里的政治成分、宣传成分太多,当我们在挣扎着、反抗着、批判着这些东西时,我们又或多或少地以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模式来挣扎着反抗着批判着。所以我当时想,谁和谁都参与过这个大的历史事件。但是这些东西最后全都没有用到作品里。所有的故事都局限在秦岭这个地方。好多东西,一旦和大的历史结合起来,就不好处理。不好处理的地方就模糊处理。比如说模糊了时间和各种番号。故事的时间也和历史时间有错位,就是要达到模糊处理的目的。
杨 辉 像作品中对冯玉祥相关史料的处理,就是这样的情况?
贾平凹 不管是冯玉祥,还是那个白朗,处理方法是一样的。人物一旦进入小说,就得符合小说自身的逻辑。这都是创作,不能“实”看。如果非要和史料对应,每一处细节都要考证一番,那就麻烦了,也没有必要。
杨 辉 所以不能把《山本》简单地划归为历史小说,也不能将其归入“野史”的范畴加以讨论。因为在已有的观念中,“野史”和“正史”处于对立的状态。读者也自然会从对立的意义上去理解,这样一来就等于把《山本》原本丰富的内容放在一个比较狭窄的思维框架里了。另外一方面,如果还是用“野史”来理解《山本》。自然会有人以历史史实作为衡量标准,来指陈作品细节的“真实性”。当然,《山本》的确写的是历史。但写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展示二三十年代发生于秦岭的历史的史实。而是在天人之际的意义上考察历史、社会、人性种种方面的复杂的矛盾纠葛。整个作品的气象和境界与普通的历史小说还是很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把历史人事放在一个更大的天地视野里面来看,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不按历史的方式来解释历史,也是诸多解释历史的一种方式。如果不局限于简单的思维,不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视域中理解《山本》所敞开的世界,那就不难体会到您写作的用心。这个问题,其实您在后记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是大家还是从这个思路来看。
贾平凹 大家现在习惯了从一种思维出发去理解问题,就把复杂的东西看简单了。我为什么要写这个题记。就是强调《山本》的目的,不是写秦岭那些历史,而是想从更丰富的状态中去写中国。不是为了纪念什么,反对什么,歌颂什么,而是从人的角度来从这些事件中吸取怎样活人的道理。从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中,反思怎样活得更好。小说实际上起的是这样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表达什么观念。
杨 辉 陆菊人这个人物在作品中也非常重要,如您方才所说,她的原型是安吴寡妇,但却并不局限于安吴寡妇的真实经历,而是有较多的变化。这个原型的故事,是如何被您编织入《山本》的总体结构之中的?
贾平凹 陆菊人也是如此。可以说细一些,她的身上有陕西历史人物周莹的影子,更有我本家三婶的影子。我在以前多次写过我的这位三婶。三婶是农村妇女,一字不识,但明事理,主意笃定,气质非凡,人也漂亮。记得当年我小妹出嫁到县城,我三婶作为娘家人去坐席,县城里的那些宾客都以为她是什么老干部。话再说回来,任何作家写任何东西,其时都是在写自己。
杨 辉 陆菊人与井宗秀有着相互参照的意义,彼此虽有好感,但却发乎情止乎礼。陆菊人做了茶总领以后,可以说也介入了涡镇的世事。她似乎比井宗秀、周一山等人更明白通透。井宗秀、周一山、杜鲁成相继死去之后,陆菊人会是涡镇的又一个“英雄”从而担负起涡镇的重担吗?
贾平凹 陆菊人和井宗秀是相互凝视,相互帮扶,也相互寄托的。如果说杜鲁成、周一山、井宗秀是井宗秀这个书中人物性格的三个层面,陆菊人和花生是一个女人的性格两面。我是喜欢井宗秀和陆菊人合而为一,雌雄同体。若问陆菊人是否会担负起井宗秀之后的涡镇的重担,我想她不会的。我也不让会,人的种种能力只有在大变革中才可能暴现出来。
杨 辉 麻县长渴望有所作为,却终究不能作为,看透这一点后,便把心思用在了收集整理秦岭草木志和禽兽志上。虽身患绝症,却最终自投涡潭。但他编纂之《秦岭志草木部》和《秦岭志禽兽部》却可能流传下来。这是否在寓意“物”比“人”更为长久?就作品总体而言,如何理解这个人物比较合适?
贾平凹 麻县长是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心里明白,也有骨气,但不会长袖善舞,又无搏击风云的翅膀和利爪,他只有无奈,只有哀叹,留一点散乱的文字在世上,这是时代的悲凉。
杨 辉 宽展师父也是《山本》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她给陆菊人和花生解释《地藏菩萨本愿经》,说那是“记载着万物众生其生老病死的过程,及如何让自己改变命运以起死回生的方法,并能够超拔过世的冤亲债主,令其究竟解脱的因果经。”而在小说临近结尾处,较多的悲惨事件已接连发生,涡镇也逐日逼近城毁之时,花生给陆菊人念《地藏菩萨本愿经》经赞“愍念众生,长劫沉沦。悲运同体,慈起无缘。当处地狱,冀解倒悬”似乎别有深意。不知这个人物以及《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山本》中有何寓意?
贾平凹 130庙大殿门口的对联就是寓意(即“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安忍不动,静虑深密”),尺八声就是那个年代的调子。前边说过,人类之所以能绵延下来,就是有神有爱,爱是人间的,中国是泛神的,而佛道是其中最大的神。佛慈悲,讲究因果,它是来匡正的。
杨 辉 借用学者林安梧的说法,陈先生以言语治病的方法,乃是一种“意义治疗”,约略近乎《古炉》中善人的方式。在《古炉》日渐颓败的环境中,善人的现实作为虽然有限,但对古炉村的精神世界而言,却不可或缺。陈先生在《山本》中的作用庶几近之。为《山本》混乱的世界中设置这样的形象,您有着何样的考虑?
贾平凹 我一直喜欢陈先生这样的人,陈先生和《古炉》中的善人是同一类的。他们首先是医生,又都是道家,做身与心的救治,陆菊人的成长,背后就是陈先生。
杨 辉 《山本》中有很多具有隐喻意义的细节。比如井宗秀属虎,请周一山来涡镇,就是取打虎上山的意思。而周一山后来不同意预备旅去平川县,也是考虑到虎落平川被犬欺的忌讳,涡镇在虎山下,自然利于井宗秀的发展。后来因内部矛盾,井宗丞死在了崇村,邢瞎子枪毙他之前,说井宗丞不该来崇村,这是犯了地名,“崇”是“山”压“宗”么。拆平川县钟楼时,因未选吉日,陈来祥就因之殒命。任老爷子的徒弟严松因与涡镇人交恶,便在修钟楼时放进了会给涡镇带来邪气的木楔。钟楼甫一完工,灾难便接踵而至,先是火灾,接着井宗秀被杀,继而涡镇遭到炮轰几成焦土。如是种种,无不说明存在着难于把捉的,与现今的观念全然不同的世界内在的运行规则。这些规则在被称为“前现代”的社会中乃是需要遵循的基本规律,并由之形成了人伦及社会秩序。但随着现代性的展开,如上种种已逐渐无人领会。《山本》以及您之前的作品在世界的此种面向上多用笔墨。写这些内容,除了巨细靡遗地呈现已逝的人的生活状态外,是否还有别的用意?比如,像司马迁一样,意识到历史理性之外的非理性的,神秘的一面?有点类似古人所说的“人道”之外的“天道”。
贾平凹 《山本》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动乱期,又是秦岭之中,种种现代人所谓的神秘、甚至迷信的事件,在那时是普遍存在,成为生活状态的一种。正是有那样的思维,有那样的意识,有那样的社会环境,一切动乱的事情才有了土壤。
杨 辉 同样是在后记中,您表示,秦岭中“山”与“谷”的错落,树与树的交错,以及它们与周遭环境的呼应,显现着这个地方的生命气理,由此您安排着《山本》的布局。《山本》的章法,因之也接近于陈思和所说的“法自然”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是如何达成的?
贾平凹 我一直热衷写作中大的意象和其实的写实,“法自然”就是让人读了书坚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温可听可触,而这一切又都是一个大的意象,将读者的思维引向“大荒”境界。但我的能力还是有限。
杨 辉 在《山本》的写作过程中,您曾书写两个条幅。一为“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一为“襟怀鄙陋,境界逼仄。”前者容易理解,后者却教人颇费思量。不知这两个条幅,与《山本》的写作存在着何样的关系?
贾平凹 书写那两个条幅,“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是一种要求;“襟怀鄙陋,境界逼仄”是一种警惕。
杨 辉 以气韵及笔法论,《山本》无疑再度说明您此前提及的从“水之性”悟得文章之道的独特价值。作品气韵生动且文气沛然,大有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之妙。但这部作品表面的“柔性”(水)之下,包含着内在的“刚性”(火)。而后者属“火”一类作品的特征。在《山本》的写作过程中,您是否有融合二者的用心?
贾平凹 写《山本》时我要求“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在写法上试着用《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战事会是怎么样。
杨 辉 在后记中,您提到老庄的区分,在于“天人合一”与“天我合一”的差异。“天人合一”是哲学,“天我合一”是文学,但语焉未详。您能否对“天人合一”和“天我合一”详细解释一下。
贾平凹 天我合一,是必须要经过我,我的眼,我的心,我的审美。《三国演义》《水浒传》是经过了多少说书人的“我”而成为《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伟大画家的山水画都是山水与其相遇而“迹化”。小说家都是有了“我”,才有了“第二自然”。
杨 辉 如果再稍作延伸,便不难发现您融汇不同思潮不同写作方式的用心。比如《山本》中有极为扎实的写实面相,也有由丰富复杂的意象构成的“虚境”。既有现代的观念,亦有基于中国古典思想的思维方式。
贾平凹 我是不满意仅仅去继承单一的思潮和流派的写作方式。如果仅局限于单一的思维,仅以某一类作品作为写作的范本,写作便不会走得远,而且容易钻牛角尖。因为当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别人早已经走过去了,这样你永远在别人后面追着跑。而且咱们现在对现代派的观念也可能是有问题的。什么是现代派?现在好多人仅仅将现代派落实到写法上,而没有落实在其对整个人类世界的大的思想和观察上。所谓的写法,也就是翻译体的写法,更多的是写心理活动,且把这故意推到一种很极致极端的状态。现代派的背后有复杂的哲学的支撑,并不是简单的写法的革新。如果仅拘泥于写法,便形成后来各种荒诞的、不正常的文字表述出来。热衷于用变型变态的文字来叙述一个东西。基本上写作就停留在这个状态上。为什么?后来很多人对卡夫卡特别推崇,就是觉得他特别荒诞。但如果一味拘泥于荒诞,在中国这个地方,就会遮掩许多对现实生活的真实的观察。不将眼光投向丰富复杂的现实,而开始向壁虚构胡乱编造。现在有些人写虚幻的,天上的东西,写得风生水起,看着很热闹。但你让他具体写一件事情,他一句也写不出来。这最终就导致他的作品完全是用他自己的观念写出来。
杨 辉 已经形成的思维方式的确会影响到对现实和作品的判断。包括一些写作者也在倡导回归中国古典传统。但稍加辨析,便不难发现他们理解传统的思维,仍然是现代的。因此上,对古典传统中的一些重要的观念及其意义,是没有办法发现和理解的。有些人也在效法《红楼梦》,但却仅止于结构、意象或者语言,对其中所蕴含的中国古典思想及其所开启的世界观察,照例是视而不见的。甚至认为这些思想观念是没有价值的。
贾平凹 《红楼梦》出现前后的那一批人,他们对现实对世界认识得很深。作品在细节上渗进去的那种力量,不是外加的。他们看待世界的目光不一样,说出的话自然不一样。《红楼梦》那一套纯粹是中国思维。中国人那个时候行为处事就是那个样子,所以《红楼梦》里面并不是故意要弄什么思想、意象等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现在的小说,总想故意往里面加一些什么。实际上小说的产生,你让它自己生长。就像栽一盆花,让它自己生长,而不要给它减一下加一下染一下,以让花更好看,而是让它自然生长。研究者现在认为《红楼梦》有警示意义。曹雪芹在写作过程中,不一定有这样的明确的意识。我是这样认为的,只要你把一个人的本性写足写通,他自然就会生发出那些意义。这是必然有的。但关键是你要把它写通。比如说种庄稼。麦子必须要长到一尺五,才能结大的麦穗子。当把生命活到最圆满的时候,自然会有大的气象。所以你写麦穗的时候,写到一尺五,它必然会结大麦穗子。但是如果写不透,气力就会不够。写不透的原因是没有看到。看不到那一步,自然那一步也就写不透。这个时候,它里面肯定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只好强加一些东西。
杨 辉 所以就像您曾经谈到的,作品要有扎实细密的写实。而在写实的基础上,去张扬一些意象,从而形成独特的境界。差不多从《废都》开始,您尝试“虚”、“实”相生的笔法。在《山本》中也是如此。《山本》有扎实细密的写实。无论人物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自然物色,都有细致的描写。这些描写甚至超过您此前的作品。当然也写到历史,写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的关系。但您把历史、社会、人性都放在一个更大的精神空间中。让历史、社会返归至与自然同一的状态,使其互为参照。
贾平凹 其实就像现在人说的,把时空拉长一些,去看任何事情。我经常说,在一个村子看不透的事,放在镇上看就很容易理解。而镇上看不透的事情,放在县上看,以此类推。把大事当小事看。小事当大事看。国际上的事情弄不清楚的时候,你就把他当成你村子邻里的事情来看待,你就能看出好多东西来。包括历史,什么叫历史?孔夫子说,逝者如斯夫。这瞬间就过去了。咱现在写小说,实际上就是在写历史。如果说太近了看不清,你就要离远一点看。我们常说每一个人的层次不一样,观点不一样。你整天关心的是你生产队的事情,你肯定就不了解县上的事情。但县长肯定不如省长。省长管的是一省人。省长又不如国家主席。一个国家主席,关注的是整个国家的事情。站得高了,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注意力也就不同了。比如说我当个村长,每天面对东家长西家短,把你能气死。但县长一看这是些什么事情,不就是鸡飞蛋打鸡毛蒜皮的事,大不了把鸡杀了,也就十来块钱。但对农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所以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看到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一样。你现在看楚汉的故事。不管你怎么评价刘邦项羽。有些人说项羽是个英雄,你不会产生杀头的危险。但当时对那一段历史怎么看,和现在自然是不一样的。视野放宽以后,很多看法自然也就不同。
杨 辉 张新颖先生提过一个观点,大意是说沈从文笔下的世界,要比“启蒙”思想所指认的世界“大”。也就是说沈从文没有把笔下的人物放在“五四”启蒙思想的框架中看,不对生活作所谓的高下的区分。如果局限于“启蒙”的眼光,则似乎自然地认为,“觉醒”的人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而那些没有“觉醒”的人,生命一如四季转换,好像一辈子下来没有多少意义。就是出生、长大,劳作,死亡,在此过程中把自己孩子养大,给父母养老送终。但是这样的人的生活也自有其价值。如沈从文所说,“他们那么庄严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他们在那分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替的严重。”如果在更宽广的视域中去看,尽管有一些宏大的历史主题在不断变化,但最根本的一些人的生活仍然周而复始如此终了。《山本》其实也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贾平凹 对着呢!这后面是一个啥症结?为什么古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天地贯通了。他把好多东西,人生,生命里边或者命运里边,经历的事情多以后,他就看透了,就悟出了好多道理。实际上天地间的道理都是一回事情,他就贯通了。但是咱们现在的社会整体缺乏那一种贯通。以分割的思维去看,很多东西就无法贯通。其实打通以后,你对于生命、婚姻、家庭以及人与人之间,或者宗族、姐弟、父母等等,看法就会不同,就彻底放开了。正因为社会要规范,所以有法律呀秩序呀等等各条绳子来捆住你,最终把散乱的社会捆在一起。当突然有人把绳索弄断的话,就一下子放开了。但这种放开,和未捆绑之前的散漫是两码事。我们为什么要读《易经》,因为《易经》里面把天地变化的东西都说清了。佛经讲因果关系,易经就是讲变化,依那样的思维,就会把事情想得特别通达。咱们经常说苏东坡人生旷达,实际上他是天地贯通了,在天地间去思考问题,眼光自然不一样。咱们现在只是站在地上思考,从一个团体,一个社会圈子里面思考,没有想到更多东西。举个例子,我经常想咱现在理解的命运的不测到底是什么,不好解释。如果把我变成一个蚂蚁。蚂蚁正在地上走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个什么东西把我压死。人看到了,知道是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养的狗压死了蚂蚁。但对蚂蚁来说,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将自己毁灭了。或者突然间洪水滔天,把天地都淹没了。如人类经常说的洪荒时期。实际上对蚂蚁来讲是那样,但是人去看的话,原来是泼了一盆水,正好把蚂蚁淹死了。实际上仅仅是泼了一盆水,是谁过去不小心踩了一下。如果这样去想象,人类发生的任何事情,你觉得好像很神秘的东西,其时有时候是有意识的,有时候却是无意识的,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以这样的思路,就可以从好多事情中慢慢醒悟好多东西:原来天地宇宙是这样构成的。什么灾难呀得失毁誉呀,也就看清看淡了。
杨 辉 所以说从“天人之际”的角度去读《山本》,可能是比较恰切的思路。《山本》写历史写人事,但却并不局限于历史人事的眼光,而是把历史人事放在天地自然的大背景下去描述的。
贾平凹 对!起码我是这样想的。我也不是针对什么,说谁是红的黑的,替谁说话或者反对谁,毫无那种心思,而且那样处理也毫无意义。我只是在里面寻找那种人生智慧,我为什么说不停地开一些天窗,就是开那些智慧的东西,个人醒悟的那些东西。当然不是很多,但一有空我就在里面写这些东西。而作品构思完成之后,自己也开始相信那是个真实的事情,是确实发生过的,确实有那样一个镇子,也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你自己都相信了,头脑里有一些成形的画面,然后把它写下来。对我有启发的就是《西厢记》。我觉得《西厢记》好像是真实的。但谁知道是不是真实的,那或许仅仅是个戏,但我觉得那是真实的。还有《红楼梦》。在读的过程中会觉得那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看电影,你看的时候确实觉得那是真的,但是电影一关,你面对的就是个银幕么。所以一定要把作品写真写实了,让读者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然后才能把读者引入另一个境界,不管是大荒的境界还是别的境界,都首先需要读者相信故事的真实性,这样才能产生一种幻觉,从而进入另一个境界。所以说就“实”和“虚”的关系而言,“虚”是一种大的东西。这又符合佛教、道教包括《易经》里边所阐述的,整个世界是一个大虚的东西,但是具体的又是很实在很扎实的一些东西。越“实”才容易产生“虚”的东西。而如果一写就“虚”,境界反倒是“实”的东西,最后就落实到反对或揭露什么东西。目的落到这里,境界就小了。境界一旦实,就是小的表现。“虚”实际上是大的东西,无限的东西。比如说天地之间,什么混沌呀,大荒呀,你感觉到的是个洪荒世界。作品应该导向这个境界。而到了这个境界,才能看到生命是怎么产生的。实际上好多哲学,好多文学等等,都是在教育人怎样好好活,不要畏惧死亡,不要怕困难,不要恐惧,不要仇杀,不要恩怨等等,都在说这个事情。一是解除人活在世上的恐惧感,另一个就是激励人好好做贡献。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教育最终都指向这个方向,让人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我觉得小说的最高境界也应该往这个方向走。小说的境界和哲学的境界是相通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杨 辉 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阐发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他研究的虽然多是古希腊思想家,但与中国先秦思想的重要一脉也是可以相通的。《论语》、《道德经》其实讲的也是这样的道理。首先关涉到的是人的日常(内圣),最后才开出治国平天下的济世情怀(外王)。也就是致广大而尽精微。
贾平凹 对!我觉得你从这个角度就挖掘得比较透了,就能解释好多问题。不管关注什么东西,最后终究还要回到人本身,但眼光却是大的高远的。现在的小说,总想着针对谁,颠覆谁或者反对谁攻击谁,目的小了,作品境界自然也就小。
【注释】
①李峰荫:《井氏双雄 血沃中华——孙中山和井勿幕、井岳秀弟兄们的英雄故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141页。
作者简介:贾平凹,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杨 辉,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