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写作是一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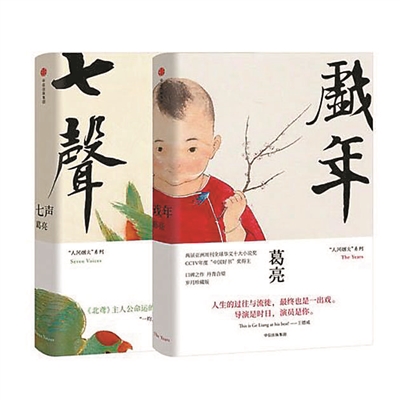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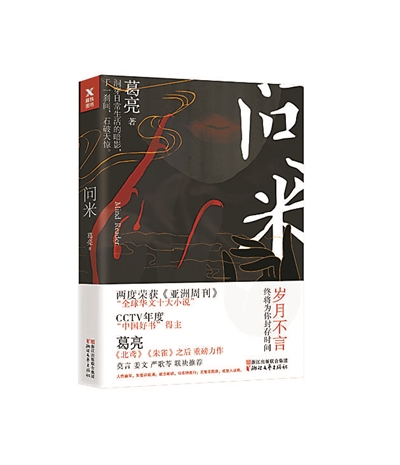

答题者:葛亮
提问者:木子吉
时 间:2018年6月
简历
葛亮,原籍南京,现居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文学作品出版于两岸三地,著有小说《北鸢》、《朱雀》、《七声》、《戏年》、《谜鸦》、《浣熊》、《问米》,文化随笔《绘色》、《小山河》等。部分作品译为英、法、俄、日、韩等国文字。长篇小说《朱雀》获选“亚洲周刊华文十大小说”,2016年以新作《北鸢》再获此荣誉,并斩获各项大奖。
1 你的新作《问米》新近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短篇小说奖。第一次写作悬疑题材,缘起是什么?
《问米》与其说是着眼于悬疑,不如说在对其进行解构。悬疑的终极意义在破解事件的真相,这一过程在阅读者的成见中,是会引起兴奋的。但这本书里的故事,无一不在表达所谓真相倏忽而至时人的无力感。或者说,悬疑成为了某种仪式感,构成了某种动力,去建设小说表层的逻辑,令人好奇甚而产生勇气,亦步亦趋,步步为营。但是,故事最终将偏离延续这一逻辑对重点的预设,你会发现,结局实际是有些颓唐的。生活的逻辑终于覆盖了事件的因果逻辑。这是日常强大的力量,充满了意外与无序。或者也是重现生活的意义,生活模仿艺术,那些逾越想象的微妙与现实比艺术的格局更为精彩,或令人唏嘘。
2 《问米》的写作风格不同于以往的先锋或古典,语言也比较口语化,是在尝试靠近现实主义写作吗?
现实主义的界定非常广泛,我除了早期《谜鸦》比较先锋之外,后面基本在走现实主义的路径。《问米》有点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态度,有实验的成分,这种置于非常情境的人性考量会非常凛冽的,我会给他一个合理化合乎现实的逻辑。《问米》尝试不同于以前的语言风格,更加生活化,之前的写作锤炼感比较强,是希望传达出精致的美感。
(问:怎么想到写通灵师的这种角色?)
我有段时间在河内旅行,很偶然碰到过这样的一个人。看起来通灵师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很远,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河内他就是个普通人,通灵师就是他的职业而已。包括《朱鹮》里自闭症的孩子也有原型。通灵师实际上在小说里是个演员,穿梭于阴阳两界实际上是个伪装的身份,并不是真正可以在生死两界穿梭,就是凡人,没有异于常人。我想表达的是非常身份包裹下的一个凡人日常化的景象。
3 从长篇小说《朱雀》、《北鸢》到短篇集《七声》、《谜鸦》、《浣熊》等等,很多书的出版过程中你好像有很多点子并非常乐于参与出书的环节?
我非常尊重编辑的想法,一直以来和做书团队合作是很美好的。每本书它不单只是一本读物,还应该代表作者、出版团队对于内容的消化。我特别高兴的是他们也很尊重我,其实每本书的封面设计我都有参与,从审美到理念,我乐意在这些层面上去参与。早期比较幸运的是,我参与合作的设计师都是两岸三地受认可的有代表性的设计师,比方聂永真,彼此审美,这么多年来是一种共同成长的感觉。
我在出版过程中跟编辑团队的沟通,挺得益于我在深圳商务印书馆几个月的工作,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对工作量的要求非常高。我当时几个月的时间做了不同类型的11本书,出版流程、环节的沟通都非常熟悉了。在这种前提下我跟我的编辑团队沟通是非常顺畅的,我知道他们的角度和立场。
4 不得不提到的是你显赫的家世,陈独秀是太舅公,祖父是葛康俞,出生在这样的家族对你有哪些影响?
这个话题像录音机一样不断被重复(笑),但我不会回避。实际上这部分对我现在的生活不构成任何影响,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是家常的人,我家族里的长辈不管怎样就是一位长辈咯(笑)。
我也没有特别要活出什么,也不是要和家族壁垒分明或怎样,这种光环实际上是一种外在的界定。比方说如果他们不是历史人物就是身边的平凡的长辈,你会特别说我的成长和他们无关吗?不会的,他们对我而言就是一个这样的老人。
祖父的严谨对我作为研究者的态度会有影响,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但这种潜移默化不太会把它作为体系化的东西讲出来,实际上在那种特殊的时代下,我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没有什么特殊性的空间。这种感觉挺好的,不会把自己特别当成什么,一旦要定位自己什么样,那挺可怕的。
5 你以家族史为蓝本,历经七年写作长篇小说《北鸢》并荣获大奖,你怎么看民国时代?
那个时代一方面是动荡的,也因为变动不居,出现了许多的空间,不止为当下者的言说,也为彼时提供了诸多人生选择的可能性。《北鸢》涉及的人群相对广泛,政客、商人、文人、伶人不一而足,每个人都面临时代的考验与迷失。仅就知识分子群体,1905年科举废除,“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仓促剪断,出现了分化与转型。有的在二次革命后设帐教学,广纳寒士;有的半隐半士,在学院中保持作为艺术家的纯粹;有的投身商贾,所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因家国之变,选择实业,远可兼济,近可独善。这些人有着不同的时代认知立场,处世方式各有千秋。知识分子的分化正是“不拘一格”最为明晰的表达。这是时代的包容,也是民间的包容。无论境况如何,都保持着内心的尊严与体面。这是那个时代的好,可见一代中国人的平定中和,拥有与时世和解的能力,彼此砥砺,相互成全。
6 你的小说很有烟火气,平时会关注热点话题吗?
会关注热点但不会去追逐。如果对某个话题感兴趣,会沉淀一段时间,觉得适合我去表达才会再捡起来。我写作比较随自己的心意,不会去分门别类、拘泥于事件本身,有时某个事件生发的某一点会触碰到我,可能就会取其因由,随意点染。更好的状态是经过反刍之后把它变成认同的现实与文学的逻辑。
7 你目前在港大任教,如何平衡写作与教学的关系?教师与作者的身份你如何定位?
长期以来,写作与教研对我而言,形成了某种彼此相照的状态。因为我本身是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写作行为更似一种途径,实现与研究对象的将心比心,反之,教学与研究一方面让我更为接近文学现场,同时,研究习惯也的确影响了我的写作行为。比如,对资料相对精准的要求、田野考察,都为写作本身奠定了基石。
两者是独立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互补的。我自己从硕士开始写作到现在二十年了,这中间心态也在变化,比如长篇小说的格局感、架构感和学生训练的逻辑能力是相关的,我不会割裂开两个身份,尊重两者之间的独立性。比方说我在上创作课时从来不讲自己的作品,我不想把我作为作者的主观的操纵感输送给学生,宁可讲其他人的作品,能抽离地从欣赏、判断角度把文学作品的可能性传达给学生,我觉得这是对学生负责的态度。
(问:你认为香港文化现状、年轻人的学养如何?他们升学就业的压力大不大?)
香港的文化板块里面很重要的一块是传统国学,这部分香港保留得相当完整,和历史遗留是相关的。五四运动时期,钱玄同、刘半农和林纾的一段公案,新文学与遗老文学观念上的砥砺,新文化运动改变了整个文化格局,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大家有没有问:遗老都去了哪里?其实当时很多遗老就来到香港,比如林纾、郑孝胥……所以香港的新文学运动比大陆地区晚了整整十年,一直到1927年,鲁迅来做了两个演讲,《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才开始真正有第一个文学期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港大的课程设置是以旧学和小学为主的,香港的文化传统是相当深厚的。
香港人的学养不能一言以蔽之,香港的流行文化和学院文化实际上是壁垒分明的,学院是学院,流行是流行,不像内地经常混在一起来说。香港学院派年轻人的学养都相当不错,这块分工相当明晰,深造的和一般意义上的普及教育壁垒分明。和欧美相似,香港的研究生一个叫做课程硕士,一个叫哲学硕士,哲学硕士将来就是要对接博士继续深造,进入到学术体系做研究的。
8 你喜欢的授课方式是什么?希望成为什么样的老师?
这个蛮有趣的,我家三代都教书。我祖父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在中央大学非常注重传道授业,他那时候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是明晰的师长与后辈的关系。到我这里实际上就没有分得这么清晰了,我上课希望跟学生有互动,希望有一些观念的碰撞,并不是说单纯的一个知识的传输者,已经逾越了这些,我教文学史也要教创意写作,不同的课程方式是不同的。
我觉得通过大学教育把学生培养成一群完全意义上的规矩的人是失败的,抹杀了个性。他将来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一群人。
(问:怎么看学生是自己的粉丝?)
学生能体会到我对他们的责任和尊重,他们喜欢我的作品有时会拿书在课堂后来签,就是一个前辈的感觉,我非常感谢这种自然的感情流露。我不会在校园里面刻意强调自己作家的一个身份,但是会接受学生的善意,就是顺其自然吧。
9 你认为写作技法和灵感哪个更重要?你写作的动力和目的是什么?
两方面同样重要,因为互为容器和载体。我希望每部小说集都有独立的气质,而这一点不仅体现于题材,形式层面也相当值得重视。《谜鸦》是我早期创作的实验意味浓郁的小说,表达青春谛视中的都市,是恰如其分的。《七声》、《戏年》写成长经历与人事,笔调更为温和平朴,叙事方式也是小说本身的温度所决定的。
香港的生活节奏太匆促了,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能让自己安静下来的途径。
10 写小说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未来创作偏重长篇短篇?
看清自身和世界。写小说的过程,多少是一种检阅。于一己而言,代表着回溯与重省。对历史,则是梳理与再现。林林总总,最后都是渗透入细节,成为人生的铭刻。
长篇短篇我都喜欢,这个不一定,我都蛮重视,未来都会涉猎。短篇更加当下,语言节奏感更加跳脱;我更重视长篇体现出来的文字厚度,我需要一种语言去匹配。对我而言,要不断开采自己在写作层面的可能性。“一个好的写作者有个很重要的特点:让他的读者捉不住。”我觉得这句话蛮有趣的,一以贯之之外不断开采自己的东西,一方面静水长流,一方面变动不居,写作才有活力。
(问:你会担心长篇作品与现在流行的快餐阅读不匹配吗?)
我非常喜欢园林,陈从周先生写关于园林时提到,不同园林的好处,有的很大有的很小,看园林有不同的方式,可以流连、可以徘徊揣摩体会。有一种方式叫洞观,以比较快的节奏在园林里游弋,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作品观感是不一样的。从我的写作而言,有时会荡开一笔,有时会将文字节奏调整得更舒缓。
我希望读者能有他们的空间,在文字里去沉淀跟流连。小说的逻辑不仅仅是事件的逻辑,它的停留有时是一种文学的逻辑。在快餐阅读的氛围里我不会调整写作的节奏,读者的审美能力是不可低估的,比方说《北鸢》在市场角度来说销量已经几十万了,这个数字已经能说明读者的反馈。这本书前前后后写了七年时间,文字是沉淀的,当我把它呈现出来,读者可以体会到里面的表达或快或慢的尊重,有共鸣才会喜欢,读者是非常真诚和聪明的。从写作来说我不会担心,就是发乎本心,不会去照顾市场需求,这违背我的写作本心。
11 你个人的成长回忆提到,你在南京长大,又在香港开始写作、成名。对你生命中两个重要的城,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南京与香港,气质迥然,一古一今。前者奠定了我对事物的审美和性格,香港更加像某种导引,将我血液中文字表达的冲动激发出来了。这很微妙,如果不是来到香港,我也许不会开始写小说。对这座城市本身的表达,于我而言又有相当的挑战。它太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
12 京戏、古词古曲、临帖等等这些中国传统元素经常会出现在你的作品中,日常生活中你经常研习吗?可以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吗?
我们家里几代京剧票友,耳濡目染,到我仅是皮毛。书法临帖能让人沉静,敛气于内。香港的生活节奏,如无个人意念的介入,是极易被大环境卷裹的。这个城市有许多山,时时开门见山,也是对其逼仄环境的补偿。所以登山与摄影,是来到这个城市才养成的习惯。
13 你的小说书名大多以动物来命名,《浣熊》、《朱雀》等等,头像也是很萌的长颈鹿,你很喜欢养小动物吗?在繁华都市怎么处理养宠物的问题?
是的,我小时候养的动物比较多,猫狗鹦鹉乌龟鱼蝾螈……能想到的几乎都养过。它们代表着这世界尚值得善待和美好的一面,在欲求上,也更为单纯和直接。
人与动物应该是互相尊重的,被遗弃的流浪猫狗实际上是对生命的一种不尊重。宠物存在的意义不是因为要依附于人,而应该是等价的、平等陪伴的关系。“如果你没有做好对它们负责任的准备,就不要养。”我比较赞同这句话。
14 你的阅读偏好以及有哪些作家对你影响比较大?
我看的书比较杂,和阶段性的喜好相关。历史类的书籍一直在看,最近在看瓷器、园艺类的文字。喜欢的作家,包括沈从文、黄仁宇和陈从周。国外的作家对我有影响的,包括聚斯金德、麦克尤恩和石黑一雄。
15 喜欢的导演作品有哪些?你如何看待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
我写过一本《绘色》,是从小到大的观影经历,通过小说的方式表达出我这个面相。特别高兴的是,戛纳刚刚颁奖出来,刚好是我最喜欢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他把所有的非常事件能够做到日常化,这是很高超的素质,看他的东西很温暖,我希望我的写作能达到这种状态。《小偷家族》的主演Lily Franky我也特别喜欢,他是个作家,演电影更像在玩票,特别真实特别日常,非常松弛。像李沧东的《诗》我也写过评论,从心里面我很崇敬这个导演。
文学作品与影视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独立又互为因果,有时候文学的意境会为光影化提供因由和灵感,是作品另一种活力的呈现,如果两方面都是真诚的,我是乐观其成的。
16 平时有哪些兴趣爱好?
摄影、旅行、去博物馆看展览,尤其一些画册上的艺术品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展馆。每次遇见其真迹,都有他乡遇故知的欣喜。有一次在阿根廷的National Museum of Fine Arts,忽然撞见了两幅莫迪里阿尼的作品,当时完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那一瞬间的激动,如同老友重逢。
17 你出生在双鱼月,你认可自己的星座吗?
据说双鱼这个星座盛产艺术家与政客,我的月亮星座在水瓶,说明在艺术性之外兼具感性与理性,月水瓶有鲜明的逻辑感,我写作时的系统感、结构感可能来自于这个。我觉得它起码有某种预设,在这个时段出生的人,应该是身心自由且有格局感的。
18 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从心所欲,不逾矩。
19 未来两到三年有什么规划?
写完新长篇小说。完成一个关于建筑文化的研究项目。希望生活的节奏可调节得再舒缓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