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人物之小与人心之大
一
金赫楠:从2002 年的那篇《飞翔的女人》开始,我一直在阅读你的小说。一路读下来, 发现你的小说创作一直专注于那些生活在乡村和小城镇的人和事,村夫农妇、基层办事员、个体小老板等等都在你的小说中充当着主角。我想知道,你的写作为什么如此钟情于这个人群?其实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有些担心会对它不太以为然,这似乎是一个最最大路化、最最老套的问题。但我仍然想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的对话,因为在我看来,这关乎一个作家面对生活时候的兴趣取向和情感趋向,甚至说得严重一些,这关乎一个作家的文学世界观。
胡学文:其实我每次开始写作的时候,脑子里并没关于人物“大”和“小”的明确概念,我只是在写我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人。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并不在意自己写作对象的身份——虽然一个人肯定是有某种身份的,因为我觉得一旦进入写作,身份不过是一件衣服,而我的小说想要触摸到的是衣服包裹的人,与衣服无关,或者说不是衣服决定一切。我自己就是小人物,为什么要写大人物?当然,这和我的经历不无关系,从童年、上学、参加工作到现在,我接触最多,或者我身边的人多是小人物,我没有理由不写他们。
当然,也不是说我就没有接触过别样的个体和人群,近些年,我也接触过官场中人、商场中人等等一些所谓似乎更高级一些的人,甚至还有亲朋好友知道我在写小说,时不时主动向我提供很多传奇曲折的身边故事,但这些人和事,却总是引不起我太大的兴趣,更没有将他们写进小说的愿望。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兴奋点或曰情感点,我的兴奋点就一直停留在那一群人身上。我把它们称之为“那一群人”,因为“小人物”这个概念是他人评定的,是从他们世俗意义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定义而来的。
如果一定要界定的话,我更愿意称自己的叙述对象“小人物”,而不是“底层”。因为总觉得底层两个字似乎不能囊括小人物的全部,或者说给人的感觉是只有人之小,没有心之大。从某种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上看,他们是小,如果说我注意到这种小,同时我更注意小这层外衣包裹着的大,那种心的宽阔让我着迷。而尽可能地去发现和呈现这种“小”之后的“大”,是我对自己小说写作的期待和要求。
金赫楠:我倒是从未反感“底层叙事”这样一个概念。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的衍生与发展从来都内含着对于事物的命名,文学的基本载体语言本身也是有命名性的。无论从文学史意义还是从理论批评意义上所命名的“底层文学”对于真正的创作又会有什么损害或者妨碍吗?重要的还是作家本身对于流行叙事腔调自觉地警惕与疏离。近些年来,底层生活和底层人物的确一直在以成为一个时髦的题材参与着当下的小说创作,曾经不同风格的作家们如今都来赶“ 底层”这个趟,底层叙事正在成为不同风格、不同背景的作家表达自己文学意图的万能场景和母题。我个人的阅读比较排斥的一种流行模式就是,拼命向读者展示底层生活的困顿与无奈,展示他们因为身处底层所遭遇的物质匮乏与精神贫困,然后居高临下地表达空洞苍白的同情,试图借此升华出作者悲天悯人的精英姿态。血泪交织、“ 站着干活,跪着做人”等等这些的确是底层生活的一种真实,但是过分渲染一种真实,往往容易遮蔽和忽略另外一种真实。如果展示困顿、表达同情与愤怒成了底层叙事惯有的异口同声,这个阶层与人群在叙事中的形象仅仅定格在被侮辱和被损害者,那么文学之于底层,没有完成应有的承担与责任。我一直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底层叙事中是不是根本就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式的矛盾:真正身处底层的这些人们,囿于文化水平、资源占有、生存条件的种种局限,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来实现对自己生活的真实呈现以及对自己内心的准确表达。所以他们和他们的生活往往只能以人物和情节进入作家的创作,通过作家的叙事来呈现和表达。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和事就面临着“被底层”、“被苦难”的可能。很多时候,即使那个作家原本来自底层,即使作家在情感上与他所书写的人是相通的,但是,终究是有隔膜的。所以,我从文学作品里面看到的底层世界永远都是作家化了的底层世界。这是一个我自己现在也没有想明白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即使悖论无法超越,但是作家却应该一直坚持超越的努力。
阅读你的小说,我能明显感觉到,你对人物充满感情,知道体恤和心疼他们,更重要的是,你一直非常努力地去理解人物,这理解中包含着对人物的尊重。面对一个被伤害而又无力反抗的人,同情与愤怒都是很自然、很容易生发的情感。这几乎每个健康的人都能做到的。而作为一个作家,情感的能力应该更多样、更深入。除了受苦遭罪之外, 你看到了小人物面对这些厄运时内心激发出来的反抗力量,那种躲在角落里隐藏着的坚韧。
我想知道,你每每写作的时候,都是从什么视角、携带什么样的情感进入小人物的世界?你在写作中怎样规避被同时期的底层流行话语所裹挟?
胡学文:一位作家曾说,要贴着人物写。我理解其含义一个是情感上的考虑,一个是叙事的策略。贴着人物,能触摸到人物的体温、心脏的跳动、情绪的起伏。言简意赅,此话甚好。但我觉得,进入人物会有另一种奇妙。作者在创作时完全进入那个人物,成为那个人物。我写《飞翔的女人》时,写荷子在地上像水一样流开,我就是荷子,那种无望击穿身体的痛,我摆脱不掉。
我曾说过,“底层”这个词没有出现时,我关注的就是那些人,或谓之小人物。当底层流行时,我笔下的人物生活中的地位和身份没有变。当底层被某些批评家诟病时,我笔下的人物仍是边缘群体。这没办法,除非我不写作。我不因底层叙事热觉得赶上了潮流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批评家的批评而躲避、苦恼。那和我没关系,我说过进入到作品中,人物没大小之分,没底层与高层之分。当然,我在写作中也力图避免被几乎大众化了的声音覆盖。比如苦难,底层有,但哪个群体的人没有呢?形式不同罢了。我不回避,但苦难并不是底层最突出的特征,把苦难与底层划等号是滑稽的,是某些人的想象。以至于许多作品为苦难而制造苦难。本来我不回避,可面对蜂涌的苦难,我躲开了。再如贫困,也是过度的想象与制造。我在一个创作谈中说:“乡村这个词一度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今天,它已发生了细微却坚硬的变化。贫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则显得尤为突出。困惑、困苦、困难。尽你的想象,不管穷到什么程度,总能适应,这种适应能力似乎与生俱来。面对困则没有抵御与适应的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同样,如果困被更多的目光注视,我会躲开。
金赫楠:我们来谈一谈《一棵树的生长方式》。它被评家提及的并不多,也许是因为它的整体调子并不符合当下流行的所谓底层叙事的主旋律。但作为一个读者和研究者,我是很偏爱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姚洞洞遭受着命运最无情的压迫,他的成长充满着失意甚至屈辱。最终,被压迫到最低点的姚洞洞开始了他对命运决绝的反抗。这种反抗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报复情结,是精心策划之后的机关算尽和步步为营;当他牺牲了自己甚至家人的日常幸福,当他把宿敌逼进了绝境,始自维持生存与挽回尊严的抗争,最终沦为快意恩仇的恶作剧。
你之前和之后的大部分作品中,也都贯穿着小人物对于命运的抗争,不论是麦子、丁大山那种沉默的坚韧,还是吴响、左石、罗盘那种一根筋式地执著,甚至荷子式的近乎疯狂的歇斯底里,这些表面看上去刨根问底甚至有些极端的行为,都是随性而发的,没有什么计划性,且都是心存善念的,歇斯底里的背后不具有破坏性,最终目的也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当姚洞洞从一个受虐者变成一个施虐者,当始自生活需要的反抗和挣扎一步步变成他的生活本身,我们从姚洞洞身上看到了底层世界的另外一种性 格:一种狡黠、机巧,一种强大的忍耐力以及 随之而来的巨大的爆发力。种种爆发本来是有合理性的,但是一旦偏执地走下去、也会 渐渐生出恶意与破坏性——我把它称之为“反抗溢出”:溢出了它能够控制的范围,溢出了它原本的合理的价值。我很好奇的是, 作为这个人物的创作者,这里面寄托了你对底层世界怎样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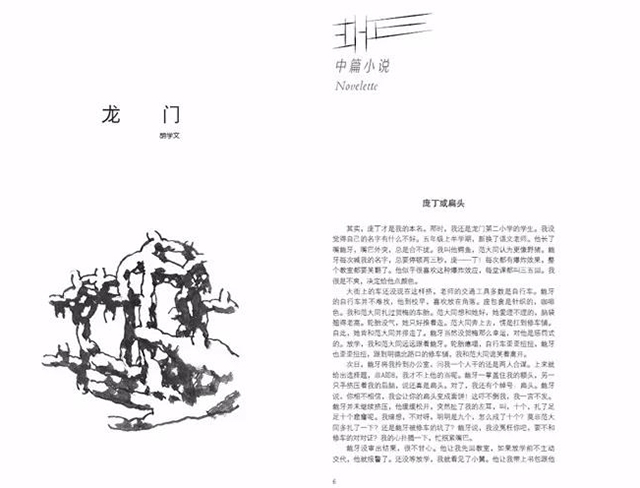
▲胡学文新作《龙门》刊载于《花城》2018年第3期
胡学文:我的所有人物都来自身边的生活。这篇小说来自我对童年乡村生活的一次回望。姚洞洞,说实话,这也是我自己偏爱的一个人物。你的偏爱,我想还是来自评论家的兴趣点,按你的话说,这个人物足够复杂, 可以提供更多阐释的空间,你关于姚洞洞的种种分析,有些的确也是我想表达的,有些却是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当然,好小说其实就是作家与批评家共同最终完成的。在我看来,姚洞洞身上携带着一种乡村智慧:在现实中,一个人不得不顾忌着什么,比如地位卑微者,可能不敢大声说笑,走路不敢直腰,眉眼不敢放肆,这也许是外界的重压使然。但没有什么权力或重压能深入其内心,至少还没到那个程度,还保持着心的自由,智慧的绽放。而且,现实越是逼仄,那智慧越有光彩。在我生活的乡村,就有这样的人物。我对这种智慧充满兴趣,想要去探究它来自哪里,会对人物和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金赫楠:你笔下那么多的反抗者,最后大都还是陷落在悲剧的结局里,好像只有姚洞洞取得了胜利——毕竟,他漫长的复仇最后实现了。但是取得胜利的姚洞洞,并没有得到自己预想当中的痛快淋漓,而是陷入了内心的恐惧与虚无。我的感觉就是,面对这个唯一“成功”的人物,你在叙事中没有直接评判,而是字里行间夹杂着质疑。对姚洞洞式反抗以及最终的所谓成功,你的态度是矛盾的。
胡学文:的确是矛盾的。我对姚洞洞的情感其实挺复杂的,他身上所体现的生存智慧吸引我,但是对这种智慧除了感叹之外, 我也觉得似乎还应该有一种警惕。这可能也就是对你所说“溢出”的警惕。在实际的写作中。这个人物被我给写失控了,我本来想让姚洞洞最后体面地站在那里,可是,最为一个赢家,他失去了赢家的气度。
金赫楠:人物自身的逻辑,战胜了作家的主观预设,写小说往往就是这样。不知道你是否留心,几年来的底层写作中,还有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因为贫穷、因为困苦,因为容易受到来自外部的欺辱与伤害,所以身处底层的人在丧失了资源占有上的优势之后,却被作家们赋予了道德上的优越感。姚洞洞这个人物的塑造,对这种想当然的道德优越感也是一个挑战。
胡学文:这还是属于评论家的发现。我在写作的时候,人物就是人物,他的性格也许很独特,但也是混沌的,他的举动是随着性格而发生的。人物出来之后,任由评论家寻找和分析吧。
二
金赫楠:你的小人物谱系中有这样一些人:老实得有些窝囊,善良得稍嫌软弱,苛求平安的同时难免怯懦,渴望摆脱贫穷、卑贱的努力中附带着个人主义,身处卑微庸常之中坚守着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在一次次的失望和伤害之后,主人公们仍就没有泯灭自己内心深处的善良,沉默地,也是执拗地坚守着人生的道德底线,坚守着自己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与努力。不过,这样的人物性格,在你的小说中其实并不多。我看到更多的,是另外一幕幕来自弱者的强势反抗。回头看看, 你这些年的小说中,其实一直贯穿着一这样几个关键词:刨根问底、一根筋、追寻。除了上述《飞翔的女人》《麦子的盖头》《命案高悬》《土炕与野草》《失耳》《像水一样柔软》《谁吃了我的麦子》《一个人和一条路》等等,以及最近的这篇《谎役》,在这些小说中,当人物遭遇到命运的残酷时,都会迸发出一种与自身处境看似不相符的强大力量去进行抗争,执著地、执拗地,以一根筋式的信念支撑着一种刨根问底的追寻到头、坚持到底。而这些追寻和坚持又往往沿着相似的轨迹走进了相似的结局。
胡学文:“刨根问底”和“一根筋”,被贴上这样的标签,我基本上是不喜欢也不反对。对于阅读小说的人来说,可能我的那些人物确实是一根筋,什么事情都一竿子捅到底,非寻个水落石出不可。我不是有意为之, 就是写着写着人物和情节就成了这样。非要仔细回想创作过程的话,我承认在写作初期,这样写有叙事策略上的考虑,比较容易实现紧锣密鼓的叙事节奏和跌宕起伏的情节相扣,人物性格也在情节的推进当中更鲜明。但是在后来的写作中,就与叙事策略无关了。可能因为我喜欢有韧性的人,所以往往努力挖掘并放大了这种韧性,所以人物看起来都有一根筋。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他自己坚守或者坚持的东西,人生不也就是一个不断追寻的过程吗?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追求,各种方式的追求,我只是因为自己的偏好而放大了其中的某一点。
金赫楠:大家都强调你这个一根筋,其实倒不是说它不好。这些人物,为当下文坛的叙事,贡献了一种对于人物性格的发现与体恤。到这里,我得插一句,因为突然意识到,其实刘好、马兑这些看似沉默软弱的人, 也不是一味逆来顺受,他们的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原生态的质朴与善良,在磨难与艰辛面前,守住一份善良,心存一些温厚,坚持一丝理想,这本身也是一种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是以一种柔弱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更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明进步和发展的最内在的呼唤和坚实的基础,是对残酷现实看似软弱其实内劲十足的长久抵抗。
回来再说这一根筋。对一直跟踪你的创作进行阅读的人来说,读多了,会对这种刨根问底的追寻产生过分的熟悉感:那种不顾一切、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坚持与执拗,那种一根筋式的刨根问底,笼罩在胡学文多篇小说当中,以至于有段时间我看到你的新作时从情节到人物不免略有似曾相识之感。
胡学文:我不过是呈现了这种追寻的艰难。我是个悲观的人,如果笔下的人和我一样悲观,不止是人物没有出路,我也会绝望的。也许没什么结果,但在追寻的过程中,我让人物也让自己看到希望。这些年我在写小说的时候确实越来越开始注重对心理的描写。但是,其实我并不认为,注重人物内心的描写就一定比关注人物的外部行为更高级。叙述的着力点侧重于什么地方,这是作家的喜好,也和写作时的叙述内容和所选择的叙事策略相关。写人物的外部行为,比如动作、语言,其实仍然可以传递出人物的心理变化,很多时候这样可能比直接写心理更有难度,所谓“不着一字尽风流”。
金赫楠:我同意你关于写外写内的看法。不过,具体到你近些年的创作,我仍然认为“由外转内”是一个突破和进步。还有一个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中篇《虬枝引》,初读后我很是惊讶,一度还又翻回到首页来再次确认作者是否为我所熟悉的胡学文。这是一个关于外出打工者归乡的故事,但是你写得很魔幻——是的,我使用了这样一个原本和你的创作不着边际的词语——魔幻:主人公乔风,一个外出打工的男人,回乡与妻子商议离婚,却在回乡的路上发现自己的村庄消失了。于是他放下了原本回乡的目的,一门心思地开始了对自己村庄的寻找与重建,但是最后一觉醒来,发现在那曾经熟悉的一切终究还是回不来了,他也因此只能永远走在回乡的路上却回不到家了。
胡学文:评论家们总是认为我的小说很实,甚至是太实。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却也因此多少有了想要做些改变的跃跃欲试。不是都说我太“实”吗?那我就写一 个“虚”一点的。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其实是满心苍凉的,按你的话说,《虬枝引》无论使用了一个怎样魔幻的架构,其创作灵感当然还是来自现实生活。你知道,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身边也有很多这样来自乡间、现居城市的亲戚和老乡,我发现每每提到自己现在住所的时候 ,他们的表述都不是“家”,只是说回什么什么地方去;而只有提到自己的乡村或者乡村所在的地域,才会使用“回家”这样的词。这种“虚”的确是我刻意追求刻意营造的,但我并不是随便逮住一篇小说就迫不及待地“虚无”起来。是对故乡的思考和对另外一种叙事策略的期待,碰撞出了这样的一篇《虬枝引》。
没有一个作家不想超越自己,问题是怎么超越,是否能超越?也许自己认为超越了, 可那种超越并非有意义。但不改变是不行的。我不知道所做的努力会是什么结果,方向也不是很明确,就像勘矿一样,这儿测测, 那儿试试。
刊载于《小说评论》201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