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小词、吴越对谈:写作是我在打开心扉说最私房的密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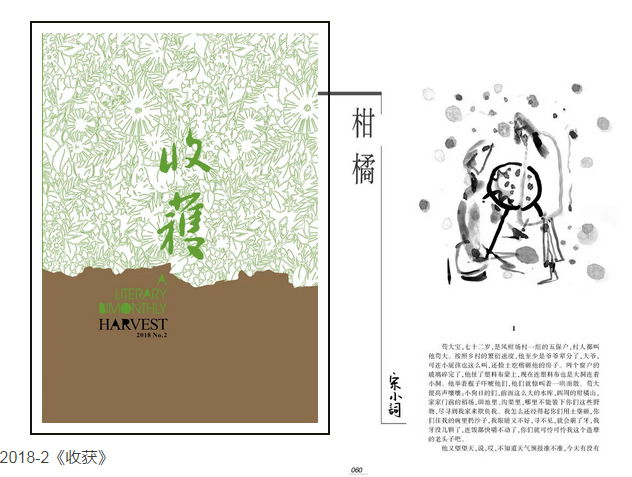
柑橘(宋小词)
凤柑场村里的苟大宝把整个青春都奉献给了水库和柑橘山的建设,他以为农村的集体道路会一直走下去,但没想到八十年代农村实行承包,人单势弱的他被剔除,为了补偿,他变成了五保户。时至晚年,潦倒失意的苟大宝遇上一个被人丢弃的年轻傻女,他视为女儿收留照顾。但村里留守的男人却打起了傻女的主意,苟大宝为了讨回自己与傻女的公道,得罪了村支书和村里所有人,日子处在逼仄狭窄的夹缝中,后来傻女怀孕,村委与村人拒不接纳,逼其堕胎,老人心生怜悯,在柑橘成熟的季节中,他们的命运走向了绝境
写作是我在打开心扉说最私房的密语
——从《柑橘》说开去
宋小词vs吴越
吴越:小词你好。对于编辑来说,作品就是作者的投名状。一个出色、特别的作品,会为它的作者引来无条件的尊敬——无论这位作者此前是不是有名,与编辑有没有交情。你的《直立行走》《太阳照在镜子上》《血盆经》等就是这样为作者挣来响亮面子的作品。先说城市题材,你对城市中人际景观的观看与把握,幽微而独到,表达手法上,泼辣而有味。《直立行走》一开头就抓住了人,杨双福与周午马开钟点房后去淋浴,“忽然感到羞耻,觉得自己像周午马的一只夜壶”,又狠又准,一个乡下女子与城市贫民之间将爱情挤榨到几乎为零的利益联姻也就在这样的譬喻中找到了自己的调性。《太阳照在镜子上》是我尤其喜爱的一个中篇,同父异母的两姐妹陶平和陶安,隔膜中隐含着恨意的历史关系,任性而美丽的妹妹带着孩子逃离婚姻,投奔姐姐,姐姐则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曾经发生在自己童年中的忽略与抛弃,她们的血缘关系如同“太阳照在镜子上”又折射到自身,经过一番曲折,消耗了许多热量,最终得到某种程度的确认,但妹妹却用她的生命告诉姐姐,也告诉全世界,什么是“活着”。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爆发-平复-再爆发的故事中,大量场景发生在姐姐的屋子里,“室内戏”一幕一幕,每一幕都完成了它在“核聚变”过程中的使命,经得起细读和重读。总之,你有一支非常准确的工笔,又装上了方言的墨水,庄谐得当,活灵活现,按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会写”、“有生活”。能否展开谈谈你如何训练、养育自己的语言和叙述的?
宋小词:谢谢你对我的抬爱,让我所写的文字在你的叙述里闪闪发光,这是对我的一种鼓励。谢谢你提的这个问题,让我有机会叙述我心底的一个小癖好,你知道吗,我每天都会跟自己做一个游戏,当我看到某个令我动容的场景时,我就会在心里做一番描述,我会给自己出题,如果是写作,要如何写才能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有时候我在等公交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认真感受城市发出的各种复杂的声音,这些声音该要如何呈现才最生动最准确,那些带着急刹的公交车它们停靠在站台时是什么样子,那些慌乱过马路的人们他们皮鞋踏着地面的声音像什么,如果我用炸豆子来形容的话,形象不形象,还有自己遭遇的一些事情,当你讲述给朋友的时候,怎么讲,才能还原其情状。走一条路,一路上之所见所闻,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做一番描述。这些都是一些很细微的,不足以向外人道的一些笨功夫。凡是涉及到说话和文字表达的都可以作为我日常的一种训练。而且有时候你身边朋友的讲话,时不时也会蹦出语言的金子,这些金子我都会一一将他们捡进我自己的宝库里。你也说过,我很擅长用方言,是的,对于我家乡的很多方言,土话,我都会细细琢磨,我有时候觉得有些方言就像萤火虫一样,它有一种光芒,它比稳重的书面用语或是普通话更有嚼头,更有味道。比方,我们那里说扇了一巴掌,不说扇,说铲,我觉得这个铲就比扇更有劲。像这些语言我都会收集起来,然后进行选择提炼,不滥用,关键时候用一下,会更有味。然后日常的收集储存,阅读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琢磨那些对自己味口的文字,看看它们的内部藏有什么样的魔力。从经典的文艺作品和日常生活中汲取养分,然后与自己的土壤进行融合,慢慢让其成为自己的武器。而且就像你说的,养育,养育是一种慢功夫,要一点一点培养。这些都是从日积月累中和有心中得来。
吴越:不知不觉中,我把你视为继池莉、方方等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主义”、“汉派小说”之脉传的又一女作家。因而我对你的城市题材小说颇怀期待。其实早先我在看到你的《直立行走》和《太阳照在镜子上》时,以为你近来的写作已经主要转移到了城市题材上,不料你拿出的新作《柑橘》是实实在在地写农村的,可见你还在使“双枪”。小说中的时间将近一年,读者也跟着你体验了柑橘树培育养护的四季,而柑橘山,养鱼塘,山间公路……这些物事被你一写,像是获得了新的生命气息。让我想起你之前的作品《血盆经》,它写的是乡村里一个无依无傍的少年郎去学做个小道士的历程,先不谈情节与主题,这样的小说如果没有大量准确、丰富、迷人的细节,譬如你所细细临摹的乡村道场的风俗、科仪等,是无法写成的。新作《柑橘》也是如此,从我的角度看,你写农村的小说语言上更放松,触觉更敏感,视野的边际更广大——而有数得很。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待写作题材这个话题?你又如何看待所生活过的城市与乡村?
宋小词:你所说的写作题材,我个人觉得这取决于写作者个人,一个写作者经历过什么,有过些什么深刻的人生体验,阅读过哪些作品,研究过哪些领域,接触过什么人,从事过什么的职业,遭遇过什么样的事件,行走过哪些地方,思考过哪些问题,有过什么样的感悟,这些都会一一沉淀在写作者的心里,等着岁月将它们融化在个人的感受阅历之中,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写作者的写作题材。像乡村和乡村女性在城市的生活是我的写作题材一样,因为我个人有乡村生活的深厚基础,知道很多乡村的故事,懂得乡村人的喜怒哀乐,懂得乡村生活的禁忌,我写城市,也写的是城市里的乡村女性,因为我本人也是这样的人,我接触的很多也是这样的人,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熟悉的,我能细腻的体验她们各种幽微复杂的情感,因为熟悉,写作起来就不感到膈应。如果让我写一个城市白富美,或是官场赌场之类题材的小说,我肯定是不知道该从那里下笔。我是一个蠢笨又很愚钝的写作者,我的写作必须要从我自己体验和经历的东西来写。就像我当记者时,其实有很多会议稿件,一些有经验的老记者不用去参加,也能写出来,但是我不行,无论是多么老腔调老套路的会议或是典礼,我都要亲临现场去实地聆听感受一番,才能写出稿件来,否则我一个字也憋不出来,为此,连我的领导都说我是个很呆板不灵活的人。我承认这种评价,这是我的短板,但我只能接受这个短板。我也知道这个短板于我的创作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暴露自己,所以我一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是很隐秘的,写作是我在打开心扉说最私房的密语,这使我感到羞耻也感到恐慌,可我又不得不如此,因为我觉得写作更需要坦诚。还有就是有时一个好的写作题材会毁在一个平庸写作者的手里,有时一个高超的写作者会把一个很平庸的写作题材挖掘出深刻的意义来。其实说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有什么样的写作者就有什么样的写作题材。
对于如何看待我所生活过的城市与乡村,这也是我近期所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从乡村出来,如今生活在城市里,我有时候会在内心问我自己,我是城市人吗?不是的,从外部说我拥有了城市的户口,拥有了城市的房子,拥有了城市的工作,从形式上说我是城市人,但从我口中浓重的乡音,从我的生活方式,从我的思维观点,从我的待人接物,这些内容上来说,我还是属于乡村的。我不过是居住在城里的乡下人而已,但我想我的孩子应该是正宗的城里人,这个小小城里人,是我和我爱人这两个居住在城里的乡下人孕育出来的,我的父母和我爱人的父母,是泥巴腿子孕育出了我和我爱人这两个半泥腿子,这样看,一个农村人想要真正成为城里人最起码要有两代人或是三代人的付出和努力。没有哪一个乡村人不向往城市,像我们这种出身在乡村的孩子,当你的家长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追求,那么赋予你的责任就是要努力成为城市人,城市带着光环,象征着文明、富有是龙门,是天堂。城市与乡村向来就是两个世界,城市越发达,乡村就越虚弱,城市越繁华,乡村就越死寂。而对于我个人来说,乡村的生活并无诗意,城市的生活也没有多少荣光,我处于尴尬的夹缝中。
吴越: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在你深植于生活的工笔之上,则是一种大块之气,悲天悯人。这才是讲故事而至于成立小说的根本,也是属于你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无论是写城市题材还是乡村题材,你都隐隐会写到那些卑微、屈辱、忍耐中的人如何付出沉重的代价讨回他们的尊严,这似乎是一个情感范式。《柑橘》写一位乡村孤老苟大宝,本来已经屈服于命运,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死后能有邻人送个终,不要任虫蚁腐烂咬噬于老屋之中。因为误捡了一个智力低下的女子,引起一连串欺凌(包含乡人的“平庸之恶”),而他在讨要公道的路上愈走愈远……苟大宝最后的结局,与《太阳照在镜子上》中的妹妹陶安,《祝你好运》中的残废半截人何志平,有某种类似性,都是求告无门自我了断。而《开屏》结尾,秦玉朵考虑从书房跳下去,“但她还是收住了自己,她不能用仅有一次的生命来跟生活对抗”和《直立行走》的最后,杨双福被周午马当成入室贼痛击倒地,似也可视为是上述范式的一个变奏。我想说什么呢?阅读你的这些小说的过程中,就像在隧道中慢慢擦亮了微弱火光,让人对自己的卑微也生出某种敬意,被火光映在壁上的影子陡然也高大起来,会有一些庄正的东西渗入心底。但这些人物最终的命运,却让火光再度熄灭。作家是他笔下世界的造物主,你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们都不是“光明”的故事?结合你推崇的作家作品,说说你对现实、对人性、对悲剧的认识吧。
宋小词:近来我特别喜欢杰克伦敦和安妮普鲁的小说,他们的小说都有一种虎狼之气,粗糙而坚硬的质感,汹涌而热烈的气势。他们对现实对人性的揭露残酷而深刻。他们的写作告诉我写作是需要胆量的,写作需要拿出格斗士的气概,面对纷繁复杂,瞬息多变的现实,面对深不可测,九曲回肠幽微如迷津一样的人性,每一个写作者身体里都要有一根定海神针,要有勇气去揭露去审视去批判。我觉得真正的写作者都不会是软弱者,他们用一双冷静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用敏感而丰富的神经去感受这个世界,力求拨开重重迷雾,力求抵达真实的境地,为人们拨开伪装的华丽外表。对于人性的光芒要极力赞美,对于人性的黑暗丑陋要坚决撕开,让其裸露。对于悲剧,我很赞同鲁迅先生的观点,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眼见很多美好很多天真很多善良都被世间瓦解殆尽了,我看到我的很多亲戚朋友他们都在自己的方寸之地里操劳挣扎,妥协与反抗,那一点点肤浅的活着的快乐不足以消除与生俱来的忧虑与恐慌。有时候我觉得这尘世间就像是压在人身上的一座大山,各种现实、制度、伦理、条条框框,像一张网一样把我们紧紧束缚,敏感的我总是时时感觉到被压迫,被挤压,被折磨,被盘剥,被煎熬,我们被裹挟着扭曲着矛盾着前进,有时候我们需要出卖一些尊严和美好的东西,来获得生存的空间,由此,我们时常感觉到罪恶,我们一边救赎一边犯罪,我们的肉体与灵魂一直处于深深的不安中,然而我们一生抗争,却最终也逃不开衰老与死亡。我对生活对人类的绝望感似乎是从胎里带来的,无论这阳光多么灿烂,无论这花开的多么热闹,对我来说都是假象,我依然看不见人生的希望。
吴越:此时正是狗年春节,大年初一,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你是否在酝酿下一部小说,或是已经忙里偷闲写了起来。写作不易,为母不易,一个同时是写作者与母亲的女性更不易了。我时常能感受到你生活中的烟火气,但艰苦写作的那一面你是不会轻易示人的。有了孩子之后,写作风格和写作作息上是否有变化?
宋小词:有了孩子之后,写作作息上肯定是变了。首先写作时间被大量挤占,整颗心都牵挂着孩子,孩子健健康康的时候,心情还稍微松缓一点,一有个头疼脑热,咳嗽流鼻涕的时候,整个人就五心不定,干什么都干不了,只能一门心思去关注孩子。基本上孩子在家我是干不了事情的,一般孩子出去玩和孩子睡觉以后才是我的阅读和写作的时间。
对于有了孩子写作风格有没有变化,我想应该有吧,因为我能明显感觉到有了孩子后,我的心胸宽广多了,以前很多事我都睚眦必报,现在真的没有了,因为有了孩子,我对这个世界还是充满了很多善念,对很多身外的物质利益性的东西淡泊了许多。以前在外面碰到事情喜欢去跟人争论,但有了孩子后,很奇怪,最害怕与人针锋相对了,总是选择自己吃亏,让一让算了。对人世多了一些包容,也多了一份理解,凡事也愿意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替别人去思考一下,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有了孩子后,我感觉我的心肠一天比一天柔软,肩膀一天比一天坚硬,像是脱胎换骨一样。连我自己的风格都变了,我想我写作的风格也一定变了吧。
吴越:我偶尔知道,你本人又还经过一回迁移,似乎过着武汉和南昌的“双城”生活,平时也见你在朋友圈中晒些南昌当地的风俗和吃食,想必你正在融入当地的生活。这些变动对你的创作的影响是怎样?
宋小词:哦,是的,2015年之前我是没有稳定工作的,2015年南昌市文联把我作为高精尖人才引进为了专业作家,进入了体制内,这使我的生活有了一个基本的保障,让我写作的时候有了一颗较为安稳的心。目前因为孩子还小,爱人单位也都在武汉,一时难以全部挪过去,所以单位领导对我十分宽容,允许我这样的“双城”生活。我每一周总有一两天会经历武汉到南昌,又从南昌返回到武汉这样一个过程。2016年我把小孩和公婆也带到南昌去生活了一整年,起先很不适应,但渐渐地也适应了,我也挺喜欢南昌的,对于这样一座能接纳我包容我的城市,我没有理由不去喜欢她,只是真正要融入进这座城市还需要足够的时间。“双城”对我创作的影响肯定是有的,这拓宽了我的写作视线,人生的变动,起起伏伏都会给写作者不一样的经历和感受,这些都会刺激到写作者丰富而敏感的体验神经,这些都会有形无形地影响创作者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