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小说是个体面对整个世界言说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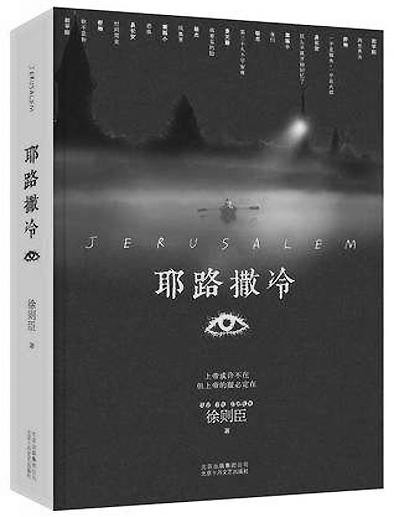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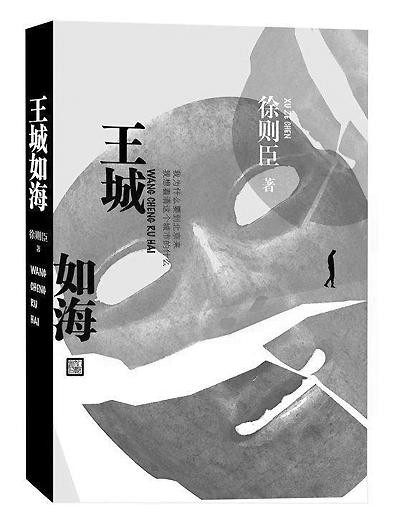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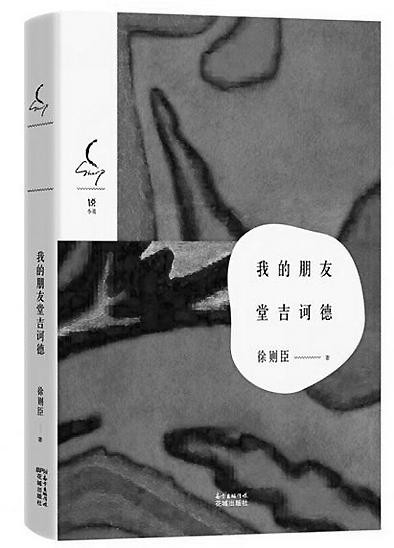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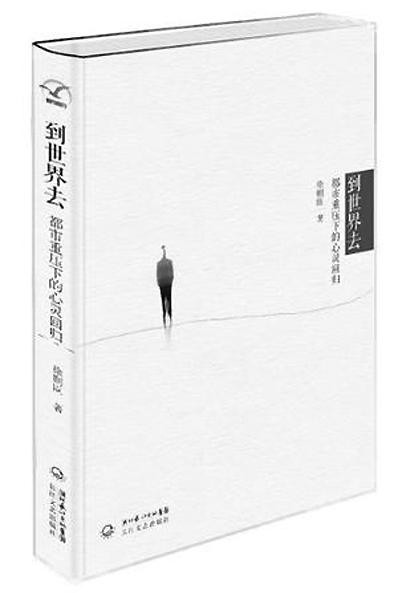
必须找到经得起推敲的结构,既可以充分地自我表达,又能区别于他人
记者:读《耶路撒冷》,先是翻到扉页上的一句话: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这其实也是其中一个专栏的题名。在我感觉里,这句话像给小说定了一个基调,或者说隐含了你一个写作的理由。如果说这部小说包含了为一代人写心灵史的意图,这样的回忆似乎还早了一点,毕竟1970一代还算年轻。所以自然会引人发问,为何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但它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了我一个提醒。“70后”作家居多已过不惑之年,像你,还有其他一些同时代作家都写了十多年,确乎可以对自己的写作做个回望了。
徐则臣:出版社选了这句话放在扉页上,有他们的考虑。准备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有朋友也说,写“70后”太早了。我觉得不早。原因是,我们都已经开始回忆了。早与不早,跟年龄没关系,跟你的经历,跟故乡的失去,还有整个世界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身处故乡,局内人,即使故乡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你未见得会意识到,可能完全产生不了回忆,因为你在那个变化流中,变化是你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但当你离开再返回,你所熟悉的都已消失或者是行将消失的时候,你会产生回忆,必须回忆,要不你可能连仅剩下的那点东西都抓不着了。是时候了,再迟你可能就来不及了。
记者:我感觉这部小说章节的编排,似乎就体现出了回忆的特点。怎么说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回忆该是线性的,从此刻起沿着某种路径一点点往回追溯。但我觉得回忆或许更像是一个同心圆,围绕一个或几个中心,像涟漪般一圈圈扩散开去。
徐则臣:这本书首尾相接,是一个圆:它从一个点出发,又绕了回来。这可能比较合乎我们文化里循环的理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循环也的确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开始我没刻意这么想,但写着写着,就成这样了。可以想一下:这世界就是这样,开始我们都想往外跑,离开故乡到世界去,但后来你会发现故乡就是世界,你绕一圈又回来了。小说也相应呈现出这样一个圆形结构。
记者:想必你为找到这个结构花了很多心思。
徐则臣:真花了不少时间。这小说写了六年,前三年主要在找结构。就像现在要写一部有关运河的小说《北上》,万事俱备,就是结构差那么一点意思,动不了笔,所以中间又写了《王城如海》和《青云谷童话》。必须找到一个经得起推敲的好结构,既可以充分表达出我想要的东西,又能跟别人区别开来。
记者:说到结构,我倒想起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说过,在情节、人物、主题、形式和结构这五个元素里面,只有结构还有不少创新的空间。我也同样想起作家张炜曾表示,结构是最少创新空间的。这是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当然我更想探讨的是,仅只是结构的创新,是否足以让你的创作跟别人不一样?
徐则臣:区别应该是全方位的,所以每一个角落都不能轻易地懈怠和放弃。结构非常重要。其一,你要结构这世界,就得找到与这个世界同构的一个形式。其二,写一个中短篇,甚至一个小长篇,就好比盖一间房子,你可以没有特别详细的构思,就跟着感觉走,完全可以。唯手熟尔,够了。写《王城如海》我就没下那么多功夫。但一个大长篇,不仅是一间房子,而是一座楼、一个建筑群。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人看完《耶路撒冷》说,小说一直写到结尾气都没断掉,后劲源源不断,滚滚而来。我把这当成是赞扬和鼓励。这固然是写作经年训练的结果,其实跟结构也有相当大关系。结构立住了,关键处你不会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你可以从容地转向局部,让每块砖、每块石头都结结实实在它们该在的地方,多好。这就是结构的意义。
记者:小说说到底是时空的艺术,结构关乎空间,结构安排好了,相当于给时间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场所。
徐则臣:对,结构科学,时间处理起来就方便了。所以,我愿意花一半的时间先来解决结构问题。长篇,尤其是大长篇,必须在故事、细节、想法、结构诸方面,尽你所能,全方位地提供新东西,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耶路撒冷》之后再写小说,我没再出过这样的情况:某个题材短篇放不下,那就写成中篇吧,中篇放不下,就写成长篇吧。短中长都有它匹配的尺度和结构。理想的结构找起来的确有点麻烦,但功夫到了,你力所能及处,老天应该不会辜负你。一部伟大的小说,结构极少是平庸的。
记者:结构与空间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像约克纳帕塔法这样一个虚拟的空间,是否也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福克纳小说各个不同的结构艺术?现代小说之前,无论中西方一些古典小说,尤其是流浪汉小说,人物在空间里流动,结构是比较单一的。当空间确定以后,小说结构倒越来越复杂、立体了。
徐则臣:对现代小说来说,更重要的命题是时间。当然空间也很重要,它是横向的、广阔的、铺展开来的,天然地和“规模”、“丰富”等词连在一起。而时间是纵向的、幽深的、尖锐的。但时间往往没有空间讨好;空间更容易立竿见影,在短时间内出效果。如果把约克纳帕塔法那样的地域,理解为“精神故乡”,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每个作家都需要这样一个根据地,一提笔,就会不由自主地往印象最深、最理解、最熟悉也最有感觉的地方跑。区别在于,有的作家始终守着同一个地名不离不弃,有的作家则是打一枪换一个地名。忠贞不渝显然要付出代价,那就是得常常费尽心思去全盘考虑,保证这地方相对稳定,包括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山高水长,不能这个小说里说“花街”在温带,边上有条运河,到了那个小说里又说,它跑热带去了,周围全是高山,长满了棕榈和椰子树。
记者:你的“花街”不断容纳进新的内容,以至于“花街”越走越长。
徐则臣:没错。在这里,人物、时间、故事也得注意连贯性,细节也要经得起推敲。在同一个根据地上,越往后写难度越大,它逼着你越站越高,越看越远。作家之所以愿意受这种折磨,一是跟他们愿意或者只能回到熟悉的地方,另一个,跟文学的野心有关,他们要经营一个独立的世界,福记的、马记的、莫记的、童记的、贾记的。恐怕有点野心的作家都想整出这么个地盘,大的蔚然成就王国,小的也得弄出个大观园来。我写一条街、一个地方,所谓的野心固然有,也是不想把自己弄得太麻烦,就像出箱包多了麻烦,就一两个,大小零碎都塞进去,上下车走路都方便。
我极少在小说里大规模地运用偶然性和戏剧冲突,这次逮着机会,狠狠地尝试了一把
记者:你迄今最“当下”的小说,或许该是《王城如海》了。因为小说触及这些年正在发生,也备受关注的雾霾问题。这部小说在每一个章节里,嵌进去话剧《城市启示录》的一个部分,话剧的各个部分合在一起可以说是和正文构成互文或补充关系的一出完整的话剧。有意思的是,整部小说也有着很强的戏剧性。
徐则臣:最初想写一个关于北京的话剧剧本。尝试过,很多东西处理不好,还是小说更顺手。那我就想,如果把小说戏剧化、剧本化呢,不只是在小说里加一个片段、引进戏剧的形式,还要把戏剧的一些要素,偶然性、戏剧冲突,都移植进去,结果就这样了。我极少在小说里大规模地运用偶然性和戏剧冲突,这次逮着机会,狠狠地尝试了一把。
记者:小说里的确有很多的偶然性,偶然性会不会让人感觉在某些地方缺乏说服力?毕竟,小说里的偶然性,要有足够说服力的话,也因为其中包含了必然性。
徐则臣:在一部小说里动用那么多戏剧性因素,已经不只是表现方式的问题了,还是一个关于戏剧的方法论问题。比如《雷雨》,一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一件事牵出另一件事,互为因果,跟多米诺骨牌似的,就一路倒下去了。有个问题可以探讨:在戏剧里,大量运用戏剧手段,是成立的,你不会觉得唐突冒犯。为什么在一个小说里就不行?我当时就想试一试,把未竟的戏剧梦想,放到小说里来实现。
记者:那是不是说,从写作的角度看,你先得假设一些巧合都是成立的,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的。然后一步步论证这些巧合,这些事它怎么就发生了。
徐则臣:写到每一个转折点我都会反复琢磨,这地方是不是完全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不会写。如果有可能,我就可以写。不管是小说里,还是生活里,总有很多命悬一线的时刻。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开头的假设,所有跟医生有关系的人,都失明了,就他老婆没有失明。不需要问为什么,你只要承认有这种可能就行了。再比如,心脏生在左侧,一刀刺下去人肯定就废了。但有些人就没事,他所有的器官都是反着长的。我有一个同学,体检的时候,把医生吓坏了,心脏找不着了。他的心脏长在右边。金庸小说里也有这样的人物。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确不该拿特例说事,但我想在这部小说里尝试一下。肯定不会一直这么干。
记者:问题是有人或许会问,小说的戏剧化,是不是非得由很多巧合来促成呢?尤其是小说的最后一章,就像是很多事在一天之间发生碰撞,然后瞬间爆发。
徐则臣: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这个结果往前倒推,能否成立?能成立就没问题。
小说结尾部分,整个戏剧冲突的时间很短,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一天之内发生的。为了这一刻的相遇和冲突,前面我草蛇灰线地铺垫了很多细节,把人物的后路一条条全给堵死了,让他们只有这一条道可以走。
记者:你能这么放开写,该是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写作的历练,变得更加自信了。上次在绍兴聊天,你说到读波拉尼奥的《2666》给你一种“如入无人之境”的感觉,我不知道你在写这般有一定探索性的小说时,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
徐则臣:波拉尼奥写《2666》,绝对是高度自信,什么都不管,真是信马由缰,爱怎么写怎么写。小说里仅凶杀案,一口气就罗列了几百个。这胆子也太大了,谁敢这么玩?但他就旁若无人地干了。看上去漫不经心,但漫不经心本身也可能就创造出了一种结构。写《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有不少人质疑,你怎么写怎么有问题。但现在,我要感谢这部小说,有些年轻作家跟我说,他们看了小说后很受鼓舞,胆子大了,因为小说也可以这么写。所以,文无定法,小说没什么确定的形式。什么是真理?成了就是真理,不成就是谬误,成王败寇。我们的问题是,在写之前只想着成,就没想过其实你不这么样写也可能会成。大家更愿意选择保险的路子。也没什么不对,但的确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
记者:有些作家在写作之前,想写作之外的东西太多了。
徐则臣:我们总想着写一个四面讨好、老少咸宜的东西。开始我也是,现在不管了,爱谁谁。《王城如海》这么短的篇幅,我用了一个复杂的结构,当然不是为了形式而花哨,这个形式是必须的,它对内容有意义,相辅相成,相互生发。
记者:我们谈到要不断给自己设置“写作的难度”,甚至于有作家还说“没有难度的写作是可耻的”。但写作的难度,是否只体现在不断变换形式,不断拓宽疆域。在同一个领域里深挖,不也同样能体现难度?
徐则臣:我很看重“写作的难度”,一直以此激励自己,也喜欢用这个标准来评价其他作家。写作是一个发现和创造的过程,失去了难度也就谈不上发现和创造,就成了伪写作。难度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有没有解决,能否解决好,更重要的在于,是否对过去的写作构成挑战,是否有勇往直前的胆量和信心,是否不断地将自己从众多写作中区别开来并最终确立出自己。在我看来,那些蜻蜓点水般到处攻城略地纵横驰骋的作家,打一枪换个地方,换个地方打一枪,恰恰是在逃避写作的难度,缺少对某一个和某几个领域的深度掘进。对摆脱不掉局限性的个体来说,存在无边界的写作吗?但也必须承认,很多作家的确也在通过形式和题材本身的变化,努力拓宽自身和我们共同的文学。凡事都不能绝对。
记者:没错。再是“如入无人之境”的写作,实际上也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写作有自信的同时,也得有自知。因为自知,才会更有自信。
徐则臣:我以前总会担心,一个东西写出来,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弄不好就会失败。问题是有哪部小说没毛病?没毛病就成功了吗?当真说起来,没毛病本身也是一个毛病,完美就是个陷阱。
不要以单一的声音去呈现这个世界,就算自我表达,也要尽力复调,尽量众声喧哗
记者:《耶路撒冷》和《王城如海》看似写的全然不同的两个题材,但从主题的层面看,又是特别相关的。说白了,前者说的是“到世界去”的问题,后者说的是“从世界回来”的问题。因为这两部小说,差不多也在同一个时期,所以有必要问问,你是不是在构思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设计?
徐则臣:真没有任何的设计,因为什么,在我看来,到世界去跟回故乡是一体两面的事,在我潜意识里,这两个东西是连在一块儿的。《耶路撒冷》之后,我就一直想写《北上》,沿运河从南到北。写不了,我就继续想《王城如海》的事。以我的习惯,一部长篇写到一半,就不必管它了,它的“大势”已成,可以自己走,你可以开始考虑另一部小说了。这大概是两者在问题意识上有所勾连的原因之一。
记者:“世界”可算得你的关键词。你不只是在小说里提,在散文随笔里也不断提到。《小说、世界和女作家林白》《 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方式》两篇随笔,主要就是探讨人、小说与世界之间的某种关系。
徐则臣:小说不是个多高深的东西,它就是作为个体的作家切入他所面对的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个体面对整个世界言说的方式。小说解决的就是个人与世界之间的问题。世界不是简单的现实、社会或者某某单一的东西,而是与个体有关的整个存在。存在主义、后现代等等,只是对世界的众多描述中的其中一种,它们有意义,在一定时间内也有效,但不是唯一的,世界在变,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之前已经有很多种理论上的描述,其后也一定还会有很多种描述。就目前而言,它对我的意义,主要是借助这样的理论部分地实现对世界的某些本质的认识,引发一些思考和发现,可能会作用于我的写作,也可能仅仅停留在思考的层面上。当然,理论本身也有可能是自足的,只在它自己的逻辑里才成立,就是一种智力游戏,这种时候,它玩的就是空转,对实践可能没什么意义。
记者:你似乎对理论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你对写作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体会,说你有一套相对自足的理论构架也不为过。以我的感觉,你是作家里面自我阐释能力特别强的,也是擅于阐释的评论家里面写作能力特别强的。
徐则臣:我当然谈不上什么理论构架,我写的就是自己的一些杂七杂八的想法。它们看起来有点一脉相承,是因为我有一个比较坚定的对理想中的好小说的想象。所有的想法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对那个好小说的描述和逼近。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处,但整体上这些想法是渐进的、相互修正和完善的。一个作家不可能完成了所有的写作才开始整理自己的写作理论,他会边写边想边实践,要实践出真知,要理论联系实践,互动着往前跑。
记者:我有时也想,作家在写作上是不是不妨糊涂一点,开个玩笑,作家自己都充分阐释了,就没评论家什么事了。其实,作家有很强的理论构建能力挺好,前提是能促进写作,而不是用理论把自己给框死了。更何况,写作和理论在一个作家身上并不总是并行不悖的,有时候反而会是相互背离的。
徐则臣:我觉得你的担忧,不是因为我在边写边总结自己的想法,而是担心我会画地为牢,把自己活生生地憋死在预设的写作理念里。这的确是我需要警惕的。在我的想象里,好小说是开放的,关于好小说的理论也是开放的,我希望我的思考也是开放的,这就意味着,当我的努力事与愿违时,我能够及时地反省和调整。不是最终非此即彼地服从哪一个,而是尽力找到最合理的那一条路。所以并行而悖并不可怕,恰恰是一帆风顺可能更糟糕,它会让你忘记反思这回事。
记者:没错,不管怎么说,作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总是好的。也因为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来一直有人提作家学者化的问题,我觉得这应该不是说要作家同时做一个评论家,或是要作家有大学问。如果作家学者化有必要的话,你觉得必要性在哪里?也不妨说说,有阐释能力,有理论基础对你自己的写作有何帮助?
徐则臣:在我看来,作家学者化的最重要一条是:你要有问题意识。你知道你写这个故事的意义和必要性在哪里。由此,你才会以文学的方式去研究问题、表达问题、解决问题。由此才会产生及物的文学,文学也正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至今的。作家的任务不仅仅是讲个好看的故事,故事漫山遍野,不需要一群人当个事儿专门去干。自我阐释说到底不重要,真要写得好,会有无数人帮你阐释,甚至你永远也想不出的东西都能掘地三尺给你找出来。学者化肯定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让你有问题意识,能够就某些重要的问题深入有效地思考下去,让你成为一个有脑子的作家。
你的世界观与别人真正区别开了,你的写作也必然成为独特的存在,但做到这样很难
记者:说“世界”都说到理论上去了,因为你在不少随笔文字里谈到对“世界”的理解。你还写了一篇《零距离想象世界》,挺有意思。感觉应该能代表你现在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一个角度,或某种方式。
徐则臣:这是写作面临的现实。现在的科学技术、网络这些东西,让世界上任意两点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我们处在一个地方,却要去想象它。叙述本身就是想象的一部分。你无论怎么描述,其实都包含了你对一个事物的想象。比如,我在北京写北京,就是一种零距离的写作,所以零距离是我们根本的处境。那么,我在零距离的情况下怎么写北京,就是我在小说里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由“世界”延伸开去,不妨谈谈世界观的问题。想到这个是因为想到,一个作家的写作该怎样在本质上与别人区别开来?对于初学写作者来说,模仿是不可避免的。反过来说,不同的作家写作很不相同,那不同又在哪呢?这关系到作家该有怎样的世界观,该怎样确立自己的风格的问题。
徐则臣:没错,模仿和超越,在我看来,关键在于是否形成了自己面对世界的独特方式。有自己的独特看法,必然要求与之契合的表达方式,别人谁也帮不了,模仿在这里是失效的。李敬泽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怎么写其实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你的世界观与别人真正区别开了,你的写作必然也会成为独特的存在。但做到这样很难,所以才会有“影响的焦虑”。总的来说,模仿在写作中是必要的,因为你得知道游戏的基本玩法,你得学习和借鉴,需要别人的光照亮你幽暗的角落,激发你的创造;其后,超越是自己的事。
记者:其实你已经“在世界上”了。这不只是说你有多种小说被翻译到国外,也不只是说你走了多少个国家,而是说从《耶路撒冷》,还有你的其他一些小说里,能感觉到你有了一种“世界意识”。当然我这么说,说实在我也不是很清楚“世界意识”到底指的什么。游历这么多国家后,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徐则臣:不知道别人在周游列国之后感受如何,这些年断断续续地在外面跑,慢慢地觉得好像开了第三只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开阔视野毋庸置疑。地域、种族和文化的差异带来看世界角度的不同,别一种和数种眼光可以补济我们相对单一和有限的思维。横看成岭侧成峰,世界有多复杂,取决于你有多少看取世界的角度。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我相信多一个角度总比少一个角度要好。诸多差异性的眼光可以补济,可以修正,可以提醒,最不济,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比照和参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有所本、有所执。世界观的变化必然带来文学观的变化。这些年我对文学的想法一直在调整,是否更加科学不敢说,但的确一直在变,说明持续有新东西在刺激,同时也在持续地反思、敞开、接纳、比较和确立新的自我。我以为这是好事。古巴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似乎很熟悉,但事实上可能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更陌生。到了美国,你会说,嗯,这就是美国;到古巴,你的感叹可能会是,啊,原来这才是古巴!
记者:视野日渐开阔以后,我想你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这句老生常谈,也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徐则臣:这句话,要放在什么条件上谈。首先,一个东西和另一个如果没有差异性,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想看一个东西的前提就是,我能从中获得不一样的东西,如果看来看去都差不离,你看一个就行,你自言自语就可以。但这个东西也得是世界的,得是大家能够接受的,这是理解的前提,也是大家能够相互交流的前提。所以,没有差异,就没有交流的需要。没有通约,就不存在理解的基础。两者很重要。我们不妨把文学比作一个分数,有分子、分母,我们通常认为文学的公约数更重要。但五分之二与七分之二的区别不在于分子,而在于分母。分子是分母之所以存在的前提,分子就代表的差异性。而在分子一样的情况下,能够区别自己的,确立自己的,则是分母的差异性。
记者:我们讲民族与世界的关系,隐含了写出一种既民族又世界的作品的渴望。不管怎样,我都觉得“70后”作家理当有这样的抱负。记得有一次张莉说到,“70后”作家生正逢时,他们在成长期看到改革开放前一些大事件的背影,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浪潮,他们是两边的资源都占了,理当肩负起更为重要的反映时代的责任。我可能记不准确,只是记得她说的大意。当然,换个角度看,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70后”作家生不逢时,他们好比被架在一个山岗上,虽然能看到两边的风景,却都没能深入到谷底,也就体会不到站在风暴中心的那种深入骨髓的体验。待到写作时,难免会有心有余力不足之感。事实上,要是碰到能力不相匹配的时候,写作上的雄心倒反而会有损于实际的创作。
徐则臣:我赞同张莉的结论,我也认为从理论上说,这一代作家应该不会让人失望。但在盖棺论定之前,不管多么强悍的逻辑都只能是推测。事实上,所有的正反面教材历史早给我们提供好了:看似生不逢时的一代人,没准最后冒出了几个大师;而那些在苍茫浩瀚的大时代里摸爬滚打过的,也可能最终烟消云散。也就是说,文学上其实是不讲概率的,大作家、大作品出来就出来了,出不来讲多少大道理都是白搭。身处其中,时代咱们没法再选了,剩下的就是各各努力,好自为之,看修为和运气了。
徐则臣,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社。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青云谷童话》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冯牧文学奖,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15年度中国青年领袖”。《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同名短篇小说集获CCTV“2016中国好书”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被评为“《亚洲周刊》2014年度十大小说”第一名,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六届香港“红楼梦奖”决审团奖、首届腾讯书院文学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德、英、日、韩、意、蒙、荷、俄、阿、西等十余种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