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当讲述成为抵抗遗忘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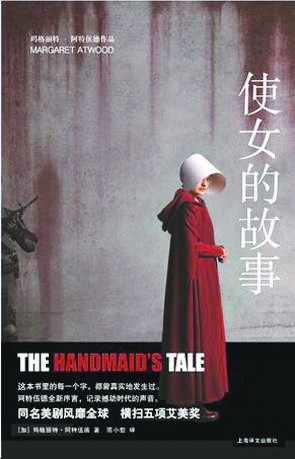
《使女的故事》[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 陈小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有些小说会让它的读者感到战栗,还有些则连作者本人都无法摆脱自己笔下世界的阴影——《使女的故事》便是这样一本书。1984年春天,当奥威尔预言过的时刻到来时,身处西柏林的阿特伍德开始写作这部在她看来“无异于一个冒险之举”的小说——读者是否能够相信,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权在一夜之间被推翻,变成了一个神权至上的独裁政体?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使女的故事”已经成了“女性反乌托邦文学”的代名词,甚至变为英语中一个常用的短语,用来指涉对女性极尽压迫的社会,尤其是强行控制女性生育自由的状况。2017年,随着同名电视剧集的热映,以及美国大选后特朗普政府对女性及其权益的一再贬抑,这部小说又再度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除了奥威尔的《1984》,熟悉西方反乌托邦文学传统的读者还会从中读到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的影子,阿特伍德也曾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类似的启发。在使女生活的国度里,20世纪末的美国面临着环境恶化导致的人口危机,健康出生的婴儿成了宝贵的国有资产。在一场没有明确定义的“大劫难”之后,美国发生了一场政变,建立了一个名为“基列国”的神权独裁统治。与任何等级制度分明的社会一样,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成了统治阶级独占的宝贵资产,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以“使女”的身份为指挥官和他们的妻子繁衍子嗣——但是她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使女们被剥夺了名字、身份、财产,沦为纯粹的生育机器,如果能够侥幸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则能够免于被送往隔离营或到殖民地清理核废料的下场——那里是上了年纪、无法生育或违背教义的“坏女人”的终点。
在使女以外,所有女性的生活都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按各自的功能被分门别类为夫人、马大(女仆)、经济太太、荡妇等,各自穿着的衣服颜色也凭身份而有所不同。尽管基列国的统治是一个父权制的建构,但男性也一样没能逃脱受害者的命运,他们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唯有特许阶层或立下战功的男人才有成婚的资格。无处不在的“眼目”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曾经的学校沦为“改造”使女的感化中心,充当教化工具的嬷嬷们不遗余力地向使女们灌输“新的正常”,而曾经的哈佛大学的围墙上挂满了违背基列国法律的死者的尸体。
刚开始写作这本书时,阿特伍德选择了主人公的名字作为小说的书名,“奥芙弗雷德”(Offred),即“弗雷德的”,意为她是那家大主教的私人财产;此外,这个名字也隐含了一个宗教献祭的受害者的意思(offered)。与剧集里不同,我们从始至终都不知道女主人公的真实姓名。按照阿特伍德的说法,那是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人都曾这样隐匿在了时间的褶皱里,沦为历史的注脚。
写作这本书时,阿特伍德谨慎地选择着自己的材料,留意不要将任何没有历史比照或现实影射的情节引入其中。除了提出“同样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在此时此地吗”这个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问题,她还试图通过这部作品,指出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已经在此地或他处成为现实的。如果说奥威尔的《1984》是对未来社会的推测,使女的世界则是对“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的轻微的反转”。我们很难不对电视剧里呈现的世界感同身受:迟迟不来的网约车、突然被冻结的信用卡、植入在使女耳后的电子定位器……没有一样不存在的科技,没有一个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细节,同样,没有想象的法律,也没有虚构的暴行。
电视剧上映初期,观众们都津津乐道于阿特伍德在其中客串的一个小配角。在那一幕里,她成了感化中心里的一个嬷嬷,毫不留情地给了女主角一巴掌,因为她迟疑着没有加入辱骂另一个叫珍妮的成员,后者被迫一再讲述她青少年时期被轮奸的经历,其他使女则齐声指控“是她的错,是她勾引了那些男人”。尽管这“只是一部电视剧”,作者本人也承认自己“只是在装装样子”,但其在现实中的投影却让人不寒而栗。在女性集体沦为弱势群体的社会里,为了获得相对的权力,女性会欣然接受对其他女性的指责甚至压迫——在社交媒体的时代,这种群体性的暴力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出版三十多年后,《使女的故事》已经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还被改编为电影、戏剧、歌剧甚至芭蕾舞的形式。耐人寻味的是,影片(1989年)和歌剧(2004年)在北美的首映时间分别对应了老布什和小布什的总统任期,无论有意或无意,这部初版于里根执政中期的小说每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的时刻都似乎恰好对应了美国右翼势力的复苏。当然,2017 年的美国并非阿特伍德笔下的基列国,让我们感到熟悉的是那个对女性极尽压迫的社会。所幸,无论她的小说呈现了一幅怎样压抑的末世图景,最后却总是保留了些许希望。
在小说结尾处,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距离基列国两百多年后的学术会议上,通过学者们的演讲,我们得知奥芙弗雷德或许逃离了基列国,并设法用磁带录下了自己见证的一切。这也是为什么小说最终定名为《使女的故事》,除了向《坎特伯雷故事》致敬外,它也暗示了这个故事的文体特征:这是一段由主人公讲给未来的潜在读者的回忆,它同时具备了童话和民间故事的奇幻色彩,也像是那些亲历过重大变革的人留下的“口述历史”。基列国从历史上消失了,而奥芙弗雷德的回忆却作为文明的一部分留存了下来。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