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文章惊海内 ——上世纪30年代美国青年汉学家在北京

费正清

顾立雅

恒慕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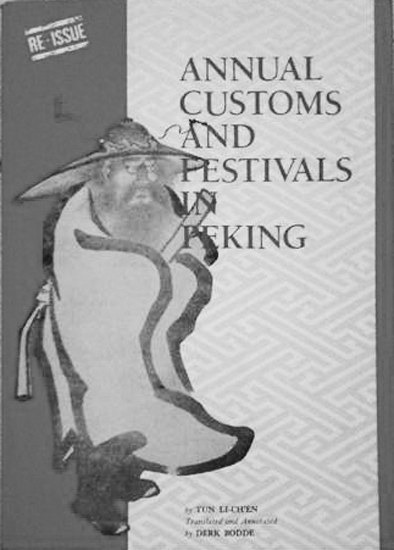
卜德译的《燕京岁时记》(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
第一代美国汉学家们虽然有着不同师承和不同的研究领域,却拥有一段共同的经历——上世纪30年代留学北京。他们在北京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刊登在北京的学术刊物上,或由北京的出版机构出版。这些早期作品可能有些粗浅和幼稚,但谁能一出手就可以“惊风雨”“泣鬼神”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开始从法国向美国转移,这当然大大得益于战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地位的迅速提升,而同时也和以费正清(JohnK.Fairbank)为代表的第一代美国专业汉学家的闪亮登场密切相关。考察第一代美国汉学家的学术背景就会发现,他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师承和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却拥有一段共同的经历——上世纪30年代都曾留学北京,短则1~2年,长则5~6年。这批人除了费正清之外,主要还有毕乃德(KnightBiggerstaff)、顾立雅(Herrlee G. Creel)、卜德(DerkBodde)、恒慕义(ArthurW.Hummel)等20多人。他们在北京学习、进修的过程中,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刊登在北京的学术刊物上,或由北京的出版机构出版。与他们日后的著作相比,这些早期的作品可能显得有些粗浅和幼稚,但谁能不经过磨练,一出手就可以“惊风雨”“泣鬼神”呢?
一
费正清在留学北京期间(1932—1935)发表了学术处女作。这篇题为《1858年条约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TheLe⁃galization ofthe Opium TradebeforetheTreatiesof1858”)的论文围绕这样一个中心问题展开:为什么鸦片输入中国为合法这一条款会被写入1858年11月8日中英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是由于英国的武力逼迫(这是普遍流传的看法),还是有其他原因。
费正清的论文共分五个小节:一、19世纪50年代的间歇期;二、英国政府的鸦片政策;三、中国实施禁烟;四、中国对鸦片贸易课税的建议;五、中国地方当局征收烟税的情况;六、一点阐释。在文章的开篇,费正清明确指出,“鸦片贸易是19世纪的一件大事,历史学家迟早都应该分析其原因、活动和影响。它同中外关系的各个方面——商业、政治和文化关系息息相关,因此它的具体情节迟早也应该通这个时期所有其他方面一样考订出来,并把两者之间的关系阐述清楚。”他写这篇文章正在于利用掌握的资料,揭示事实,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文章的第一小节,费正清指出,19世纪50年代随着英美商人想在条约口岸买到更多的丝绸和茶叶,他们也就必须在口岸外销售更多的鸦片,以便筹集必要的资金。“由于中国人不买外国制成品,外国商人购买中国产品最方便的方法,要么像17和18世纪所做的那样,大多使用带来的成船的白银,要么像19世纪初以来日益普遍的做法那样,使用成箱的鸦片。”这样丝、茶贸易和鸦片贸易就像一个连体婴儿那样不可分离,但问题是前者是合法的,而后者是非法的,——1842年的《南京条约》没有给予鸦片贸易以法律根据。在接下来的两个小节中,费正清考察了1842—1858年中英双方的政策,中国是厉行禁烟,而英方则采取不予支持和保护,实际是放任自流和纵容的政策。但中方的禁止也不是各地都一样,“禁烟在北方较为得力,特别是京城地区,一直坚持到较后的日子;在南方各省,鸦片输入与日俱增,种植鸦片也已经开始,而镇压措施却越来越少。”在鸦片泛滥难以禁止的情况下,中国官员开始陆续建议将鸦片作为合法贸易进行征税。费正清在文章的第四小节对此进行了考察,他指出,头一个建议征收烟税的官员是湖广监察御史汤云松,时间是1851年1月16日,但这位御史的奏疏未见下文。两年后张炜、吴廷溥两位御史上了同样内容的奏折,这次得到了皇帝和军机处的重视,但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军机大臣们在答复中强调补救的办法不是使鸦片合法化,而是更严厉的镇压。但不久太平军占领了南京(1853年3月)并席卷东南几个最富庶的省份,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于是征收烟税的问题再次提出并在一些地区得到了部分的实施。在文章的第五节,费正清以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四个口岸为例,具体说明了1855—1858年征收鸦片烟税的情况。1853年以来尽管北京政府还在强调禁烟,但地方政府为了解决为军队发饷等财政问题已经开始悄悄地向鸦片征税,而福州、厦门则更把征税公开化(1857年),这些都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前奏。通过以上的分析,费正清在结论部分指出,那种认为1858年英国强迫中国皇帝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流行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只说出了一半事实。另一半事实是“中国人希望通过对鸦片贸易全面征税,增加收入”,所以“承认鸦片贸易也是中国内政问题产生的结果”。
费正清这篇文章的重大突破在于使用了中文资料。在他之前,马士(HoseaB.Morse)在权威性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一书中也讨论过鸦片贸易问题(第一卷第八章《鸦片问题》,二十三章《鸦片,1842—1858》),但马士完全依靠外文材料,没有直接使用中文资料。费正清论文的一半是讨论1853年到1858年中国地方官员如何不执行中央政府的禁烟令而自行征收烟税的,这部分内容在马士的书中完全没有。利用原始的中文档案进行近代史研究是费正清的一大特色,这在第一篇文章中就显露无遗。
费正清的处女作完成后,发表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卷第2期(1934年7月)上。中国社会及政治学会是1915年由一批中外人士共同在北京发起建立的。1916年该会创办了英文会刊《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ChineseSocialandPoliticalScienceReview),第一期于4月出版,以后每个季度出版一期,4期为一卷。1941年终刊。
二
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上发表过论文的还有毕乃德,共两篇,第一篇《同文馆考》载第18卷第3期,第二篇《中国常驻外交使团的建立》载第20卷第1期。但毕乃德更看重的是他与中国学者邓嗣禹合作的英文本《中国参考书目解题》(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一书,1936年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正式出版。
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正如前言中所说,“是为了向西方学者初步介绍中国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参考书。”该书将中文参考书分为八大类——书目、类书、辞书、地理著作、传记著作、表格、年鉴、索引,共介绍了近300种参考书目。每一种书目都是先介绍作者、主要版本,然后对内容和价值进行简要评述。如综合性书目类中的《书目答问补正》条是这样的:“《书目答问补正》,5卷。张之洞在缪荃孙的协助下编写,张的序言写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范希曾又对之进行了修订、增补。南京国学图书馆1931年(民国二十年)活字版,2册。这份精心编选的书目收录了晚清时期依然存在的2266种重要书籍。一代鸿儒张之洞于1870年代编写了这本书,目的是方便初学者查找文献。该书原名《书目答问》,多次印刷。1920年代目录学家范希曾对原书进行了修订增补,他的增补在现在的版本中用“补”字标示。前4卷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顺序编排,每一种书给出卷数、作者名字、朝代以及编者和修订者所知道的所有不同版本,不少条目还有关于该书内容和价值的简要说明。第5卷开列了一些丛书目录,使本书成为中国第一本将丛书单列的书目。另外本书还附有编者认为对初学者而言最为重要的书籍目录,以及清朝著述诸家名录。这些著述家被分为14类,按照时间先后排列,名字第一次出现时编者也给出了他们的字号和籍贯。本书无疑是《四库全书总目》之后最为重要和最广泛使用的书目。对于某个领域的专门研究者来说,本书目可能不够完备,但对于想全面了解中国典籍的人说,本书是必不可少的。”
书目是通向学术研究的起点,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于中国研究来说,则更显得重要。因为中国历史长,文献多,目录学自刘向、刘歆父子以来早已成为专门的学问。因此该书出版后立刻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欢迎,1950年和1971年又出过两个修订版(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直被作为中国研究的最佳入门书之一。
三
除了用英文出版著作,留学生们还尝试用中文发表论文。在这方面成绩最突出的是顾立雅,代表作是《释天》,载《燕京学报》第18期(1935年)。
顾立雅此文的目的是想探讨中国古代天神观念的起源。从传世文献来看,似乎商人就已经有了天神观念,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惟天监下民,典厥义”(《尚书·高宗肜日》)。顾立雅经过研究后认为其实不然:“《商颂》五篇乃西周中叶以后宋国人之所作,此在中国学者已成定谳。《今文尚书·商书》凡五篇,其中天字共见十八次。然吾人细加考察,知此五篇亦周人所作。《汤誓》之文法与西周金文相近,其所函之意义亦与西周人之言论相同。《盘庚》三章之文法则同东周时之金文,其文气甚顺,多用‘之’字为连接词,不仅非商人之文,且不能视为西周初年之文。……《古史辨》第一集顾颉刚先生谓《盘庚》为商书中之唯一可信者,至于近年,顾氏之意见已与前日不同。顾氏曾与余言,《盘庚》乃周初人所作,至东周以后曾经学者所修改,则《盘庚》亦非商代文字。《高宗肜日》……如为武丁时作,则祖己对其父所陈说之词,于礼亦不合。如以为在祖庚时作,则是时祖己恐已去世,因其弟祖庚已继位为王。……学者又谓祖己为殷臣,其说又有抵牾……盖此文为周人所作,因其文法与西周金文相近,其中故事亦周人所杜撰,周人但知祖己之名贸然引用,而不知祖己乃王子而未就位者,故文中措词屡有失当之处。《西伯戡黎》乃周人对于殷代灭国事之宣传,假殷臣祖伊之言以出之,谓殷社将绝,乃曰‘天既讫我殷命’,又曰‘殷之即丧’,又曰‘今我民罔勿欲丧’。凡此数语,皆非殷臣对天子所应陈述之词。且此处言殷者二次,殷字为周人名商之词,此字甲骨文字中所未见。且文中述祖伊生时之言而称之曰祖,亦可证其出于后人所追述。……《微子》为周人攻击商人更激烈之文字,在《微子》中言商人无一可取,又文中屡用殷字。其所用语辞如‘微子若曰’,‘父师若曰’,据金文以证之,‘若曰’之词皆出史臣之笔,如此重要言论不能出之史臣,亦可证《微子》非商代之文。”所以《诗经·商颂》和《尚书·商书》中虽然有天神观念的痕迹,但不能因此说商人已经有天神观念。顾立雅认为,天神观念是周人建立的,在没有打败商朝以前就有了,克商建立周朝后则更加发达。
天是周人的神,那么商人的神是什么呢?顾立雅在研究甲骨文字时发现“帝”字很常见,“殷人言帝或上帝,其见于孙海波氏之《甲骨文编》者有六十三处”,而“天”字则很少见,主要用法也是代“大”字。等到两个部落接触特别是周克商以后,帝与天出现了同化的趋势:“此事如希腊之Hera与罗马之Juno本二神,Aphrodite及Venus亦二神;名虽异,其后二民族日渐同化,皆认为同一之神,帝与天字之关系亦如是。”顾立雅此文的最终结论是:“天之本谊为大人之象形字,即有地位之贵人。其后即以此名祖先大神,而此天字乃代表多数之祖先大神,执掌生民之事。其后用之既久,因多数之神所造成之集团,亦名为天,而忘其本有多数之义矣。在上之神名之曰天,因是名其所居之地亦曰天:此皆周人克商以前所用之义。及与商人文化相接之后,上帝之于商人,其性质如天之于周人。其后两民族日渐同化,以为上帝与天乃一神之异名。故周人之文字中同言一神,或名为天,或名为上帝:其意义之沿革如是。”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天与帝逐渐同一,但在西周金文、《诗经》《尚书》中,天用来指称天神的频率还是远远大于帝和上帝。顾立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在《诗经》中所有天字之作天神观念用者凡一百零六次,而帝字做上帝用者只三十八次。《尚书》中有七篇可定为周开国时之作者(《大诰》《康诰》《酒诰》《洛诰》《多士》《君奭》《多方》),在此七篇文字中天字凡见九十七次,帝字只见二十次。金文中可信为西周之作,而见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及吴其昌《金文疑年表》者凡二百十九篇,其中天字共见七十五次,帝与上帝共见四次。”可见周人在指称天神时还是更偏向于使用自己原有的称谓。
四
和顾立雅一样,卜德在北京进修的主要科目也是中国哲学(他后来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译成英文),但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和生活体验的丰富,卜德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文化精神是异常丰富的,不仅体现在四书五经和其他经典著作中,也体现在老百姓日常的衣食住行之中。《燕京岁时记》很快进入了他的视野,该书是一部记录北京岁时风物民俗的专书,以新年第一天开始,逐日逐月地介绍各种节日、庙会、食物、游戏以及有关的名胜古迹,生动而全面地展现了老北京的风俗画卷。该书打动卜德的一点就是“书中一次都没有直接提到孔夫子”,他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儒家虽然形塑了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和道德,但对于一般老百姓的影响却相对很小,他们的思想意识更多地体现在日常的节日和习俗中。”1930年代虽然离敦崇写作《燕京岁时记》的年代(完成于1900年,刊印于1906年)相去不远,但其中记录的一些节日已在淡化或消失。卜德在留学过程中对北京的生活越来越迷恋,他的翻译就个人来说是出于思古之幽情,而从学术上来说则是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老北京的生活,从而让他们从社会底层的方面了解中国的思想。
翻译《燕京岁时记》(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in Peking)的一大困难在于其中有太多太多的专有名词,很难迻译。卜德的做法基本上是直译,遇到个别极难翻译之处则采取意译或部分省略的方法。例如在《灯节》一节中,敦崇列举了多种烟火的名目,卜德一一做了翻译:盒子(smallboxes)、花盆(flowerpots)、烟火杆子(fire and smoke poles)、线穿牡丹(peoniesstrungonathread)、水浇莲(lotussprinkledwithwater)、金盘(goldenplates)、落月(fallingmoons)、葡萄架(grapearbors)、旂火(flagsoffire)、二踢脚(dou⁃ble-kicking feet)、飞天十响(ten explosionsflyingtoheav⁃en)、五鬼闹判儿(five devilsnoisilysplittingapart)、八角子(eightcorneredrockets)、炮打襄阳城(bombs for attacking thecityofHsiangYang)、天地灯(lanternsofheavenandearth)。如此等等。又如在《九花山子》一节中敦崇列举的菊花名目多达一百三十三种,卜德翻译了绝大部分,个别实在难以传达的只好略而未译,如“汉皋解佩”、“文经武纬”,“沉香贯珠”,对此,卜德在页下的注释中请求读者予以谅解。
卜德的“译者前言”写于1935年9月21日,由此可知他在此前已经完成了翻译工作。译本正式出版是在1936年,出版者是当时在北京十分活跃的法文书店,其老板是热心文化事业的法国人魏智(HenriVetch),书店的办公室设在北京饭店。
五
留学生在北京期间都忙于自己的学业,但也不是完全“两耳不闻窗外事”。恒慕义的《关于文学革命的几点思考》(“SomeThoughtsontheLiterary Revolution”)一文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该文发表在1926年的《新华文》(TheNewMandarin,北京华文学校校刊)上。
恒慕义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指出文学革命“是今天中国最有希望的运动,对中国人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远远超过辛亥革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今天发生的真正变化是在文化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所以大多数外国人都感受不到它真正的意义,他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另一方面习惯于从政治角度衡量所有运动(也是他们最熟悉的角度)。但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体,不如说是一种文明体。所以与其用政治理念来衡量中国的发展,还不如用在广大帝国发挥凝聚和融合的力量的文化来衡量。……遵循这样的民族特色,今天最有头脑的中国人关心的首要问题是重估他们的民族文化,而不是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宪政、国会、投票。他们可能没有明说,但他们的行动表明辛亥革命是不成熟的。他们知道,政治的重组必须在文化的重建后才能水到渠成。当一个民族还没有统一的国语的时候,期望国会能够有所作为只是空想。当一种文字只有少数人理解而多数人不知所云的时候,全民教育、社会责任、政治民主等等美好的愿望只能是纸上谈兵。不去料理根部只去修理枝叶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恒慕义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用英文向外国人阐释“文学革命”的重要性,让他们明白,这场由几个文人学者发动的革命比辛亥革命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未来的道路。
在接下来的部分,恒慕义集中笔墨说明了白话取代文言的必然性以及文学革命先驱所做出的贡献。文言对于中国一般的老百姓来说都很难,何况对于外国人呢?恒慕义在文章的最后说:“文言的艰深使大部分西方人根本无法掌握中国文明的要义。现在有了这个新的,也是简单得多的语言媒介,他们至少能够明白今天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古老文化的。这对于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将来国际间的友好相处都将发挥无法测量的影响。”这是就西方普通民众而言,对于专门研究中国的汉学家来说,文言虽然不是障碍,但白话显然更为明晰,更容易理解。恒慕义在北京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翻译成了英文,这篇洋洋洒洒六万多字的文章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被认为是现代白话散文的代表作(后曾收入周作人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在恒慕义之后,陆续有西方汉学家开始将中国现代小说、诗歌等翻译成外文并展开研究,他们的目光不再只盯着古代的诗词歌赋。从学术上来讲,文学革命造就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