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推出新作《御窑千年》“瓷器之路”传递中华文化

雍正瓷胎画珐琅柳燕图碗

元青花

元青花

清道光粉彩御窑厂图螭耳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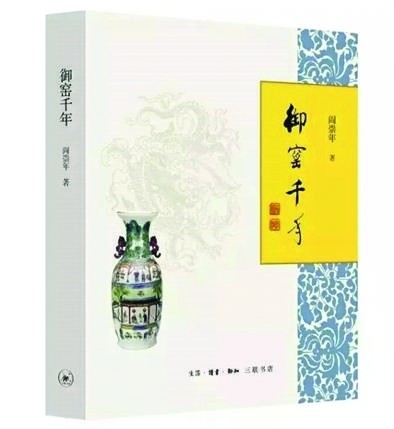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需要既重道、又重术,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我们对瓷器之路的回望,对于理解“一带一路”这一关系国家未来和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很有裨益的。
●历史与瓷器,要互相观照。我力求用自己的学术积累,从历史学角度,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让历史研究与御窑瓷器,宏观与微观,双方对话,彼此观照,从而既使历史生动,也使器物厚重。
1 让读者感知中华传统的瓷器文化
记者:刚拿到《御窑千年》时,我以为这是一本中国瓷器史专著,也因想到一个清史研究专家,居然会写这么一部要不是对中国瓷器有精深的专业研究实难胜任的书,感到特别好奇。读后倒是感慨,历史学家写瓷器文化真是别有千秋。就像这本书介绍文字里说的,在这部简明瓷器文化史里,你立足于千年中国历史,以小见大,寓理于器,品味御窑瓷器的传世精品,纵论御窑的兴与衰,透视瓷器的情与趣。不妨说说写这本书,是出于什么样的机缘?
阎崇年:我过去对瓷器的确了解不多,但我和瓷器特别有缘。现在回想起来,御窑和陶瓷其实一直徜徉在我的学术考察之中。早在1992年,我前往台湾地区访问,就曾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山洞库房,看到许多珍贵的瓷器。每件瓷器都用丝绸层层包裹,用丝绵填衬着,库房里恒温恒湿,盛放瓷器的箱子还包着铁皮,想是保留了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时候的样子。这次经历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我没想过写瓷器。直到前些年,在“百家讲坛”主讲“大故宫”系列之后,有观众问我能否写写故宫收藏非常丰富的瓷器,让广大读者能够更好地感知中华传统的瓷器文化,我认真考虑后,决定做这件事。
记者:可以想见,为写这本书,你做了大量的准备。
阎崇年:这本书,从搜集资料到动笔写作,我十易其稿才告完成。要说准备的时间,粗粗算来,有差不多三年。之前学术准备没有算进去。我读了一百多本有关瓷器的书籍,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物档案、图录、考古报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就借去外地考察的机会四处看窑址。主要的官窑、御窑瓷器产地及场址,我走访了很多。景德镇御窑、浙江龙泉窑、河南钧窑、陕西耀州窑、广东潮州窑、广西中和窑、山东博山窑、福建德化窑、河北定窑等等。我也去参观了“南海一号”沉船的水下博物馆。这里面,有的窑口只是遗址了,像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现在还在烧造瓷器。
记者:你在书里提到最多的地方,还是景德镇的御窑。
阎崇年:是这样,我去过景德镇多次。在那里,我逐渐了解到制瓷的七十二道工序。从采瓷石、采高岭土开始,工匠们怎样把瓷土粉碎、淘洗、制成陶泥,怎样做瓷胎、绘画,以及满窑、烧窑、开窑等一道道工序。这七十二道工序,是任何一道都不能出一点点问题的,所以每一道都要严格检查,只要查出一点毛病就遗弃。那种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我感觉和造航天火箭一样,虽然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行业,但一样地严肃认真、精益求精。你看那个点火的过程,他们不是靠仪器,而是凭经验观察窑内的温度,真是相当了不起。
2 回望瓷器历史,对于理解“一带一路”等重大问题很有裨益
记者:你谈到的工匠精神正是我们眼下特别提倡的。这让我想到,这本书里虽然提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工匠,但能在史册上留下名字的实在太少,而实际上,正是很多工匠筚路蓝缕,为陶瓷发展和创新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阎崇年:其实,陶瓷的历史,也是陶瓷工匠的历史。因为,陶瓷工匠是陶瓷历史的主体。在陶瓷生产过程中,陶瓷工匠贡献巨大。他们中的一些人或以身殉职,或以器名世。尤其是御窑瓷器,它们的设计、生产都汇聚了当时最好的能工巧匠。其实不只是工匠,我翻阅相关目录学时,就感觉关于御窑,关于陶瓷,历史上记录得实在太少。虽有宋人蒋祈的《陶记》、明人王宗沐的《陶书》、清人朱琰的《陶说》、蓝浦的《陶录》、唐英的《陶冶图说》等,填补前贤之所阙。但这与中华浩浩洋洋古籍相比,实在少得可怜。一部《四库全书》,采入了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书籍,共计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但居然没收入一本关于御窑和陶瓷的著作。御窑瓷器,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著述却少。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记者:在你看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阎崇年:这跟我们重道轻器、厚理薄技的文化传统有关。片面地将“器”蔑之为“雕虫小技”、“奇器淫巧”,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影响,是造成中国近世落后挨打,割地赔款,备受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需要既重道、又重术,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记者:在这本书里,你还谈到,古代的“瓷器之路”和现在的“一带一路”基本重合。当时写的时候,你是否想到过这一点?
阎崇年:中国古代的瓷器之路,与“一带一路”的这种重合,可以说,我们对它的回望,对于理解“一带一路”这一关系国家未来和民族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很有裨益的。所以,我在相关系列讲座和书里,专门讲述了“瓷器之路”。当然,我写瓷器文化有自己的考虑。我是研究历史的,我知道历史研究主要有四个面向,第一是人,第二是事,第三是文,第四是物。这么多年我主要摸索的是前两个,我通过文献档案,来研究努尔哈赤、康熙、袁崇焕等历史人物,包括那次主讲“大故宫”,涉及的也主要是皇家的制度、人物、建筑等方面,也没有过多关注器物。我觉得自己在通过物来反映历史这方面做得不够。而最适合的“物”,无疑就是中国的瓷器。
记者:为什么说最合适的“物”,就是中国的瓷器?我能想到众所周知的一个理由是,“中国”的英译“China”,就是指的“瓷器”。你尤为关注瓷器,是看重它作为中华文化伟大符号的重要意义吗?
阎崇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英译是“China”,但未必了解这背后的来历。这里有一个故事,瓷都景德镇,古时候叫昌南镇。相传瓷器销往国外,外国人不知道这种器物该叫什么,只知道来自昌南,于是就将“昌南”谐音作china。所以,china不仅成了瓷器的英文名,还成了中国的英文名称。
记者:照这么说,瓷器成为中华文化最为重要的符号,有其特殊的偶然性。
阎崇年:其实并不偶然。中国瓷器就是这么一个特别的器物,上至王公贵族、艺术家,下至普通百姓,大家看了都喜欢。而且不只是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喜欢。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和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是中国瓷器的发烧友。让我吃惊的是,在非洲竟然有整扇大门,用元青花碎片作为装饰。四大发明中,指南针并不普及,它只有在开船的时候用得着。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也一样,不是老百姓都用得着。只有瓷器,它能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且能保存下来,即使过上千年都光彩如新。2007年,南宋初年沉船“南海一号”打捞出水的时候,里面有的瓷器还和新的一样。
3 让历史研究与御窑瓷器,宏观与微观,双方对话,彼此观照
记者:看来外国人喜欢中国瓷器是有道理的,这在这本书里也能找到佐证。比如在《大元青花》一节里,你写到元青花瓷器最早是由英国学者霍布森发现的。你还写到,继霍布森之后,美国学者约翰·波普在国际陶瓷学界第一次证明,元青花瓷器并非孤例,而是一大类瓷器。我疑惑的是,为什么是国外学者最早做出了这样的论证?
阎崇年:因为中国历史文献里没有记载。元代后期,青花瓷器就远销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地,但元亡以后,青花就逐渐不被后人知晓了。在长达六百年时间里,人们一直以为青花瓷是直到明代才出现的。还有一个缘故,一些珍贵的元青花瓷器,在民国时期挖出来之后,卖给了一些中国商人,那些商人又把这些瓷器转手卖给了外国人。所以,中国人自己看不到这些瓷器。
记者:我感兴趣的是,既然国外学者论证为元青花,那它就是中国元朝时期的瓷器。为何你在这一节里花那么大篇幅论证元青花“根在中国”?
阎崇年:写这一节,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最难的部分,就是这个论证。以前没多少人这样做过。我在书里从文字、窑址、实物、纹饰四个方面,以十二条论据进行了论证。比如我讲到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上面有62个字或61个字的铭文,不仅是用中文写的,而且写了时间、地点等六个方面,这个就很清楚了。还有不少元青花,都有龙凤、仙鹤、鸳鸯等动物,或牡丹、菊花等植物的图案,那也很清楚是中国元素。还有一些元青花绘有中国戏剧人物故事图案,带有浓郁的中原农耕文化气息。我着力比较多的是纹饰方面,因为元青花以蓝色纹饰、大量留白为特征。把内蒙古基本跑了一遍以后,我站在大草原仰望,笼盖四野,满目一片蓝颜色、带点儿白云。我就理解了,蒙古族为何“崇白尚蓝”,元青花为何会有这个特点。而且这个特点在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里都是没有的,它的出现也表明创新的重要性。
记者:这如何理解?
阎崇年:御窑得以千年,其根本就在于不断创新。“御窑千年”的历史文化,在精美瓷器的背后,隐藏着的精华是“新”,就是思想创新、管理创新、技艺创新、产品创新!所以我在“序”里说,中国瓷器文化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不是姓“皇”,而是姓“新”。创新,既是御窑之魂,也是瓷器之魂。元青花就不用说了,元代还有釉里红,这改变了单一颜色瓷器的局面,开创了彩色瓷器的新境界;当然,这不是说此前的瓷器没有创新。像宋代的青白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不可复制的。再有明代的斗彩、五彩,清代的珐琅彩、粉彩,都是各个时代创新的产物。
记者:那某个特定的时代与瓷器创新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不同朝代的瓷器,何以会如此大异其趣。
阎崇年:可以说是非常直接的关系。瓷器一开始是烧不出颜色,烧不出花来的。你就是蘸上颜料,也是很不容易上色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元代之前没这样的技艺,说原因其实也简单,因为瓷器颜色由不同矿物成分和烧制温度等多种因素形成,但元代以前缺乏一种叫做“钴”的矿物质颜料,这种颜料的译名是“苏麻离青”,蒙元时期因频繁的文化交流,把这种颜料从西亚传过来了。
有了这种颜料,才算解决了在瓷器上彩绘颜色的问题。所以,我们谈唐宋以来瓷器的历史,会特别强调元青花。因为,从全世界来看,元青花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首次出现了彩绘瓷器。这之后才可能出现其他各种彩绘瓷器。
记者:这本书书名为《御窑千年》,可见其中说到的瓷器,跟宫廷有着密切的关系。
阎崇年:宫廷无疑受制于时代。像元青花,元代之前宫廷怎么推动,也不太可能出现。但宫廷有时会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比如有些陶瓷的官样,就直接在北京出,也就是宫里画好了官样,让某个瓷窑去烧造。但有些影响是间接的。打个比方,这本书里137幅插图,我有一次问了好几个专家,让他们写字条,写出他们最喜欢其中哪一幅,结果他们不约而同选了清雍正瓷胎画珐琅柳燕图碗。他们都这么选,我想是因为这个图碗很简洁,色彩很自然。它不像宋代时那么简单,也不像乾隆时期那么繁缛。这一对图碗描绘了一幅花红柳绿、春燕双栖的形象。其中一个碗,两只燕子相互呼应。另一只你看是不是有些特别?
记者:看图片上面只有一只燕子,是不是另一只燕子在图片里看不到的另一面?要只是一只燕子的话,是不是说用了留白的手法?
阎崇年:另一面也没有,这只碗上就一只燕子,那怎么体现双栖呢?仔细看,画上的这只燕子在回望,可能是等另一只燕子飞回来,那只燕子没有画出来,这一显一隐、一明一暗的画法,就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了。你再看这图碗,真是雪白雪白,非常细腻。应该说,这对图碗已经达到高雅的意境了,所以谁见了,谁都喜欢。
记者:我注意到这本书的封面上,用了清道光粉彩御窑厂图螭耳瓶。
阎崇年:从艺术上讲,这并不是最好的。选这个做封面,是因为这件瓷器瓶外壁通体以粉彩描绘了清代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实景的缘故。我在书里面也详细做了描绘。这件瓷器以御窑厂内倚珠山而建的“御诗亭”为中心,东、西辕门上各挂一面黄色大旗。旗上以黑彩书写“御窑厂”三字。再看两侧白墙青瓦,有回廊、拱门。正中的高大厅堂里,几名监工在议商事情。厂内工匠各司其职,专心劳作。画面还反映了原料开采、送料、成型、制坯、运坯、画坯、施釉、画彩、满窑、烧窑、出窑、装运等各道工序。画面所使用的彩料有红、黄、绿、紫、蓝、黑、金彩等。如果你看到整件瓷器,你还会看到上面画了61个人物。所以说,这件瓷器也非常重要,它是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管理状况的珍贵实录。
记者:你举的这个例子,解答了一个困惑。瓷器怎么体现其艺术性?每件瓷器都是不可复制的,不可复制固然是艺术独创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毕竟不能等同于艺术性。
阎崇年:这里有一个情况。中国自秦始皇以降的皇朝时期,有关陶瓷艺术存在一种现象,士人的艺术与工匠的艺术,两者是分裂,不相契合。但是,从宋代以降,特别是元代以来,两者逐渐开始结合。元代时,就常常由宫廷画师绘出官样,交到景德镇官窑烧造。明代,尤其是清代,很多宫廷书家、画家,甚至皇帝,都参与其事,所以出现了“郎窑”“年窑”“唐窑”。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两者的融合,才开出了瓷器艺术的灿烂新花。
记者:这般高妙的艺术性,如果不是御窑烧制,是很难达到的。这是不是你选择御窑作为研究考察瓷器的一个重要缘由?
阎崇年:我选御窑作为切入口,是有原因的。因为瓷器的历史太过复杂,各地的民窑很多,都有自己的特色。但在鸦片战争以前,官窑和民窑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制瓷的官样从皇宫出来,是由当时最好的艺术家、书法家绘制的。还有,一些制瓷的原料,比如清代的珐琅彩,一度由皇家控制,从进口到自行研发,特别昂贵。这样你就明白了,御窑瓷器,是精华里的精华,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工艺水平和工匠们的最高智慧。
记者:那何谓御窑?
阎崇年:这么说吧,御窑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它既可以指皇家御用窑场及管理机构,又可以指烧造过御用瓷器的窑场。从狭义而言,御窑贯穿明、清两朝;广义而言,御窑萌芽于宋、元,成熟于明、清。广义的御窑,历史已逾千年。
记者:也就是说,你指的“御窑千年”,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的。
阎崇年:对。有人就提出异议说,明设“御器厂”,清设“御窑厂”,至今七百多年,哪里有千年?我考虑的就是广义的御窑。朝廷之窑,先有官窑,后有御窑,而官窑已绵延千年。另外,景德镇获御赐镇名,奉旨董造,可以作为御窑的一个始源标志,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我觉得“御窑千年”,本是明清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更是明清宫廷史研究的应有之义。在中国,研究宫廷历史,不知御窑,是个缺憾;于历史,学点瓷器知识,学术视野会更加拓展。历史与瓷器,要互相观照。从历史看御窑,由宏观到微观;从御窑看历史,由微观到宏观。我力求用自己的学术积累,从历史学角度,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让历史研究与御窑瓷器,宏观与微观,双方对话,彼此观照,从而既使历史生动,也使器物厚重。
4 作为一个当代学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守自己的学术使命
记者:这本书谈了御窑,谈了瓷器,也探讨了瓷器的产生和发展,还有烧造瓷器的原料和工艺等等,但另一方面,正如责编张龙所说,这本书侧重写了与瓷器文化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各式各样的人。显见地,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在重瓷器的同时,也特别关注人在瓷器发展史上的作用。
阎崇年:是这样。这本书里写了四百来个人。就像一台戏一样,公子、美女、丫鬟、管家等各个角色,在上面粉墨登场。我写的这些人中,既包括主导瓷器生产、制定窑业政策、监督御窑发展的皇帝、官员、宦官,也包括为提高烧造瓷器工艺水平、提升瓷器艺术品位的工匠、文人、画师。在历史上,写人更像是纪传体的专属,司马迁在《史记》里就写了很多人。但有关陶瓷的著述,都不怎么写人。当然,我写人,是通过人来反映器物,人在瓷器里头。
记者:不仅是人在瓷器里头,有些人在书里,给人感觉与瓷器浑然一体。
阎崇年:我在书里写了三四个特别优秀的督陶官,像陈有年、王锳、唐英。其中数唐英对我们最有启发性。唐英是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的督陶官兼制瓷高手。雍正命他协理督陶那年,他都47岁了。初到御窑厂,他于瓷器烧造,如他自己所说是“茫茫不晓”。但他面临新的职务不是退缩、应付,而是担当、奋进。他放下官员架子,“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终把自己从外行变成了内行。而且他非常清廉,他有一句诗叫‘真清真白阶前雪,奇富奇贫架上书’,品德可谓非常高尚,这都值得我们学习。
记者:唐英在瓷艺上的贡献是不消说了。他还把制瓷工艺与诗、书、画、印相结合。你也说到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他对御窑瓷器的制作及其发展创新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且编写出《陶冶图说》等著作。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唐英在制度上的贡献,因为这还需要他有远远超出陶瓷专业领域的魄力和能力。
阎崇年:对。唐英任内,就人事、财务、生产、工艺诸多方面都立规矩。原来御窑开支浩大,财务制度不清。他制定了《烧造陶器则例章程》,两百多年前就实施成本核算,应该说观念是非常超前的。
记者:到底是什么促使唐英成为中国御窑千年第一人,而且是世界陶瓷史上一大家?
阎崇年:我在书里也探讨了这个问题。你看,唐英那么敬业,那么清廉。他督陶长达27年,经他手的瓷器就达一百多万件。那么,他的动力来自哪里?我没看到有文章分析他这么多年兢兢业业、刻苦钻研的动力。我觉得这和他的出身有关,唐英是包衣。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写到,“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我觉得唐英就属于这种情况。应该说这样的身份,造成了他内心特别矛盾,也促使他奋发有为,他珍重自己的工作,每到一个岗位,都竭尽全力把它做好。
记者:在我印象里,能不凭主观臆断,而是从具体的材料出发,一步一步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里去,这是当下历史研究里比较缺乏的。你对历史研究孜孜以求,是出于什么样的动力?
阎崇年:我治史的旨趣归总起来就八个字:求真求理,师法自然。研究历史,难就难在要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而且历史研究是一个宏观、微观不断切换、相互交融的过程。研究者自己对一个史实一定要先搞清楚,然后理清楚,最后讲清楚。我在这本书的“序”里还插了一段闲话,讲到同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联系的十四年里获得的几点心得。我从演讲人与观众、听众如何互动的角度,讲了“四个明白”,就是要学明白,写明白,讲明白,还要让人听明白。我们说,一个战士应该做到守土有责,作为一个当代学者,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守自己的学术使命。
5 做历史研究要有明确的观点
记者:从一些资料里了解到,你最初攻读的是先秦史,后来听从中国科学院杨向奎教授的指教,转攻清史。作为历史研究者也好,还是普通读者也好,怎样突破个人的喜好,对历史人物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
阎崇年:评价历史人物,无非就是根据历史事实,根据他们所处的历史地位,看他们在一些事情上是不是尽了力,是不是对历史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记者:那对于中华文明遗迹的评价呢?在“百家讲坛”上,你主讲了“大故宫”。你也曾有写“大长城”、“大运河”的打算。你在这些遗迹上,都加了一个“大”字。这是否因为你受了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影响,觉得我们得放宽历史的视界去看这些遗迹?还是因为你觉得这些遗迹本身,即使放在世界的坐标系上,也当得起一个“大”字,所以有必要加以强调。
阎崇年:我说了“大故宫”后,观众对我在“故宫”前面加个“大”字是赞同的。故宫的“大”大得名副其实。你想啊,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文明都中断了,这些古文明的皇宫都没有保留下来,而现在存世的皇宫,不管是巴黎的卢浮宫、英国的白金汉宫、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面积都没有北京故宫大。说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皇宫中面积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再有,故宫的历史大约为600年。中华五千年文化和艺术的精华都集中在故宫。它有180万件珍藏文物,1000万件档案,200万件满文档案,其中任何一件都是无价之宝。所以,在当今世界,就其占地面积之广阔,建筑组群之雄伟,珍藏文物之丰富,连续时间之绵长,蕴含理念之深邃,文化影响之久远,故宫都无与伦比。当然中国的长城、运河也是“大”的,这都是以事实说话。不过,“大长城”我恐怕是写不成了,“大运河”还在考虑中。
记者:有道是“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感觉你在力求讲清楚史料的同时,也是讲求文采的,所以这本书虽然讲的是有理有据的历史,读来却不觉枯涩。这让我想到,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有鉴于此,我想问问,在具体而微的历史写作上,你有何思考?
阎崇年:姚鼐的这个观点,我自己的体会是,做历史研究,写论文要有明确的观点。你用哪些材料,从哪儿开始分析,自己都要清楚明白。说到考据,你写文章,要从史料、实物或出土的文物出发。在这一点上,我是很谨慎的,我写这本书,凡是民间的瓷器,还有个人收藏的,我一件都没选。我选的瓷器,都是出自故宫的,博物院的,光是宫廷的还不行,还必须是传承有序,说得清楚来历。辞章当然也是要讲的,但历史学研究,不像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那样倚重才华,而是更重积累。所谓史学家成功于史才、史学、史识,可以说,没有多年积累,没有高见卓识,就难以在历史研究上取得大的成绩。
记者:谈积累,还得是有效的积累。照你看,怎样才能完成这种有效的积累?
阎崇年:这方面真没什么诀窍。归总到一句话,就是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说故宫,我都记不得去了多少次,少说也在一千次以上吧,有一个时期我是天天去。我去干什么,就是去学习,去读书的。所以说有些东西,你读多了,看多了,思考多了,也就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