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把评论的事做到极致是怎样?据说就是一种情怀

我想多一点自觉,总比少一点自觉好。就是对这个文脉多一点感受,总比少一点感受好。
文艺批评要有“置身其中”的自我意识
徐芳:在网络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有人甚至说:可以把文艺批评的神经拉进异次元?而这将是一场怎样的场景?是否批评需要合理,而生活则不一定……当代文艺批评该如何做到不隔?你觉得当下应该关注哪些现实问题?
张新颖:先说说对批评的不满。我好像想不出,有哪一个行当——专业,像文学批评一样,遭受着来自多方面的不满。批评的历史和对它不满的历史一样漫长,可是它还一直活了下来。
就说现在吧,作家不满批评,读者不满批评,领导不满意,群众不买账,就是批评内部,似乎也互相不满。批评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让人把不满发泄到它身上。而且,你会发现,对批评不满和指责,总是最安全的,我的意思是说,不会犯错。
为什么不满呢?就是它没有达到要求。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话题,常常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批评?可是,这样的讨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我们”,所以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需要和要求。永远也不会出现让这个构成无比繁杂的“我们”满意的文学批评。
我并不想讨论批评的性质,它的功能和意义,我只是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批评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和要求而产生的,而且在我看来,恰恰是那些为了满足一些需要和要求而产生的批评,不那么有意思。
为了满足作家的需要,会产生那种“贴身保镖”现象;为了让领导满意,为了让读者喝彩,都有可能生产出批评来。我一方面这么说,即批评不是为了批评之外的需要和要求而产生的,另一方面又会矛盾地觉得,其实各种各样为了满足不同需要和要求的批评,也都有存在的理由。
因为我强调批评是一种个体精神活动,没有统一的批评,所以很难对复杂多样的批评一概而论。
批评如何做到不隔?这问题说起来复杂。和什么不隔?和人生不隔?和现实不隔?和艺术传统不隔?和作家的创造性劳动不隔?和批评家个人的实感经验不隔?我用了这么多的疑问句,也是要指出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而每一个方面,对批评来说,都不是容易对付的。
我曾经说过,批评从个人生命、文学传统和生活世界中产生,始终别忘了批评是从哪里来的,就有可能克服“隔”的毛病。批评中很多有用的东西,理论、概念、思想、观点、方法,都有可能成为产生“隔”的因素。如何不隔,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方法,只能是批评家自己意识到了,慢慢加以克服。
批评如何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中的哪些问题,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意见。但我想说的是,当代批评本身就置身于现实之中,要有一种“置身其中”的自我意识,并且把这种自我意识带到具体的批评工作中去,把“置身其中”的个人的实感经验,带到具体的批评工作中去。
谁都能感受得到,我们今天的现实无比复杂,要承认我们自身和这个无比复杂的现实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轻易和简单地概括这个现实,不能假设自己在这个现实之外,批评这个现实。

究竟有没有一条我们自己理出来的,概括出来的,可以说得清楚的那个传统?
徐芳:把评论的事做到极致是怎样?据说就是一种情怀?您的文章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理论评论奖,印象中获奖的多是砖头厚的专著,而你这篇《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是以一万多字的单篇文章获奖,这说明了什么?
张新颖:这个大概不能说明什么,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书有书的好,文章有文章的好。以前理论批评奖里面,获奖的有书,也有单篇文章,虽然单篇文章比较少。
徐芳:你说过“要说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恐怕就是,因为我多年从事沈从文的研究,我以沈从文为个案,描述了现代和当代文学之间密切联系的一条脉络。”但有人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为什么理论评论要解析经典名作、经典作家呢?是否所有历史上的艺术、文学研究,都必须和当代相结合?
张新颖:不是说所有历史上的艺术、文学研究,都必须和当代结合,而是说,我们在当代,不能假装我们这个当代是凭空产生的,或者可以孤立存在,和历史不发生关系;当代的创作,也不可能和历史上的创作不发生关系。
我做现代文学研究,一个很深的感想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最近的文脉就是现代文脉,或者换个说法,是我们现代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其实已经超过了用“重要性”这样的词来描述。怎么说呢?不论我们承认不承认,意识没意识到,我们都是一个现代文学传统,或者说是现代文脉的承受者。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这样讲话,为什么这样写作,就有一个最基本的现代汉语的问题。但现代汉语的文学历史,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时间。我们不能以为现代汉语这个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一个最近的创造过程中才逐渐产生的,这里面当然不是一种力量,但是最重要的一种力量,就是现代文学的创造力量。
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东西完全无知的话,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所以我想多一点自觉,总比少一点自觉好。就是对这个文脉多一点感受,总比少一点感受好。
现代文脉这个东西,不是一条一脉,也不固定。我们会把一些东西固定化,把一些东西给它命名,但究竟有没有一条我们自己理出来的,概括出来的,可以说得清楚的那个传统?有否那一条线,有否那一脉,其实我是很怀疑的。这些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大家也知道,其实在现代的起点上,汇入很多很多的声音,但就是这个众声喧哗的宽阔局面,也慢慢变得狭窄了。
我们在讲文脉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它固定化、概念化,不要相信概括出来的东西,要由我们自己去体会。有的传统,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还有一些传统一下子看不到,那个脉它是比较隐藏的,但那个比较“隐”的脉,它一定是比“显”的不重要吗?这个也不一定。
还有一点我想说,作为一个今天的人,我们不要害怕传统文脉,怕那个东西会掩盖且抹杀掉我们的创造性。我想应该有一点勇气,比如说像当年的艾略特,他讲个人才能和传统的时候,他说儿子发明父亲。当艾略特老了的时候,他也会反省这个说法,但儿子发明父亲,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现代文学传统,就是我们那个遗产,到底是不是有价值的,这个不仅看遗产本身,还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把那个传统激活,去从那里面发现有价值的部分。
所以这个不是考验传统,而是考验我们自己。有的东西就是了不起,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比如说撞钟,有些人撞不响,有的人力气小,回响也就比较小;有的人力气大,就很响。
其实是考验我们自己的力量,包括我们自己的创造力,有创造力才能够把这个传统激活,才能够从这个传统里面发现更有价值的东西——你如果真的能够把它激活。真的有所发现的话,再用文脉这个词来讲,比如说我们找矿,找到了一个脉,就了不得。所以,如在个人的创作上,为自己找到一个脉,这个脉并不受任何专家学者指引,而是你自己去找到的,它就能够给你提供力量,更可以持续地支持你不断创造。
我描述沈从文传统在当代创作中的回响,其实有上面说的这么个思想背景在,所以我说是一个个案,一条脉络。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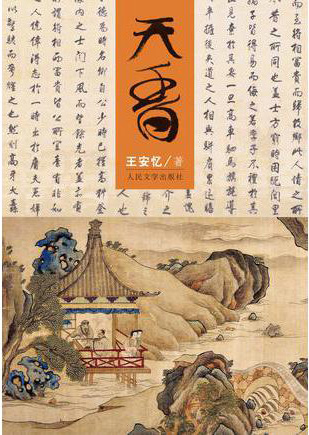
“气数”和伟力,造就繁华的上海
徐芳:你曾和王安忆做过大量关于创作的对话,她倾尽心血去写,也写出了极大的分量。我认为她的作品里“物”的形象十分鲜明,就以《天香》为例,你认为《天香》中的“物”,与罗布·格里耶所状写的“物”有什么不同?在格里耶那儿,“物”与“人”一样,可以成为作品的主体,“物”是与“人”并列的一个中心。王安忆笔下的“物”与中国古代的“物”之间,有没有某种传承关系?
张新颖:太不一样了。罗布·格里耶的“物”是要和主观的感情投射隔离开来,《天香》里的“物”——顾绣,她叫做“天香园绣”,却是载体、中介、创造物,不仅和小说里的人物不可分割,而且和小说叙述者的认识、感情紧密关联。而且我觉得《天香》好,就好在这个“物”聚集了很多东西。
王安忆多年前留意顾绣,不论这出于有意识的选择,还是无意识的遭遇,现在回过头去看,是预留了创作拓展的空间。如果说这一物件选得好,就因为自身含有展开的空间,好就好它是四通八达的。四通八达是此物本身内含的性质,但作家也要有意识地去响应这种性质,创造性地写出来才行。
“天香园绣”这个物件,有几个“通”所连接、结合的丰富层次:
一是自身的上下通。“天香园绣”本质上是工艺品,能上能下。向上是艺术,发展到极处是罕见天才的至高艺术;向下是实用、日用,与百姓生活相连,与民间生计相关。这样的上下通,就连接起不同层面的世界。
还不仅如此,“天香园绣”起自民间,经过闺阁向上提升精进,达到出神入化、天下绝品的境地,又从至高的精尖处回落,流出天香园,流向轰轰烈烈的世俗民间,回到民间,完成了一个循环,更把自身的命运推向广阔的生机之中。
二是通性格人心。天工开物,假借人手,所以物中有人,有人的性格、遭遇、修养、技巧、慧心、神思。这些因素综合外化,变成有形的物。“天香园绣”的里外通,连接起与各种人事、各色人生的关系。“天香园绣”的历史,也即三代女性创造它的历史,同时也是三代女性的寂寞心史,一物之产生、发展和流变,积聚又融通了多少生命的丰富信息!
还有一通,是与时势通,与“气数”通,与历史的大逻辑通。顾绣产生于晚明,那一时期人对生产技术的认识与掌握已进步到自觉的阶段,“天香园绣”也是顺了、应了、通了这样的大势和“气数”。
“天香园绣”能逆申家的衰势而兴,不只是闺阁中几个女性的个人才艺和能力,也与这个“更大的气数”——“天香园”外头那种“从四面八方合拢而来”的时势与历史的伟力——息息相关。放长放宽视界,就能清楚地看到,这“气数”和伟力,把一个几近荒蛮之地,造就成了繁华鼎沸的上海。
中国文学有缘“物”抒情的传统,王安忆的小说和古代“物”诗,未必有什么直接关联,但她写“天香园绣”通性格人心、关时运气数、法天地造化,其实也不妨看作是一种“抽象的抒情”。
虽然批评有时候是判断,批评却并不就是判断
徐芳:该怎么理解文艺对评论的本质诉求?文艺批评接受文艺创作的过程,或就是一个审美的过程?
张新颖:其实批评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就像小说有各种各样的小说,诗歌有各种各样的诗歌一样,但我们总想要一种一样的批评,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每个人对批评的理解不一样,这才是正常的。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理解的批评。
批评是一项尴尬的事业,在今天,尤其如此。公众要求批评对作品说话,判断作品的好坏优劣,要求批评给出结论和说法,这个结论和说法要简单、明了,如果还能痛快,那就更好了。
批评家好像是拿着一把尺子去丈量作品的人,有时候他们不仅被要求报出丈量的结果,而且还被要求亮出他们的尺子:他们经常被追问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可是,我想说的是,虽然批评有时候是判断,批评却并不就是判断。批评家也不是作品的丈量员,我的手里没有尺子。
当批评家以批评的方式面对文学的时候,并不需要有一个或几个标准,一把或几把尺子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不需要以掌握了某种真理,或某种正确理论的姿态去居高临下地判断。
我这样说,并不表明我认为批评是和真理、理论无关的,是完全随意的;比起那种认为已经拥有了真理或理论的批评来,我更愿意认为批评是在寻求真理、形成理论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它和文学作品对话,它可能会从作品中受益,得到帮助,当然也可能得不到帮助。
批评从作品中受益,得到帮助,这是无比美妙的事情,拿着尺子的批评家——不论这把尺子是用来测量作品的,还是时刻准备变成戒尺来打作家手心的——是无法享受这样的“美妙”。
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批评是从它所批评的作品中产生出来的。我不能同意,那种认为批评是寄生于作品的想法。
批评是从哪里来的?批评家的观念和趣味,他的观察、描述和判断能力,他的发现、阐释和想象能力,他的修养和风格,他的人格和信念,是从他个人的人生经验和所受的教育总量中,从人类悠长丰富的文学传统中,从他所置身的广阔深厚的生活世界中,一点一滴累积形成的。
这一点一滴累积形成的,是一个独立、坚实、自主的个体,虽然批评家不带着尺子,他却不是内心一片空白地面对作品。
批评家带着足够的谦虚和作品对话,同时他也带着足够的自尊和作品对话。他面对作品说话,却不仅仅是对作品说话,他更是面对着批评和作品共同置身的广阔深厚的生活世界说话……面对着批评和作品共同拥有的文学传统说话,同时,他也可以是面对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教育总量,自己对自己说话。
因为批评从个人生命、文学传统和生活世界中产生,所以,个人生命、文学传统、生活世界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批评就有可能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批评面对作品说话,作品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批评就有可能有多么丰富和复杂。
比起要求批评判断作品的好坏优劣、给出结论和说法来,相反方向的要求——要求批评充分实践它可能有的丰富和复杂,充分实践它的独立、自主和自由,充分实践它的严肃和亲切,它的一丝不苟和活泼生动,它的直接明朗和曲折隐晦,甚至充分实践和深化它自身的欢乐和痛苦——我以为,是更难的,却更值得去努力的。
朝向这个方向的批评实践,不仅有益于批评自身,而且将有益于与它紧密联系的个人生命、文学传统和生活世界,有益于和它对话的文学作品。(题图来源:齐鲁网、视觉中国、豆瓣)
【嘉宾介绍】张新颖,1967年生,山东招远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韩国釜山大学交换教授(200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教授(2006年),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2006年)、第一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2008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4年)等多种奖项。主要作品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精读》、《沈从文的后半生》,当代文学批评集《栖居与游牧之地》、《双重见证》、《无能文学的力量》、《置身其中》、《当代批评的文学方式》,随笔集《迷恋记》、《此生》、《有情》、《读书这么好的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