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残本两岸重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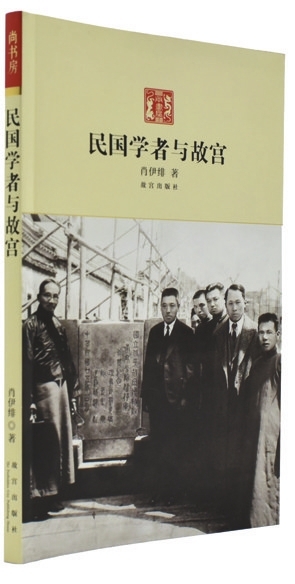
《民国学者与故宫》

叶恭绰(1881-1968)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书影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1931年“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出版,沈尹默封面题笺。
◎前世今生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1408)冬成书,全书编成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皇帝赐名为《永乐大典》。
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挑选文渊阁藏书,共装100柜,与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北京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荡然无存。自此,贮于北京皇宫文楼中的大典遂成孤本。
嘉靖三十六年(1557),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明世宗朱厚熜担心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新抄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叶,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些严密有序的举措,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重录工作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辞世时尚未竣工,直到隆庆元年(1567)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
明朝灭亡之后,《永乐大典》正本已不知下落,或称殉葬永陵,或称毁于李自成战火,总之是再没有于世间重现过。世人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也正是这嘉靖年间的副本之一。只不过,这一卷所辑录的全是古典戏文,记录的是原汁原味的宋元剧本,非常珍贵、至为难得。
其实,《永乐大典》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都是记载宋元剧本的,共计二十七卷之多。《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这一卷,只是统归为“戏”字号、凡二十七卷中的一卷,而且还是其中的最后一卷,是一部已经损失严重、很不完整的残本,但却是目前所知唯一存世的《永乐大典》“戏”字号残本。
◎迁台秘史
《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何时迁往台湾,迁台历程又有着怎样的坎坷磨难?它是怎样历经四百年劫难而又重现于世的?所有这一系列疑问,无疑皆凝聚着深沉厚重的国家记忆,理应为后世所铭记。
据史料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于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年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清廷朝臣们频繁借阅,也因之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1772)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1000册。
清代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此外,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更不计其数。其中,尤以英军抢掠最多,将其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1875)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5000册,实际缺失已达6000册以上。
另据记载,光绪二年(1876),清查大典库存数量之后短短一年时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竟只剩下800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还遭人为抢劫,翰林院所藏大典副本至此全部化为乌有。各国将抢劫的大量文物古籍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可能就在此时远渡重洋至大洋彼岸的英国。直至1920年,叶恭绰(1881-1968)赴欧洲考察实业,在伦敦一间小古董铺里,意外发现并购回了这一册大典残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已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部分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可能也恰在此时或稍早,叶恭绰也将自己从英国购回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秘藏于天津租界银行的保险柜中,以此避免意外发生,确保国宝不再流落异邦。
当时北平图书馆仅藏有60册《永乐大典》,并没有收藏《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但曾专门派人据此卷抄录了一份副本留存,当时主持抄录副本工作的赵万里(1905-1980)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是著名文献学家,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时任北平图书馆善本部采访组组长的他,正着力访求各类流散民间的珍贵古籍,因见部分《永乐大典》遗失海外,国内无存,甚为痛心,便有意将境外之《永乐大典》进行抄录,以补馆藏不足。叶恭绰从英国回购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当然引起了赵的重视,他迅即组织人力,对原本进行了精心的“景钞”。所谓“景钞”,也即“影钞”,是近于影印效果的一种人工复制,即是按照原书原有行格、篇幅、字数、字体进行全方位的一比一复制,类似于现代复印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赵万里可能还是国内最早撰文、专门介绍《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学者。赵氏所撰《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一文,并附有一页珂罗版书影,刊载于《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3、4号合刊的“永乐大典专号”之中,是年为1929年。这期“专号”中,赵连撰三篇论文,一为《永乐大典内辑出之佚书目》,二为《馆藏永乐大典提要》,第三篇即为《记永乐大典内之戏曲》。可以看到,在综述他所经历的《永乐大典》收藏、访求、研究史中,专列一文来探讨《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的相关内容,足见其对这部大典残本的浓厚兴趣。
赵万里对馆外《永乐大典》的访求、抄录副本工作从1930年代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在历时近20年的抄录工作中,经其组织抄录的这些《永乐大典》副本本身也已极其珍贵,绝大部分均难得一见,独具文献价值。从现存的赵万里所抄副本情况来看,大部分为红格誊抄本,但并非所有副本均采用原比例复制的“景钞”。究其原由,无非有两种。一是所据原本已不是明代嘉靖写本,而是清代各类官方或私人的过录本,没有必要“景钞”;二是原藏者不愿意提供原件,或时间仓促,没有足够的主客观条件予以“景钞”。
可以说,正是由于叶恭绰的慷慨无私、赵万里的高度重视,才合力促成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景钞本的诞生,这一景钞本也成为北平图书馆的重要馆藏之一。在这一景钞本的基础之上,又陆续有若干种仿钞本、精钞本诞生,均是馆方或者学者再次录副的结果,其中一种还于1954年辑入郑振铎(1898-1958)主持编印的《古本戏曲丛刊》初集,这个“影之再影”的影印本,成为大陆戏曲研究学者能够比较容易用到的工作底本,也几乎就等同于叶氏所藏的原本。那么,叶氏所藏的原本,此时又身在何方呢?
事实上,在北平图书馆景钞本诞生之后,国民政府决意古物南迁之前不久,1931年5月,由北京大学马隅卿等人发起的“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又主持铅字排印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此书就是以北图景钞本为底本校印的。为什么没能用叶氏所藏的原本作底本校印,或者说为什么不直接以原本影印出版,恐怕与当时原本根本就没在北京有一定的关系。其实,叶恭绰本人早有将原本影印出版、以广流传的想法,并没有深藏不露、秘而不宣的意思;他还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亲撰跋文,简述了原本发现经过,也提到“亟愿此书流通”“影印姑待他日”云云;在马隅卿等以北图景钞本为底本校印出版之际,他表示“乐观其成”。
或许,由于叶恭绰已经预料到了战事的危急,此时已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转移秘藏。此举虽然让后来的学者们未能一睹真容,一时也未能采取影印原本的出版方式,不得不以景钞本为底本来排印出版,这多少有些遗憾,但毕竟保全了国宝,在行将来临的战乱中及时做出了果断抉择。
1933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原先同时秘藏于天津银行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是否也随之南迁,不得而知;此时叶是否已经将此书捐赠或售予北图,也无从考证。但有一点确是可以肯定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随后踏上了飞赴美国、转迁台湾的旅途。这从时局的演进与叶氏的生平事迹来看,都可以做大致的推定。
原来,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存放在上海的珍贵图籍也因之受到严重威胁。北图代理馆长袁同礼(1895-1965)和上海办事处代表钱存训(1910-2015),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此次选取的3000种图籍中就有60册《永乐大典》。这批精之至精的善本,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又全部转运台湾。
与此同时,叶恭绰也在为保护国家文物不遗余力。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他准备避难香港,临行前,秘密将珍藏的7箱文物寄存在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就有国宝毛公鼎等重器。抗战胜利后,这批当时由军统局秘密保护的国宝,全部转交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此外,叶氏还将大批珍贵古籍和文物直接捐献给图书馆、博物馆。1943年,他将藏书906种3245册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其珍藏的文物则或捐赠、或出售,尽归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相关文化机构收藏,如《鸭头丸帖》归上海博物馆,《楝亭夜话图》归吉林省博物馆,等等。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在抗战后才露面现世的,均没有留在叶手头的珍贵文物、古籍,早在抗战前或抗战中就已经由他精心筹措、苦心操办,分散保存于当时国民政府的各类文博机构之中了。而其中独独未见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可能是唯一有资格、有便利、有机会登上避难美国国会图书馆专机的叶氏旧藏之一。
再来看1949年从香港回到北京的叶恭绰。他更为积极地从事文博事业,经其手鉴定、搜求、购藏、捐赠的文物古籍不计其数,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始终未再露面,他本人也从未提及。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抗战前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不再属于他个人,无论是其捐赠、售予或战时托管,这册书已经属于“国家财产”,登上了飞往美国、转迁台湾的航机。
关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在抗战前后的踪迹,以及最终运至台湾的这段历程,笔者的上述推测与判定后来得到了初步证实与进一步的厘清。据台湾学者汪天成教授考证,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是当年由“中央图书馆”通过中英庚款董事会,以保存文献名义购入典藏的(详参:汪天成《〈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戏曲艺术》季刊2010年第1期)。也即是说,当时的国民政府确实是从叶恭绰手中购得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使之从私人藏品化身为国之重宝,历经国难种种,终将其转运至台湾。
但与笔者推测略有出入,也更为传奇的是,《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当年并未搭乘飞赴美国的专机,而是滞留在了香港,未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转运出去。随着香港被日军攻占,它与中央图书馆寄存在港的大批善本古籍,还曾被劫往日本,抗战胜利后方才重回南京。1948年,此书终于得以与中央图书馆大批善本古籍一道迁往台湾,珍藏至今。
◎失踪传闻
1934年12月,《燕京学报》第九专号刊印了一部名为《宋元南戏百一录》的专著。书中附印了一页珂罗版影印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题为“永乐大典小孙屠戏文”。这是继北平图书馆景钞本、1931年排印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面世之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首次向公众以一页书影的方式展露真容。相信对于普通学者、读者而言,《宋元南戏百一录》让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原始影像,虽只有一页,却也着实令人惊喜。但殊不知,这一页“真容”也并非真容,只不过是北平图书馆景钞本的首页而已,因为仿照原本“景钞”得十分逼真,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就是原本。
当然,让学者们激动的不可能只是一页影印图案,更为重要的是,时年36岁的作者钱南扬(1899-1987),就此开始深入研讨一个专门的学术概念“南戏”,并为之摸索考证了七年之久。在书中,他确证了南戏曾经存在的形态与特征,而且还把后来有遗存内容的剧本一一罗列概述。
到1979年10月,已经80岁的南戏研究专家钱南扬,终于完成了其南戏研究里程碑式著作《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他在“前言”中不无感慨地提到学界中流行已久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踪传闻。他写道:
《永乐大典》自卷一三九六五至一三九九一,凡二十七卷,收戏文三十三本,详连筠簃刊本《永乐大典目录》。这本《戏文三种》,乃是仅存的最后一卷。此书已流出国外,一九二○年,叶玉甫(恭绰)先生游欧,从伦敦一小古玩肆中购回,一直放在天津某银行保险库中。抗战胜利后,不知下落。现在流传的仅几种钞本及根据钞本的翻印本,可惜见不到原书了。这次校注,即据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
钱南扬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曾经见到过《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或者至少亲自查阅过北平图书馆景钞本的知名学者。但他仍然没能逐一查阅、使用并研究《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全部内容,这也是无疑的。否则,他不会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的工作底本上退而求其次,选择“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铅字排印本。这个铅字排印本的底本,乃是北平图书馆景钞本——钱氏的工作底本,实际上已经与原本隔了两层“纱”。换句话说,钱的学术研究,没能拿到最接近原汁原味的“原本”,从古籍校注角度而言,“纯度”当然还不够,多少还是有些遗憾的。颇具意味的是,这部与《宋元南戏百一录》出版相隔已45年之久的著作之中,仍然在卷首插印了一页北平图书馆景钞本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由此可见,包括钱南扬在内的大陆学者们对该书原本的珍视与关注,随之而来的遗憾与困惑,也因此萦绕半个世纪,挥之不去。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出版之后20年,1999年,与钱南扬师出同门,同为曲学大师吴梅弟子的王季思(1906-1996),组织编撰的大型丛书《全元戏曲》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编校出自《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元代剧本“宦门弟子错立身”时,他也感言:“本剧原与《小孙屠》、《张协状元》一起,存于《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中。由于原书遗失,故这次整理,以《古本戏曲丛刊》影印的钞本为底本,参以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本。底本原不分出,为阅读方便,从钱本分为十四出。”以上这些感言得以公开出版刊行之际,90岁高龄的王季思也已于三年前逝世。他在书中的这番感言,也成为中国学术界最后一次确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失踪的说法。
这时,距离叶恭绰从英国购回《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整整80年过去了;距北平图书馆景钞本之诞生,也已经近70年了。但凡有可能亲自看到过、抄录过、校印过、研究过、接触过《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中国学者皆一一作古。叶恭绰、赵万里、马廉、胡适、吴梅、傅惜华、唐圭璋、冯沅君、任中敏、谭正璧、钱南扬、王季思等,皆相继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而《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的下落依旧还是个谜。
随之而来的阅读与研究状况是:在中国学者视野中,《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失踪70年了,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到北平图书馆景钞本;接下来,“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也不多见了;再接下来,只能查阅《古本戏曲丛刊》中的“影之再影”的影钞本;到最后,钱南扬所著《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成了最为常用的通行本。
◎重现台湾
距钱南扬所著《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出版之后30年,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台湾嘉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发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论文,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即《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明代嘉靖年间内府重写本)并没有失踪,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即原“国立中央图书馆”)。
原来,台湾学术界也曾根据钱南扬所言,一直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已经失踪的观点。但汪天成坦言“一直还心怀侥幸,希望能再看到原书”,寄希望于在大陆或海外寻求原书。接下来,一次因备课查寻资料的偶然机遇,竟意外让这册“失踪”已近一个世纪的国宝重现。他在论文中激动地写道:
后来在备课时,因为要讲到包背装,需引用台湾“国图”的《术语图说》来解说,可是一点开之后,图例竟然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我顿时愣住了。由于是远景看不真切,于是赶快去查“国图”的馆藏目录,结果真找到《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而且看到了更清晰的图。就这样我还不放心,特地再到“国图”去看了微片和原书,确定真的是《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惊喜之余,出于学者的审慎,汪天成再次逐页逐字检阅原书。由于担心这并不是明代原本,而是另一种未经著录的景钞本,他甚至于核对了明代原卷抄录者吕鸣瑞名下的现存所有《永乐大典》抄录笔迹。他将《永乐大典》卷六六六、卷二二三七、卷七三二四、卷七五一八、卷七六七七、卷八九一〇、卷一二三六八、卷一九七九一等多卷字迹逐一核对比照,最终确定了他在台湾“国家图书馆”中见到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正是明代嘉靖年间内府重写本,也就是当年叶恭绰从英国购回的原本。
此时,已经被中国学术界宣称“失踪”达80年之久的《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终于重现于海峡彼岸。据汪天成初步研究,这部原本的内容,与此前流行于学术界的各个版本均有较大差异,无论是景钞本、排印本、影印本、校注本还是各类辑选本,都存在或多或少、程度不一的错讹与脱漏,这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持续而且深远的。可以预见,《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在台湾的重新发现,将重新厘清相关研究中的一些误区,重新建立起新的、更为精确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这必将掀起新一轮的相关研究热潮,诞生新一批的学术研究成果。这次神奇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原本的学术价值,当然毋庸置疑。
(本文摘自《民国学者与故宫》,肖伊绯著,故宫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定价:3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