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诗人郑小琼和她的《玫瑰庄园》 这个时代的“慢写作”——诗人郑小琼访谈

郑小琼:女,1980年6月生,四川南充人,2001年南下广东打工,有作品散于《人民文学》《诗刊》《独立》《活塞》等。迄今出版诗集《女工记》《黄麻岭》《郑小琼诗选》《纯种植物》《人行天桥》等十部,其中《女工记》被喻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关于女性、劳动与资本的交响诗”,有作品译成德、英、法、日、韩、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语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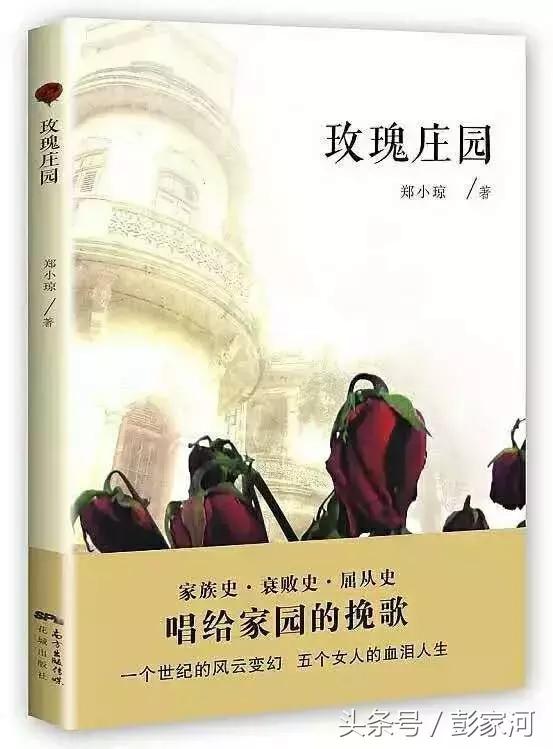
郑润良:小琼你好,祝贺你的新诗集《玫瑰庄园》出版!今天我们一起来谈一谈这部诗集以及相关的话题。
郑小琼:润良你好!
郑润良:据说这部诗集是从2003年开始创作的,我想读者和我一样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部与家族记忆相关的主题诗集?
郑小琼:写作《玫瑰庄园》完全偶然。2001年我从四川来广东打工,开始写诗,大部分以怀乡为主。2003年,偶然看到潘鸿海先生的《外婆家》,刹那间内心涌起很多往事,莫名地怀念四川老家,美丽而怀旧的旧宅,记忆中外婆家的老宅子被拆掉,很有韵味的蜀地建筑,青砖黛瓦,苍树翠竹,阴翳的窗下青苔布满地砖,老式的水井,笨拙的辘轳……它们正一点点消逝,连同像外婆那一代的老人,我突然思念外婆。外公家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娶了数房妻子,外婆最小,几房妻子又各自生育了儿女,除了生育之外,他们还各自领养了儿女,比如我外婆,自己生育了三个女儿,两个儿子,还领养了一个儿子。外婆经常说起外公家的往事,当我看到潘先生的画,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虽然潘先生画的是江南,但是在我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熟悉的乡愁。受画中的意境影响,我想写一组关于四川家族记忆的诗歌,于是开始写《玫瑰庄园》。就像若干年后,我再读到潘鸿海先生的另外一幅油画《又回外婆家》,我一直觉得那位姑娘与我有着太多的重合,而那位姑娘背后是弯桥、流水、斑驳的灰墙,正在我们的记忆中消逝,它们曾经是我们血液中的乡愁。我想写一写这些在时间中消逝的记忆、生命、万物,诗歌的情感能穿透时间与空间,诗句间绵延的低沉是对过去的记忆甚至是因为茫然而失忆,用记忆的触须能抵达外婆那一代人内心,在传统、自然与个人经验中感受生命的自身,它的低沉曲调并非虚无,而是生命被压抑下的隐痛,它们构成了我的这部诗集中的主题。
郑润良:我知道,也是在2003年,你创作了一部对你个人而言很有意义的长诗《人行天桥》。你说过,在长诗创作方面受到了发星、海上、周伦佑等人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他们的作品对你的创作理念和长诗创作的具体艺术层面的影响。
郑小琼:海上是一位很优秀的诗人,周伦佑是“非非”的创始人, 两位写了大量杰出的长诗。我2002年接触到海上老师的诗歌,诗人发星寄给我,他的诗打开我的诗歌视野,让我的诗歌风格有了巨大的转变。在之前,我写的主要是乡愁主题的诗歌,语言也比较传统守旧,接触他们的诗让我的诗歌从语言上到思维上都有比较大的改变。2003年,在他的诗歌影响下,我创作了《人行天桥》《完整的黑暗》《内心的坡度》等一批长诗,同年也开始写作《玫瑰庄园》。周伦佑老师的《象形虎》在诗歌技术上给我不少启示,比如修辞、句法的转换、诗歌的思辩、解构等。两位老师都写了大量的长诗,而他们长诗的结构影响了我的写作。
郑润良:在80后的诗人中,你应该是迄今为止得到最多认可的诗人。张清华老师在为你的诗集《纯种植物》的序中对你的诗作做了高度评价,“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诗篇使词语、信念、价值这些虚妄的事物在我们这个狂欢和娱乐的时代废墟上得以幸存,使诗歌保有了令人仰望的品质和尊严。除了赞美,我别无选择。”能否谈谈你和张清华老师、谢有顺老师等评论家相识交往的具体过程以及他们在你创作《玫瑰庄园》这部作品过程中的影响。你觉得评论家和作家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郑小琼:两位老师在我诗歌成长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张清华老师是最早写关于我的评论的评论家之一,在十多年前,张老师写过一个评论叫《当生命与语言相遇》,谢有顺老师写过《分享生活的苦:郑小琼的写作及其“铁”的分析》,两位老师的评论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的诗歌,而两位老师十几年前对于默默无闻的我的鼓励,让我对自己的写作有了自信。他们两位是很值得信赖的老师,我在写作《玫瑰庄园》时遇到了困境,我曾写信给两位老师,他们各自推荐了一些书给我阅读,如果以前的阅读是比较零散的,而两位老师的推荐,让我的阅读有了系统性,比如我的另外一部诗集《纯种植物》,便是由两位老师推荐阅读后写出的,如果没有他们推荐的书籍,也许不会有这部诗集。好的评论家与作家之间,既要有对文学的深度与美感之间对手般较量,也需要有朋友般的对文本的“新感受力”的发现,在朋友与对手间寻找平衡,我们要避免朋友间无底线的“表扬”,也避免对手间无底线的“酷评”。
郑润良:这些年你在《作品》杂志主要的关注点也是编辑长诗,能否介绍几篇你个人特别喜欢的长诗。你觉得长诗写作在这个时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郑小琼:比如我编过的长诗里,我很喜欢陈先发、格式、周伦佑、孙文波、伊沙等人的长诗。我曾连续数年发孙文波的《长途汽车上的笔记》,这组长诗是孙文波为我们时代贡献的杰作,让我想起杜甫的在夔州时的诗歌,特别是《秋兴八首》时的杜甫风格,它们应该是这个时代诗歌最重要的收获。比如我编伊沙的诗歌的感受,我一直把伊沙与很多口水诗区别开来,是因为伊沙在口语诗中建立起了他内心深处对生命的关怀与爱憎,特别是细节处呈现对人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的关怀,正是这个基础才使得伊沙的口语诗有了诗歌的品质,很多复制伊沙的人沦为口水诗是因为缺少这个基础,二者之间的差异让我想起中国诗歌史中的“乐府诗”与“打油诗”之间的区别。
郑润良:这部作品从2003年开始创作,2016年才完成。这么长的创作时间中,你觉得自己主要是为了应对哪些方面的障碍?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自己已经突破关键性的难题?
郑小琼:这部诗集伴随我诗歌写作的成长,第一个十六首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创作了前八首诗歌后,我还没有完全架构好整部诗集的结构。随着我的阅读扩大以及诗歌视野的开阔,大约一年之后,我再重新阅读这组诗歌,我知道自己需要写一个四川家族的长诗,特别是与女性有关的,我开始写第二个八首,在第二个八首中,我确定了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比如诗歌的分节、长度,以及风格,我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中外诗人在诗歌体例等探索性的诗歌,确定了这部诗集的形式,比如节与行,长度,有意识地进行控制训练。后来,当我完成了前四十二首时,我觉得需要深入那个时代背景,了解各种专业知识,比如花草树木、建筑物的风格等。这部诗集有两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是2004年,我确定这部诗集的整体风格,另一个是我遇到瓶颈时,诸多老师的帮助,让我继续将这本诗集写完。
郑润良:你说过你的诗歌受到了先锋诗歌的影响,你是怎么理解“先锋”这个概念的?你觉得自己的诗歌是先锋诗歌或者说你的创作是以“先锋诗歌”为目标的吗?
郑小琼:我认为先锋诗歌需具备中两个条件,“在破坏中建构,在建构中拓展”,破坏旧有的体制、规则、秩序等,破坏的同时需要在探索中建构,建构的目的是为了拓展诗歌在语言与美学的疆域,太多的自诩为先锋的写作只有破坏,没有建构与拓展。我自身也在努力地拓展与建构新的美学或者语言上的疆域,朝此前进,比如《玫瑰庄园》对诗歌体例表达上的探索,在打工题材的写作,对固定审美的词语与意象,比如对“铁”“雨水”等美学意义的拓展,在诗歌中我努力将一些词与意象冲破以往固有的条条框框的樊篱,探索事物与语言的可能性,拓展事物表达的疆域。
郑润良:《玫瑰庄园》这部作品花了大量篇幅书写五位祖母的情感世界,为什么要以这么大的篇幅来塑造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这与你这部诗集总体上要表达的家族记忆以及时代之痛有什么关系?
郑小琼:《玫瑰庄园》是一本以女性为主题的诗集,表述了对五位祖母、我自身、以及女性在现实世界中不由自主的命运,包括男女的不平等,女性婚姻、人生的不幸,甚至因为性别带来的生命的不幸。《玫瑰庄园》有一首溺死女婴的诗歌,在生命的哀歌与痛哭中,性别带来的不平等,或面对饥饿“偷粮妇人避难他乡”,这种避难饱含着复杂的情感,有的女性被用很少的粮食为聘礼为名几乎等同于卖到他乡,面对时代洪流,女性生命如此不堪。在几个祖母的身上,她们有的出身富裕家庭,有的有一技之长,有的进过学堂等等,命运却殊归同途。外婆在世时,常说家里穷,嫁给外公只是想有饭吃,为了果腹之餐而嫁给外公。结果没两年,就解放了,果腹之餐没有了,却跟外公不断地接受批判。在虚构与现实之间,《玫瑰庄园》构成了我对中国传统家族的叙事。它们来自诗歌中描写的飞鸟、植物、星辰、亲人、乡村、建筑,从一个小小的庄园间出发,抵达那个时代的记忆,构造自己诗歌的呼应与回响,从小小的庄园中感知历史与时代的冷暖。
郑润良:除了几位女性形象,作品中祖父、二伯父等几位男主人公的形象和命运也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对这些男主人公,你在形象设定方面有什么样的前期思考?
郑小琼:在《玫瑰庄园》我先确定祖父这个形象,祖父这个形象也来源于外婆说的几个人物原型糅合,为了塑造这个人物,我找了不少当时四川人留日的资料,有官费出国,也有自费出国。四川人内心有 “一出夔门天地宽”的理念,实际清末新政之后,川人出国极多,在1906年时,川人留日的人数占据十分之一强。原本书生报国,却不曾在时代的潮流间,书生报国无门,却只能居乡,日益堕落。在祖父与二祖父身上,我看到了时代的悲剧。
郑润良:很多没有细读你作品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你的成名只是近年“诗歌现象”之一,认为你只是占据了题材、经历等优势,而没有看到你在诗歌艺术形式层面的努力与天分。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你的许多作品即便仅从文本的意义上看,也是技术含量很高、挑战性很强的作品。从2001年开始正式写作,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在诗歌创作上就有这么大的飞跃,不能不说你是有些天分的。除了天分,我更感兴趣的是你个人在这方面做了哪些特别的努力,有哪些独到的感悟让你快速成长?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自己的作品与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了?
郑小琼:我是一个做事很缓慢的人,也是一个很笨拙的人,但在写作上我一直有自己的计划,我会努力地朝着自己的方向掘进,因为笨与缓慢,外界对我的影响比较小。比如《玫瑰庄园》这部作品,十几年,就是这样写着,慢慢儿写,坚持,有些事情就成了。我并非那种有独到的感悟一下子快速成长的人。在我的写诗人生中,我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比如周发星等,他的出现让我的诗歌有了重大的转变。我是缓慢地成长,一些早期的打工杂志可以找到我早期的诗作,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我一步一步成长的过程,在《人行天桥》前,我曾写过《自叙者》,这个长诗现在看来只是一个半成品,正是因为它,才有后来的《人行天桥》等。
郑润良:具体到《玫瑰庄园》这部作品,在形式、结构上显然你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和思考,可以感受到古典诗词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
郑小琼:是的,我努力的探索诗歌的各种可能性,比如打工题材诗歌对工业化词语与意象的运用,如何将一些工业的物象与词语入诗,比如水泥、电脑、钢筋、锣钉等,如何让它们具有诗意,或者在诗歌中闪光,美国的语言诗,美国的查尔斯·伯恩斯坦的诗歌在这方面有过探索,我曾托人找到他的邮箱,交流了我的一些看法。在《玫瑰庄园》更多的是探索在现代诗中如何融合中国古典与传统,温和而优雅的用词风格,中国古代诗人喜欢用典故,在这部诗集中,我也用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典故。我希望在自己每一部诗集中都有自己探索的呈现,比如在诗集《黄麻岭》探索对“铁”“雨水”“锣钉”等工业词语在现代诗歌的美学意义,在《女工记》中继承中国古典乐府诗、古典文体“记”以及诗经中的“风”等叙事结构,在《纯种植物》探索如何恢复“大词”的尊严与纯粹。
郑润良:我一向觉得历史感对于青年作家是尤其重要的,我们必须努力去探询和理解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时代中的方位。相对于以往的关注当下现实的作品,《玫瑰庄园》显然把重心移向了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你个人是如何理解这部作品在你所有作品中的意义的?
郑小琼:它只是我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在写作《玫瑰庄园》同时,我在写一部叫《七国记》的诗集,这部诗集一共七首,我完成五国了,其中《魏国》已经收录在我的诗集《郑小琼诗选》中,这是一部纯粹以历史为主体的诗集,我希望透过历史来看现实,看人,看到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悲剧。
郑润良:你的写作总体上都是属于“慢写作”,在功利主义氛围弥漫的时代,这样的创作态度让人敬佩。完成《玫瑰庄园》后,你还要什么样的写作规划?
郑小琼:除了上面《七国记》之外。我还计划写一部的乡村诗集,虽然今年我将出版一本乡村诗集,青年诗人王东东写的序,这个主题上我可以挖掘得更深入,呈现一些不同的视角,我想重新认识传统,比如中国大地那些在缓慢消逝的事物。
郑润良:向这个时代的“慢写作”致敬,谢谢小琼!
郑小琼:谢谢润良!

郑润良,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后,《中篇小说选刊》特约评论员,《神剑》《贵州民族报》《人民文学》醒客APP、博客中国专栏评论家,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文学评论高研班学员。《中篇小说选刊》2014-2015年度优秀作品奖评委、《青年文学》90后专栏主持。
玫瑰庄园(节选)
郑小琼
镜子
园间春色浅,镜里伤心深,流水有点
遥远,青鸟未传佳音,我隐身书页
春寒浸满幽居的孤独,祖宅门上镜子
充满象征与暗喻,肃穆的寒意与古怪
从镜中打开玫瑰庄园,在玻璃水面寻找
深不可测的命运,穿过虚构的门与小径
邂逅美丽的空间与秩序,祖母们在厢房
念经、唱戏、刺绣、读书,后院花已开
前堂太师椅,祖宅居住初春黎明与晚秋
深夜、祖父的胆怯,树木回忆飞鸟,鸳鸯
嬉水蜀绣,三祖母梦见缀饰荷包,下午
我从镜中返回现实,它已悬挂大门的上方
镜子有符咒、巫术与迷药,门框刻老虎
狮子和怪兽,三祖母眺望诗中的鱼、鸥鸟
和远帆,细雨淋湿月亮,时间坚贞悲怆
岁月慵懒,潜泳渡过悲凉的河流,遇见
迷雾与桃木梳,镜中浮现祖母芬芳的寂寞
镜子深处居住死于非命的亲人,镜子囚禁
鬼魅与不详物,我想揭开镜面,偷偷看眼
镜里世界,真实或虚无,它灵异的避邪术
涨死井中的大伯父,他在镜底的哭泣
吊死屋梁的三祖母,我幻想她单薄的身影
他们在镜中等待我,玫瑰不开,忧郁不去
我在后院搭长梯,寻找镜中的玫瑰庄园
雨水
瘦小的心熔化柳树与松色,窗外雨声
有人敲门点灯,有人尖叫恶梦,黑夜
陷落成楼梯,谁在登楼,谁在盘旋
雨推开乌云积聚的青天,墙外行人
他在等谁,微雨淋湿心,红烛孤床冷
栀子含泪,蔷薇横卧东风,雨水在外
徘徊,她在庄园听雨,衰老的天空
面目全非,衰竭的云朵步履艰辛
雨水随台阶延伸,浸湿她的耳朵,它运送
雾与繁星,从菊花里取出秋天与熟悉的
脚步,去年在园外站立,雨打新柳,鸟啼
旧梦,蝙蝠刺疼檐壁,我在祖宅点灯读书
寒烟小院,疏灯虚窗,祖母们用雨水叙述
她们的声音隔得远,细雨余微寒,我写诗
饮酒、听风,考证红漆家具与雕龙太师椅
往事若星迹,此刻还有谁在等候,雨未停
啊,一切都已变迁,她们消逝窗外的竹林
我在纸上写下旧日的装束,祖父疾病缠身
祖母们平和而亲切,韶华似流水,想想她们
伤心便遍布全身,推门见冷雨、落叶、乌云
有人在雨中咳嗽,他把光阴嫁给大烟与疾病
世俗诟病季节与眼泪,也轻视松色与竹林
我的诗歌寻找到失意的屋顶,它缓慢的孤独
布满阁楼,雨水潜入祖宅的身体,悄无声息
册页
门庭若古老册页,雨燕翻阅屋梁悲喜
春天的蛇腰在墙外游动,我把它唤
柳条,也唤她小小乳名,庭院深井
睁开清澈眼睛,诵读雨淋湿的诗篇
她吹熄灯盏,打开窗棂,让月光进入
房间,它用清凉的孤寂洗涤她的脸
琥珀般面庞,透明,囚禁她的羽翼
惊蝉像白马踏碎青瓦,有人穿过旧楼
远去,有人雕床抽烟做梦,她成为小小
俘虏,为脆弱的悲剧增添废墟般记忆
庄园大门布告她的生活,三房姨娘
退回幽闭院墙,诗歌换成五彩蜀绣
月光不再是白哗哗的银子,可以换酒换诗篇
她读懂月光是夜晚的幻觉,习惯用寂寞擦亮
栩栩如生的往昔,它们开始丧失,游行的
背影模糊,新闻有些泥泞,她在房内踱步
窗下停伫,空荡荡的时间究竟要用什么填空
她还保留成都学堂的理想主义,尘世的庄园
只需享乐与容忍,大家闺秀或鸦片中吐雾
算盘,丝绸,阴云般面孔,骨骼里烦恼
她不习惯用黑夜或白天覆盖生活,理想与信仰
固执而坚硬,一寸一寸刺痛她肉体,在小镇
连月光也有烦恼与忧愁,她读不懂门庭册页
把命运埋进月光中的横梁,像诗句的迷茫
祖母
清瘦的冬天剩下梅花与酒,夜半清冷
有人踏雪远行,消逝窗棂,有人围住
炉火,抽烟打盹,郊外苍山负雪,院间
枯枝开花,冬天剩下积雪、白菜、浮云
有人送来春日的爱情与燕子,有人带来
冬夜的孤冷与黄金,你将美色封在园中
把燕子寄给远方,剩下落日、忧伤布满
玫瑰花园,从此爱情似流水,随嘉陵江
去了远方,你还在等待什么,起身遇见
明月的碎片与坠落树林的星辰,暗红的
蜀锦蓝色的鸳鸯,窗帘隔开冬夜与佃农
烛灯,用力阻挡破门而入的回忆与黑暗
旧事一件件,让你消瘦、痛苦,日子似雪
一瓣重复另一瓣,坚硬飘逸,灼痛怀爱的心
依恋过的面孔与姓名,已依稀而陌生,你的
悲哀细腻,霏雪掩没往昔,春日淹溺镜中
你把自己安置在心碎的角落,几十年后
我返回祖居,捡起你碎了的心,它苦涩
孤单,啊,它们仿佛在梦中叩门、行走
叹息、痛苦,在纸上生活,现实主义的雪
将爱情冻伤,你和我,隔着女权主义与
女性主义,我们隔着数十年前的冬雪
地主与佃农,失眠的细节经历你稀薄的
人生,我坐在庄园冥想祖母们的爱情
人生,我坐在庄园冥想祖母们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