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然《独龙花开》:情系独龙江 孜孜著长卷
![]()
吴然和孩子们。冯牧笔下巴坡小学旁古老的藤索桥,如今已是安全牢固的钢索吊桥。

“小小梦之队”在校园里认真练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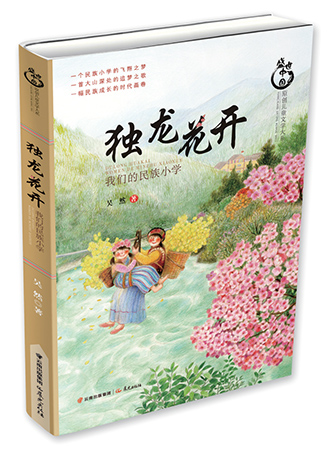
记者:《独龙花开》是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您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是什么?
吴然:说到写这部作品的初衷,不由得让我想起30多年前的1981年。当时,我买到冯牧前辈的一本散文小集《滇云揽胜记》,读到他在1974年8月,由作家、诗人张昆华和怒江军分区战士陪同,跟随马帮,在开通不久的人马驿路上“拄杖而行,夜宿窝棚”, 整整走了三天,翻过高黎贡山,来到了独龙江。冯牧在当时的乡政府所在地巴坡,看望了兴建于1956年的独龙江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巴坡小学,他说他“爱上了独龙江畔的第一个小学,以及小学旁的那座古老的藤索桥,当小学生们走过桥面时,他们摇晃得好像打秋千一样……”这些朴素的文字,让我感动。我知道,正是这所小学结束了独龙族刻木结绳记事、目不识丁的历史,让独龙江听到了孩子们读书的声音。当时就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去拜访这所小学呢?1985年4月底,我到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采访,很想借这个机会去独龙江一趟。朋友指着高黎贡山白茫茫的积雪说,通往独龙江只有惟一的一条人马驿路,现在被几米厚的大雪封冻着呢!朋友告诉我,在大雪封山将近大半年的日子里,独龙江的人出不来,外边的人也进不去。我只好带着遗憾离开贡山。
多年来,我到过云南边疆许多地方,走进过许多民族小学,认识了不少各民族小朋友和老师,也写过一些有关民族小学的散文,其中《我们的民族小学》作为课文,选在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第一课。每当我走进村寨里的小学,同学们都争着问我:《我们的民族小学》这篇课文是不是写他们学校的?这时候,我就更想去还没有去过的独龙江,更想去见见独龙族小朋友。这简直成了我的一个心结。直到2006年,我已经退休了,才和一群朋友到了独龙江。第二天,老县长高德荣就带我们去看巴坡小学。这个小学已经很破旧,门窗都损坏了,小小的窗子没有一扇镶着玻璃,而是用木条钉着。几间窄小的教室,学生不多,老师正在上课,我们走进去要好一阵才能适应室内的昏暗。老县长讲,他小时候在这里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以后又在这里教了五年书。我拍下了悬挂了半个世纪的校牌,同学们都争着看我的数码相机里有没有自己。中午吃饭时,我们吃洋芋、包谷,喝着没有放油的鱼汤。从独龙江回来后,我以《巴坡小学》为题写了篇散文,发表在2007年2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
我一直牵挂着独龙江,牵挂着独龙江畔的小学。
2014年元旦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就云南省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做出重要批示:“获悉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十分高兴,谨向独龙族的乡亲们表示祝贺!独龙族群众居住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我一直惦念着你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希望你们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以积极向上的心态迎战各种困难,顺应自然规律,科学组织和安排生产生活,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早日实现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梦想。”
可以想象,如此巨大的喜讯和温暖传到独龙江,是一种多么欢腾的情景!而我也想要找机会再进独龙江,好好为独龙江写一本书,交出一份情系独龙江几十年的儿童文学作家的文学答卷。应该说,这就是我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吧!
记者:《独龙花开》中展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独龙族的民族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比如独龙族的歌谣、独龙毯“约多”、溜索以及独龙江峻美的自然风光等,读完作品就像看完一幅生动的独龙族历史文化长卷。为了写好这幅长卷,您在写作过程中,都下了哪些功夫?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哪些?
吴然:在动笔之前,特别是写涉及少数民族、历史、地域、文化等内容的较长的作品,每个写作者恐怕首先都是在努力扩充和丰富自己相对欠缺的知识。我也一样。我先挖掘自己的阅读记忆和现有的知识储存,把从阅读中发现的线索随时记下来。再系统地到图书馆和资料室有目的地借阅、查寻相关史料,包括地名志、植物志、动物志和教育志,收集各民族主要是独龙族的童谣、民歌、神话、传说,以及民族服饰、节庆、礼仪、宗教信仰和民族风情、生活习俗等等。同时也请教一些民族学和民俗学学者,特别是独龙族学者如李爱新、罗荣芬,还有著有《独龙族文学简史》的李金明等等。这些案头工作都是必要的写作准备。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我深感独龙族过去的苦难深重。而今天,他们正为“早日实现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梦想”,做着怎样的努力呢?这就要实地深入生活“眼见为实”。
2015年9月,晨光出版社潘燕副社长安排第五编室主任张磊陪同我去独龙江深入实地采访。我们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府六库约上州教委的杨李明老师,到贡山县城后,又拉上“和大姐”和丽芬老师,穿过6.68千米的“高黎贡山隧道”,三个多小时就到了独龙江。高老县长正要赶着去指导村民种草果。见到我,以他特有的风趣笑着说:“我正想着,这么久你怕是要来了啰……你自己看好啰!我还有别的事……”朝我一笑,就匆匆走了。
我和几位同行者流连在独龙江畔,倾听它流淌的故事和歌谣,触摸它奔跑的脉搏和心跳。走村串寨,拜访已经越来越少的文面老人,和正在院子里织约多(独龙毯)的独龙族妇女交谈……
一个来江边背水的小姑娘,并不忙着往竹筒里灌水,而是采了杜鹃花花枝,给自己做了个花冠戴在头上,左看右看映在江水里的影子。她告诉我,她叫阿普芬,读五年级了,是中心学校的学生。她要烧水给阿比(奶奶)洗头、洗澡擦身子。
独龙江下游的“马库国门小学”有许多缅甸的孩子来上学,很多孩子都有亲戚在独龙江。“小导游”龙雨飞的小表妹木子玉,就在国门小学读书。她告诉我她来报名读书的时候,请老师给她起个笔划少的名字,老师想了想说“木子一”笔画少,你是女孩,缅甸出玉,就叫“木子玉”吧!她说,她高兴得亲了老师一下……
和大姐告诉我,她当老师时,第一次自己过溜索,到了溜索中间就不动了,“像一个葫芦挂在摇摆的溜索上,生生用手‘走’过去,满手都是血……”
梅西子校长陪我在学校里转悠,她说怪得很,刚到中心学校几天,她随便就能叫出学生的名字。一个抱着篮球的同学告诉我,他们校长有“妈妈味”……
所有这些都成为我难忘的记忆,并在书中有所展现。
记者:您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他们各自的生活串联起整部作品,从不同人物的视角来展现不同的主题,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结构?
吴然:起初也不是这种写法。我甚至想写成一部童话作品,让独龙江“自己讲述”,还有意加进现代生活元素,让浪花们互发“微信”。写了一些,觉得忐忑。发给好友、批评家冉隆中,被他批得一塌糊涂。我认真地思考了冉隆中的批评,翻着采访本,如同梅西子校长说的,像“找羊肚菌”(一种野山菌)那样去发现,去认识。也从采访记录中重新回到现场,回到水声喧哗、争相向我诉说的独龙江……于是我调整了思路,抓住教育这个“牛鼻子”,从独龙族第一个识文认字的孔志清写起,从点燃独龙江文明火种的第一个小学——巴坡小学写起,一直写到中心学校的“小小梦之队”到西安参加“2015‘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比赛夺得奖牌……我找到了一个切入点,那就是独龙江小学(也许是边远山区许多小学)的一个特点:“放月假”。这是因为独龙江小学都是全日制寄宿学校,又因为学生离学校一般都比较远,实行的是“月假”,也就是一个月放三次假,10天一次,假期三天。在雨水多的季节,也会个把月放一次八九天的“月假”,在路远的村寨,老师还要亲自把学生安全地送回家。
梅西子校长告诉我,独龙江小学没有“家庭作业”。所有的作业,都在学校里在课堂上完成了。独龙江小学生的书包很轻。但是,在放“月假”回家的时候,梅西子要求老师也给学生布置一种“不带书包”的“家庭作业”:劳动、保护环境、改变不良习惯。正是这一点,让我“豁然开朗”,把学校和社会紧紧结合起来,把视野从学校拓展到家庭、自然等等,并由此有了用文学表达习总书记2015年4月考察时对云南的“三个定位”(“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的可能。于是就有了利用“月假”给奶奶沐浴、听奶奶讲“文面”的阿普芬;有了用诚实劳动挣钱的“小导游”龙雨飞,向妈妈学织约多的木琼花以及和爸爸“守秋”放了小麂的阿木支,等等。写作中,大事不虚,小处不羁,有的地方还带有儿童视角的观察与想象。方卫平认为,由此写出了一个民族今天的成长故事,孩子在成长,大人也在成长,交织着“无数大人和孩子成长的身影”。儿童文学评论家李利芳所说,这种似散而聚的结构“拓展了我们对纪实儿童文学这一文体的既定想象,丰富了原创儿童文学各文体类型的创作”。
记者:您描写了独龙江畔巴坡小学、独龙江中心小学老师与孩子们的生活学习经历,也写了独龙族的教育发展历程,更书写了独龙族从弱小愚昧走向文明开化的过程。您觉得,教育对于独龙族这样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来说,其最重要的意义或者说特殊性是什么?
吴然:我一直关注边疆的民族教育。一个民族的发展进步,特别是人口较少的“直过民族”,教育至关重要。以独龙江来说,如果没有1956年建立的巴坡小学,那独龙江和独龙族会是什么样子简直不可想象。正是这所小学的建立,在这里播下知识和理想的火种,并渐渐漫延开来,改变着独龙江和独龙族同胞,使整个独龙江焕发出朗亮的神采。当然,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这一点,老县长高德荣深有体会。他曾向梅西子倾诉了一些“糟心的事”:他怎么也想不到,想不明白,发给村民的核桃树苗,还专门有人反复做栽种示范,有些人家竟然不挖坑栽种,一直堆放在墙角,甚至丢在房头上,成了烧火的干柴!专门组织人为家家户户修了猪圈、厕所,尿尿屎屎的还是老往江里倒。外表崭新的安居房,一进屋还是臭哄哄的……还有酒,一个个喝得昏天黑地,什么正事也干不了……他得出结论:“说一千,道一万,最后化成两个字:教育!”
独龙族是个“直过民族”,但是教育不能“直过”。要实现独龙江的梦,最根本是教育。老县长说得不错,教育扶贫是一种特殊的精准扶贫和精神扶贫。当然,各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这就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要给予保护和传承。在云南,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都要翻译成18种少数民族文字,进行双语教学,这也是保护民族文化的一种教育形式。
记者:您为什么选用纪实性文体这种表现方式?在您看来,纪实性儿童文学是否更偏重于书写社会、历史等宏大题材,如何在书写这些宏大题材的同时又在作品中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
吴然:我以前主要给孩子们写作短小的散文,当然也写过如《小霞客西南游》那样的长篇游记。游记应该说也是一种纪实文体,记录的是作者的旅途见闻、感受等等。但和我这次写《独龙花开》又有不同。游记是在见闻中直白地抒发作者自己的感情,而写《独龙花开》则要把作者的感情转化熔铸给所写的人物。虽然纪实性儿童文学并非都偏重于书写社会、历史等宏大题材,但是《独龙花开》还真以文学表达的形式涉及到如习总书记的批示和关于云南的“三个定位”这样的重大题材。也如丹增老友在他审读本书时所说,这就需要“相应的篇幅和体量”来承载,并采取了如他所说的 “寻找足迹”的写法。也就是深入实地考察、体验,努力融入你要写的人物之中,了解他们而成为他们的朋友,这样才能把他们写活,最终通过他们去感染读者,打动读者。我想努力这样做。但是,我不敢说我做到了。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作品入选课本最多的作家之一。《独龙花开》的语言清新质朴,富于画面感,江水和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您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对于作品的语言有着怎样的自我要求?
吴然:冰心老人在给我的一封信上说:“给儿童写散文不容易,要有童心。你的散文小集朴素自然,我很欣赏”。郭风前辈为我的一本散文集作序也认为,我的散文“既朴素,又写得生动,富有儿童情趣和教育旨趣”,又说“十分难能可贵的”是我写的“毕竟是儿童散文,是写给孩子们看的真正的儿童散文”。我知道,这是两位前辈对我的教诲和鼓励,其中对语言的关键词:朴素、自然、生动,以及“要有童心”,要“富有儿童情趣和教育旨趣”,都是我努力的方向和文学追求。同时,我也努力用新鲜的语言写作。希望通过语文课和阅读,把我们美丽的母语种植在孩子们的心里。
记者:云南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您看来,云南的儿童文学作家在书写民族故事和富于民族特色的作品方面还有哪些可以作为之处?
吴然:诗人徐迟曾经用“美丽·神奇·丰富”六个字为云南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这六个字也蕴藏着极其宝贵、无可替代的儿童文学资源。因此,云南儿童文学曾经以“太阳鸟”作家群的亮丽飞翔和鸣唱,为丰富中国儿童文学艺术宝库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天云南儿童文学又吹响了再出发的集结号。有意思的是,早年的“太阳鸟作家群”是以男性作家为主力在冲锋陷阵,而今天的新一代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则是湘女(陈约红)、汤萍、余雷、刘珈辰、李秀儿、蒋蓓、沈涛、和晓梅等女将们撑起了一片天。我相信,如果年轻的作家们加强文化自信,真心实意深入生活,发掘好用好“美丽·神奇·丰富”的儿童文学宝藏,开拓创作疆域如绘本、图画书等,云南儿童文学定然会让书写富有特色的民族故事再放异彩,给读者带来惊喜,给儿童文苑带来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