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冷静的历史是无法失落的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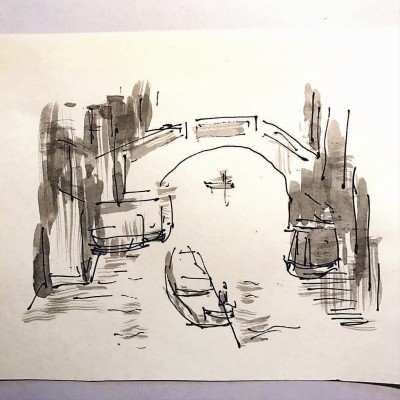
作家金宇澄继长篇小说《繁花》摘得茅盾文学奖后,日前推出非虚构力作《回望》杂糅个人记忆、家族历史和时代风云
这是一部纪念“我的父亲母亲”的记忆之书,也是作家回望历史后的回声。继长篇小说 《繁花》 摘得茅盾文学奖后,金宇澄的又一力作 《回望》 日前出版。书写父辈故事,如何避免流于一地鸡毛,又能窥见历史的鲜活面貌? 金宇澄的做法是,采用我、父亲、母亲三种不同的叙事角度,交织大量信件日记等私人记忆,展开枝蔓丛生的讲述。
“三个部分相互有重合,也有间隙,线条不一致,我觉得这种状态蛮好。就像我们听一个人说这件事,换一个人讲,说不定又是另外一种说法。”金宇澄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说,记忆与印象,就像泥土中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有枯萎和干瘪的过程,“如果你疏忽它的特殊性,它们将消失,而冷静的历史,仅是巨兽沉重的骨架,或许是无法失落的遗迹。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就在日前的思南读书会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评价说,《回望》在某种意义上可看成 《繁花》 的前传,从大体的时间线来看,《繁花》开始的部分是 《回望》 即将结束的地方,两本书合起来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一些被历史长河所裹挟的细节,如涓涓细流般重新被找了回来,站在河岸的人,无法忽略水面闪烁的岁月光影。
三重视角交错,编织有体温的家族叙事
《回望》 的雏形,是2015年第5期 《收获》 刊发的专栏文章 《火鸟:时光对照录》。金宇澄在文中回望了父母的青春———曾叫作维德的进步青年,从故乡江苏黎里小镇走出,抗战前夕加入中共秘密情报组织,他与爱好文艺的进步女大学生邂逅,历经生死离别。父辈的前世今生、旧时大家庭的盛衰起伏,交织成带有个人体温的家族叙事,在作家隐忍的文字中汩汩流淌。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父母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
父亲去世后,金宇澄常陪母亲翻老相册,旧影纷繁,牵起绵绵无尽的话头,他请母亲讲一讲旧照片,记下时间和细节。《回望》 采用我、父亲、母亲三重不同的叙事角度,作家刻意保持了三段记忆之间的某些差异,保留了一种“在场感”。对于上一辈故事采用这种交织的复述,金宇澄坦言,他的写作常常“瞻前顾后、下笔踟蹰,习惯被七嘴八舌的声音和画面切断”。在一次次梳理中,父辈经历的细节,油然融入到作家少年时期的记忆碎片里,金宇澄提到他喜欢的导演杨德昌,尤其难忘电影里父亲的形象,“一直记得在影片的咝咝声中,那个长期独坐不动的寂寞身影”。
在《收获》 杂志副主编钟红明看来,金宇澄的非虚构充溢着小说家笔法,“是一种文体的自觉和清醒,透着精心和讲究。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力量,以及他对知青年代的反思,对那阶段生存的展现和充分的认知,我觉得超出了我所读过的同题材作品”。在她看来,回望,很朴素的一个动词,似乎低到尘埃里的姿态,但那是要经历怎样的伤痛与沧桑,才会拥有澹泊澄澈的觉悟? 至少,金宇澄写出父母一辈的信仰与抉择,而不是大时代可有可无的点缀。此时,记忆的重要价值浮出水面:让历史变得似乎触手可及。
同样以上海叙事见长的作家小白,在《回望》 里发现了很多隐秘的细节。比如书中写到在提篮桥监狱,父亲听到了日本兵散步时唱的俄文 《伏尔加船夫曲》,而不是 《樱花树下》,让他觉得惊异。又比如讲述当年太湖的强盗来到小镇,三里长的店面由西向东传来乒乒乓乓关“排门板”的巨响,惊涛骇浪般的强盗冲进当铺,抢走一格格抽屉,把里面的银元倒进船舱,抽屉扔弃河里,水面上飘浮的全是抽屉。“这种仿佛电影一样的声响与画面效果,非常高级,令人过目不忘。”小白说。
“开放式写作”,让读者深度参与互动
《回望》 第二章正文中,穿插了大量书信、父亲笔记、日记摘抄、互动百科的词条解释,以及种种著作摘录节选,各种背景声涌入,几乎是以一种众声喧哗的方式,四面八方地呈现大时代里的丰富细节。看似碎片化,也正是金宇澄独具匠心的所在。“这种方式有不确定的效果,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不同线索,生成自己的认知判断,我不想按照一般的传统的习惯,把几大块材料来做清清楚楚的整合,这会失却一些原生的味道,可揣摩的空间也显得狭小。”由此,《回望》 形成一个开放式的结构。
选择开放式的形态,部分来自金宇澄对当下阅读习惯的判断。他爱看五花八门的书评、影评,去年有本火透了的《S.》 让金宇澄觉得“有意思”,“小说形态本就有多元样式,书页间夹杂照片、明信片,甚至罗盘,每一页空白处,有各种颜色笔的笔记和对话,多线索并行,营造出好奇与解密的阅读氛围”。金宇澄认为,读者是聪明的,所以“作者只需要考虑如何丰富自己的表达,请读者选择答案;作者甚至不妨‘懒’一些,多点留白让读者想象”。
不难发现,比起一般创作立场的“自我”,金宇澄格外留意读者与创作的即时呼应。长篇 《繁花》 最早便是在弄堂网连载,他化名在论坛上码字,每天更新一节,读者追看、跟帖、评论,“这种互动,其实就是以前西方传统的客厅、沙龙式阅读,作家写出一段,当天念给熟悉的友人听的,即兴分享对作品的看法”。作家木心说,小说家是享乐主义者。在金宇澄看来,“享乐”多了一重意味,那就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一“让人消遣与感动”的游戏中,饶有趣味地不断试探文本的弹性与余味。
采访问答
金宇澄:文字风格最好是排他的
问:新书《回望》扉页上题词“献给冬的孤独,夏的别离”,又深情又萧索,有何意味?
答:这是我按照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短章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 (薛庆国选译) 改写 的。诗作译文是:冬是孤独/夏是离别/春是两者之间的桥梁/唯独秋,渗透所有的季节……我注意到前两句所概括的意义:冬和夏,截然相反的两极,是悲剧性的对立,很符合这本书的某种特质。
问:书中提到母亲的那句话“在梳理记忆的这段日子里,她变得沉静多了,正是记忆的价值所在”,比起辨析历史,你是否更在意文学意义上的“留存”?
答:是的,文学更大的价值在于我能够留住一些什么。也许是长期当编辑形成的某种敏感,我清楚这本书究竟叙述、梳理和记录了什么。加上种种局限,这部非虚构作品里总是会出现空白,因此,我要把仅存的那些细节,进一步细化,做到细之再三,有种叠床架屋的效果,整体上才可以获得某种平衡。
问:这部作品明明是非虚构叙事,为何还是透着小说家的运笔?
答:用哪种文字质地来表现作家所理解的样式和内涵,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其实和音乐美术一样,必须显示作者的个人特征,你要学会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文字最好是排他的。即使是非虚构,同样要有个性化的样式和内涵。
问:从《繁花》到《回望》,你强调的“在场感”一直很明显,对一段段岁月的截面叙述画面感十足。这种内在勾连会延续到你的下一部作品中吗?
答:我确实一直注意画面和在场感,喜欢简练与克制。不过,目前还不清楚下一部作品会是什么,因为我不是有计划、有惯性的作者。我当了近30年小说编辑,编辑心态更占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