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逝世60周年|在人生的地毯上编织图案
当提到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时,《月亮和六便士》《面纱》《刀锋》等他笔下的长篇小说经常得到许多关注与讨论。在这些书中,毛姆书写了不同角色较为完整的一生,来讨论人类最宏大、最焦虑的终极问题:在《月亮和六便士》中,他以“安稳如六便士般的平庸”与“天边如月的理想”,用证券经纪人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抛弃家庭、工作与诸多社会准则来追求极致艺术理想这样充满冲突的人生,试图在一种混乱且模糊的地带拷问人们的自我;《刀锋》中的男主人公拉里虽不像前者那般极具侵略性,但也在每一个人生选择之中抛弃了本应拥有的优越物质生活,通过宗教、修行等充满灵性的探索,追问既然人终将一死,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年1月25日-1965年12月16日)
毛姆的长篇小说往往需要漫长的铺垫来构建一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如斯特里克兰德在塔希提岛的月亮,或者拉里在印度的雪山。与长篇小说相同的是,他笔下的短篇小说反反复复书写的内容还是可以归为一个母题,正是他那本半自传体小说的标题——“人性的枷锁”。但在短篇小说这个逼仄的舞台上,毛姆以笔为“刀锋”,迅速剥离出了文明的假象。
他的文字里充满了“伶牙俐齿”,用幽默到有时近乎残酷的方式将覆盖在原始欲望上的一层如遮羞布般薄薄的漆刮了下来。在这些短篇里,毛姆并不急于解释人性,也不试图为人物寻找任何“更高的动机”,看他们在虚荣、贪婪、恐惧与傲慢的牵引下,如何做出真实的选择。
毛姆与莫泊桑的一串珍珠项链
毛姆的短篇小说与莫泊桑具有相似的气息。这一点他毫不避讳,并在文学评论随笔集《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中写道,他年少时热爱读莫泊桑,确实深受其影响。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罗长利/译,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读创/新流文化,2023年4月版
然而他笔锋一转:“在他的人物身上,贪婪或许是唯一强烈的人类情感。他当然能理解人心的贪婪,但纵然表示出厌恶,心底却是暗暗同情的。他无疑有点庸俗,然而,若只因这类事就否认他的杰出成就,那也是够愚蠢的。……哪里会有完美无缺的作家呢?”可见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莫泊桑那种“极富同情心”的写作模式并不让毛姆欣赏。他走向了另一条路:仍与莫泊桑一样精心雕琢有趣生动的故事,来制造情节上的惊奇,但并不用其笔来表达同情、揭露社会、为底层打抱不平。毛姆更热衷于制造“认知的崩塌”。
莫泊桑写“珍珠项链”,毛姆也写“珍珠项链”。莫泊桑的珍珠项链让玛蒂尔达一生为虚荣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或者是成为了她告别虚荣的契机,总的来说戏剧化又颇具社会教育意义。毛姆的珍珠项链则真的很像闲谈时的一个乐子:一个身份低微的家庭教师因为珠宝修理店的失误,意外获得了天价珍珠项链的佩戴机会。为了把项链寻回去,修理店出了300英镑的报酬,被这位家庭教师用于假期来挥霍:她成功在这个意外之财促成的假期里傍到了大款,辞去了工作,后面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傍大款专业户。
故事的最后,毛姆让讲述者劳拉说出了她所期待的“另一种结局”,并借这个更合人心的版本,悄然完成了一次讽刺:她说,如果这个拿到300英镑的家庭教师最后嫁给了一个穷得要命、身体残缺、工作普通的男人,并且用这300英镑过上了可怜又有点幸运的生活就好了!这样非常具有教育意义。
他拒绝在这个故事里提供任何“正确答案”。在《珍珠项链》中,他甚至直接点破:“真人真事从来就没有编出来的真实。”这句话几乎可以视作他的写作宣言。他并不急于判断她是否“用错了”这笔意外之财,他只是呈现一个荒诞的事实:一次偶然的命运偏移,并不会自动导向更高尚的人生。更重要的是,毛姆对那些急于要求这个故事“变得有教育意义”的旁观者,显然并不赞同——为什么一个随机改变人一生的事件,非得被改写成一则道德寓言?在这里,毛姆的态度是明确而反传统的:人生并不配合我们的价值期待。
“我”之存在与见证
有趣的是,毛姆还在《珍珠项链》里写了这么一个桥段来回扣自己另一篇小说《万事通先生》与莫泊桑的《珠宝》:
谁都听说过这类故事,妻子骗丈夫就玩把戏,故意把特别贵的珍珠项链说成假的。这样的故事都老掉牙了。
“你太夸张了。”想起了我自己写过的这个故事,我这样对她说。
那个几乎无处不在的“我”,始终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若即若离地出现,像是随时要打破那堵墙,却又从未真正跨过去。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在场感”,让“我”并非一个全知视角,也从不承担裁决者的责任,只是一个听故事的人、一个转述者、一个恰好在那里的人。这种位置让读者也会好奇:我们深知这个“我”是套着毛姆壳子的“我”,但这些故事是不是真的毛姆亲眼见到的?那听上去时而合理,时而又太玄乎了。
例如毛姆另一篇短篇小说《在劫难逃》,就让“我”睡在了一张死过人的床上。这个死去的荷兰人生前逃到了婆罗洲的荒原,试图躲避仇家阿奇人的追杀。他千算万算,最终在这张“我”即将睡的床上暴毙。他浑身上下连一丝伤痕都找不到,只是一把阿奇人手中的曲刃短剑“就横搁在他的咽喉部位”。
毛姆没有让具体的凶手出现,他只是重演了那个他很喜欢的古老的“萨迈拉之约”的宿命论:你越是挣扎着逃离命运,你就跑得越快去见死神。恐惧本身就是最致命的毒药。毛姆用这种不可知论的结局,嘲弄了人类命运的徒劳:这里没有鬼魂,这里只有无处不在的、湿热的恐惧——这故事是真的吗?没人知道。毛姆并不需要凶手出场,他只需要让读者意识到: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而如果这一切只是心理作用,那同样令人绝望——因为你连恐惧的源头都无法指认。
毛姆非常擅长写这种“不由自主”。这种心理的崩溃在《蒙德拉戈勋爵》中更完整地上演。莫泊桑的许多短篇(比如《奥尔拉》)也特别喜欢探讨这种介于心理疾病和超自然现象之间的模糊地带,去营造那种“到底是‘我’疯了,还是真的有鬼”的恐怖感。《蒙德拉戈勋爵》讲述的是一位权势显赫、性格傲慢的勋爵,在一次公开场合中以近乎羞辱的方式毁掉了一个名叫欧文的“小人物”的尊严。此后,勋爵开始反复做噩梦:他经历着让他精神崩溃的很多出丑事件,每一件事情都与欧文有关。梦中,他当众唱了一首怪异的歌,现实中的第二天,欧文就哼了两句里面的歌词;梦中,他用酒瓶砸了欧文的头,现实中的第二天,欧文说他的头很痛。勋爵在清醒与梦魇之间逐渐失去边界,最终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崩溃中走向死亡,而欧文也在同一天离奇身亡。
这个结局十分诡异:从勋爵找来的心理医生的“精神分析”的视角,这似乎是一个关于“良心愧疚”的故事。勋爵的傲慢使他成为一个极端的自恋者,无法在意识层面承认自己做错了。既然意识上不认错,他被压抑的“愧疚感”就只能在梦中(潜意识)爆发出来。梦境的逻辑是他最害怕的“体面的崩塌”——他习惯了羞辱别人,惧怕被羞辱。心理医生给出了建议:“正视它,去道歉”,这是唯一的“治愈”方法,因为这能让你潜意识里的“愧疚”得到和解。然而,勋爵拒绝了。他的“傲慢”人格战胜了“愧疚”。最终,他崩溃走向死亡。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莫泊桑式的心理悲剧:一个被自己傲慢和愧疚逼死的人。但毛姆不想止步于此,他开启了一个新的反转:欧文第二天为何能精准说出勋爵梦里的细节?“梦只是勋爵自己的事”这个前提被打破,两人也正是在同一天前后暴毙。一场起于愧疚的妄想为什么让对方也死了?——这正是这篇小说最精妙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它把一个看似简单的“因果报应”故事,变成了一个更黑暗的东西:这不再只是一个“加害者被愧疚折磨致死”的惩罚故事,是一个“受害者的怨恨变成了超越死亡的诅咒”的故事。
毛姆想写的,是一种在“人性的枷锁”的碰撞之中所产生的后果,即“相互毁灭”。勋爵的罪是傲慢,而欧文的反击,则是勋爵低估了的“恨意”:困在自己的怨恨之中,无法原谅,也拒绝遗忘。恨意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它物化成了超自然的力量,不仅入侵了勋爵的梦境,更在勋爵死亡的那一刻,宁愿自己死,也要追到地府去继续折磨勋爵。这两种枷锁彼此呼应,最终形成了一种封闭的、互相吞噬的结构。毛姆并不试图调解这场冲突,他所看到的就是:当人格本身成为枷锁时,人是无法被拯救的。

《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毛姆短篇小说全集1》(陈以侃/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6年10月版)收录了《珍珠项链》《午餐》等
幽默地书写无意义人生
毛姆喜欢幽默。他的幽默虽然充满讽刺,却并不依赖机智的反讽或夸张的情节,而更像是一种对“荒唐的文明瞬间”的精准捕捉。他尤其擅长描写那些乍看之下合情合理、细想却令人茫然的对话与行为。毛姆的幽默,正是发生在这些“无事发生”的时刻:当所有人都在维持体面,他却偏偏点出那头被刻意忽视的房间里的大象,用一句看似俏皮、实则刻薄的话,把虚伪的表层戳裂。
例如在《在劫难逃》中,主人给“我”讲述完了这则荷兰人暴毙的事,发生了如下对话:
“真滑稽,是不是?”
“呃,那就全凭你的幽默观了。”我回答道。
我的主人迅速地看了我一眼。
对于诡异的死亡评价为滑稽,毛姆的回应堪称经典。
在毛姆众多的短篇小说中,《午餐》无疑是其“刻薄幽默”的代表作。初读之下,这似乎只是一个男作家被女粉丝“敲竹杠”的滑稽轶事,但毛姆通过极其精确的节奏控制,把这场心理防线的溃败写成了一出层层递进的喜剧。
一个男性作家收到了女粉丝的来信。信中对他恭维再三,并提出希望他能够请她在远超他消费能力的一家巴黎高档餐厅吃一顿饭。“她信中的恭维话说得我心头发痒,而且那时我太年轻,还没能学会对一位女士说‘不’。”他如是想,一场虚荣与贪婪的博弈由此开始。
那位“崇拜者”是一位精明的社会捕食者,她看穿了男人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软肋,于是构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语言陷阱。他看到菜单,心中一惊,但她说:“我中午从来不吃什么。”他于是马上放下心来,“慷慨大方”地回答:“哦,可不要这么说!”她马上又说:“除非你有头等鲑鱼。”
这种压制过程建立在他的节节败退上:他每次刚松一口气,侍者就恰到好处地询问下一道餐点的选择;她每次都以退为进,不断否认自己的欲望,来合理化自己最昂贵的选择,宣称“我午餐从不吃任何东西”,却说:“我只吃一样东西”,“除非你有……”还说:“医生不让”、“习惯如此”或“只是尝尝”。这个循环——从头等鲑鱼,再到鱼子酱、白葡萄酒、嫩嫩的龙须菜、纯洁的桃子——一步步把男主推向“断头台”。
只点了最便宜羊排的男人汗流浃背了:他无法承受在一个高级餐厅里承认自己没钱,尤其是在一个“崇拜”他的女士面前。毛姆把高级餐厅变成了一个“社会剧场”。在这个剧场里,男主被迫扮演“慷慨的绅士”,而女主则利用这个舞台,彻底掌控了局面。
《午餐》的男主为自己的虚荣付出了短期破产的代价。而结局——“但我终于复了仇。我不认为我是位睚眦必报的人,可是当不朽的大神插手这件事时,你暗自得意地看着这个结果也还是可以原谅的。今天她体重三百磅。”小气记仇的他看到贪婪的她这么肥胖,他也就安心了。
在《午餐》里,毛姆不同情那个男人,也不批判那个女人,他只是觉得这两个人都很可笑;他不断拆解人们赖以维持自尊的幻觉——关于体面、关于道德。在虚荣与算计的合谋之中,人往往既是受害者,也是共犯。
正是在这些短篇小说里,毛姆一再拒绝为人生提供“正确示范”。他不关心人物是否堕落,也不急于判断他们是否做出了“更好的选择”。他更感兴趣的,是当所有自我安慰的幻觉被剥离之后,人会以怎样的方式继续活下去。
这一点毛姆自不会在这些短篇中给出什么回答,但他在《人性的枷锁》中写了主人公菲利普想起的一则东方国王的故事:
哲人把人类的历史归结为一行字,写好呈递给国王,上面是这样写的:人降生到世上,便受苦受难,最后死去。人生没有意义,人活着也没有目的。他出生还是不出生,活着还是死去,都无关紧要。生命微不足道,死亡也无足轻重。
这听上去颇为虚无的话,却让菲利普感到狂喜——因为他为此感到人生无比轻松,“他那无足轻重的地位转化成一种力量。突然,他觉得自己跟那似乎一直在迫害他的残酷命运势均力敌了。既然人生毫无意义,世间也就没有残忍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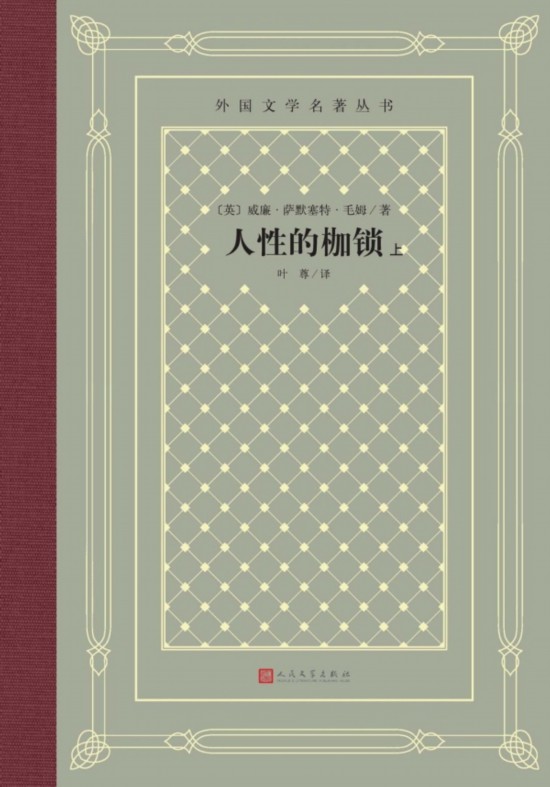
《人性的枷锁》,叶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因此,纵观毛姆的作品,他本来就很少批判,更像一个地毯展示商,把一整张由虚荣、恐惧、欲望、傲慢与偶然编织而成的人生摊在你面前。在这张地毯上,没有主线,也没有中心图案。每一根线都看似微不足道,却又彼此纠缠。你无法从中找出一个“应当如此”的方向,只能看见无数已经发生的结果。
毛姆并不试图告诉你哪一段人生是正确的,哪一种选择更高尚。他只是冷静地提醒你:这就是人类亲手织出的图案,而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其中编织着、缠绕着。
或许正因如此,《人性的枷锁》中那则关于“人生无意义”的寓言,才会让菲利普感到狂喜。那不是一种绝望,而是一种卸下重负的时刻——当人生不再被要求证明自身的价值,它反而获得了一种奇异的自由。
毛姆的短篇小说,正是在这种自由之中展开的。他不要求人物成长,也不期待他们觉醒,更不强迫命运朝某个方向收束。他只是把一张张已经织成的地毯铺陈出来,让读者自行决定:你自己的那张地毯想要怎么编织,又是否愿意承认,这些花纹本就没有被设计成“有意义”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