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兹:莱蒙特的工业叙事从此开始
在波兰中部,有一座名为罗兹(Łódź)的城市。它的市徽是一只迎风前行的小船,正如市名“罗兹”的含义。波兰长篇小说《福地》以罗兹为背景,描绘了19世纪末波兰工业城市发展历程中的蓬勃与残酷。从此,罗兹这座城市的形象便深深镌刻在波兰文学史上。
有关罗兹的历史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上半叶,起初它只是一座小村庄,到15世纪上半叶,罗兹获得城市地位,逐步成为所在地区的农业、手工业、贸易中心。波兰被瓜分后,罗兹于1807年被划入由俄国实际控制的波兰王国管辖范围。随着农奴解放及工业革命在棉纺织业掀起的浪潮,罗兹在数十年间从一个普通的棉纺小镇,一跃成为波兰王国的工业中心、聚集财富的“福地”。
1924年,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福地》的作者、波兰作家伏瓦迪斯瓦夫·莱蒙特(Władysław Reymont),莱蒙特早年家贫,曾从事裁缝、铁路工等职业,底层的生活经历为他的创作积累了素材。为了创作《福地》这部小说,他多次前往罗兹体验生活。友人戈兹林斯基在回忆中提到:“他对罗兹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以各种形式捕捉着这座城市的种种:他走进轰鸣的工厂,穿梭于城内城外,在咖啡馆和餐馆之间徘徊,与市民进行热烈的交谈,在深夜将自己的印象一一记录。”最终,莱蒙特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探赜索隐的笔力,在小说中对罗兹进行了全方位的、近乎纪实的描写,赋予了罗兹超越地理坐标的深度。这座因纺织业而崛起的城市被推至文学舞台中央,它的独特性格与气质在空间书写中一一呈现,展示出一幅立体而极具张力的城市发展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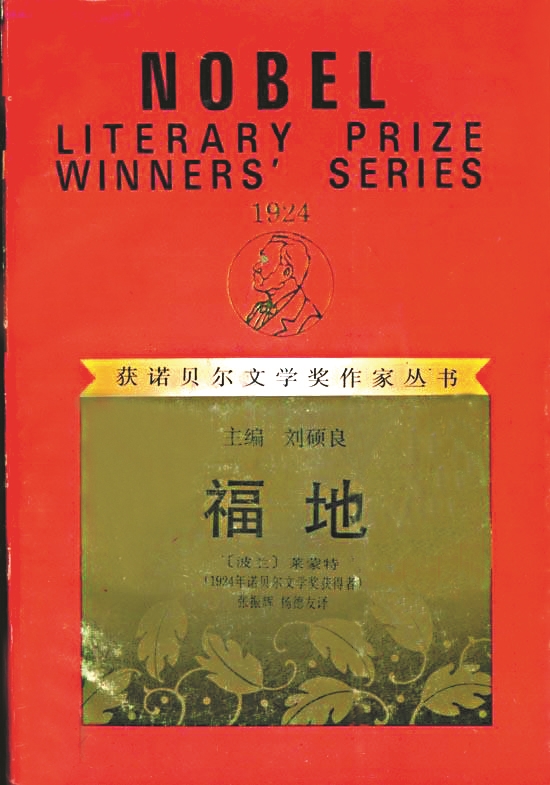
《福地》,【波兰】莱蒙特著,张振辉、杨德友译,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
城市空间的族群版图
在罗兹,有一条全长约4.2公里的皮奥特科夫斯卡大街,它不仅是欧洲最长的商业街之一,更是不可错过的城市地标。大街两旁店铺林立,餐厅、娱乐设施与工厂旧址交相辉映,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独特氛围。1821年,波兰政治活动家伦别林斯基主持制定罗兹的织工定居点规划时,将之前的皮奥特科夫斯基通道拉直、拓宽,建成了一条城市大道,就是后来的皮奥特科夫斯卡大街。同时,大街两侧被划分出多个地块,修建“前店后厂”的职工住房,新城广场(今天的自由广场)则是这个定居点的行政与生活中心。
《福地》中的皮奥特科夫斯卡大街由三个部分构成:“从加耶罗夫斯基市场到纳夫罗特街属于工厂区”,这片区域主要聚集的是德国工厂主和波兰工人。这里厂房林立、机器轰鸣,每天拂晓,成千上万的波兰工人便从“积满泥水的沟渠似的小街小巷”中涌入德国工厂主的厂区,如同“一群群无声的黑色蚂蚁”,在大街上汇成“宛如长蛇”的队伍。“从纳夫罗特到新市场属于商业区”,商店、酒馆、剧院等商业设施在这里汇集,德国和犹太资本家们占据着剧院的高档包间,谈笑间尽显对这座城市经济掌控的阶层优越感,而处于社会底层的波兰与犹太平民,只能挤在喧闹、昏沉且弥漫着烟雾的旅馆餐厅里借酒浇愁,闲谈生活的困顿与无奈。“从新市场往下到老城则是犹太人卖旧货的地方”,工厂里的废水在这里排出,“道路上面满是泥泞,路面也被踩坏了”,是富人从不踏足的“边缘地带”,却“挤满了犹太人和往老城打工去的工人”。通过这样的空间布局,莱蒙特将多民族群体巧妙地编织进一个连续的物理空间,既道出了不同民族的社会处境,也展现了罗兹这座城市生动的民族交融图景。
莱蒙特并未在《福地》中直接描写皮奥特科夫斯卡大街上的“豪宅”抑或厂房,但他笔下的布霍尔茨宅邸、楚克尔家宅无疑是对这些建筑的精准复刻。在多维的空间中,德国资本家和犹太商人的形象与性格跃然纸上。
德国人是罗兹工业秩序的掌控者。他们带着资本和技术而来,以工厂主的身份在罗兹立足。他们行事严谨、崇尚效率,是资本逻辑的坚定践行者,这一点从莱蒙特对德国工厂主布霍尔茨宅邸的描写中可以看出。在布霍尔茨家的穿堂里“挂着厂里的各种照片、一班班工人的名单和标明布霍尔茨地产的挂图”。步入屋内,可以看到“房间里的家具摆设得庄严大方”,迎面而来的是一种“冷漠和严肃的气氛”。布霍尔茨的办公桌上,摆放着按部门精准分类的信件,它们将会被投进一旁柜子上的入口中,“这些入口的上面写有相应的题字,然后信再通过管道往下送到厂长办公室里,到这里它们就立即被分送走”,从而避免程序冗余。这一连串空间的描写,将布霍尔茨这位德国工厂主细致入微、一丝不苟、讲求条理和效率的特质刻画得入木三分。而这并不仅是他个人的性格缩影,更折射出当时在罗兹的德国人群体的精神气质与行为方式。
犹太人是这片土地上灵活的“渗透者”。他们天生擅长经商,逐“利”而居,在流动中寻找生存空间。工厂主楚克尔的家中可谓是“投机商”式的布景,如同一个微型的世界市场:客厅里,阿拉伯的龙涎香、波斯紫罗兰和玫瑰的香味混杂在一起,充斥着整个房间。餐厅里则摆放着“布列塔尼式的餐具橱”,在一张大桌子周围,“摆着许多古德国式的、雕刻得十分别致的橡木凳子”。整个住宅如同来自世界各地稀罕物的大卖场。莱蒙特生动再现了犹太人四海为家、在流动中经营与获取的民族特质。
19世纪的罗兹以其民族多元性催生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多民族共存成为这座城市不容忽视的社会特征。《福地》中的波兰人、德国人、犹太人从来不是孤立的民族符号,而是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他们的融合碰撞并非靠文化认同,而是靠“资本逻辑”绑定:首先,他们有了共同的信仰——金钱;其次,共同的信仰催生了共同的道德——不再是传统的善恶二分,而是“金钱至上”的资本准则;最后,这种信仰与准则,又催生出共同的“罗兹式语言”——一种混杂着德语技术词、波兰日常词、犹太商业词的独特表达方式,这种语言将他们连接在一起,本质是为了快速达成交易,推进生产。通过这三层绑定,罗兹在多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凝聚出鲜明的整体性,展现出其多元的城市性格与气质。

伏瓦迪斯瓦夫·莱蒙特
城市空间的资本逻辑
如今当人们漫步罗兹街头,依旧能探寻到19世纪波兰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所铭刻的城市印记。坐落于市中心的红砖建筑群“曼菲萝工厂”是当下罗兹最受欢迎的复合式商业中心,是罗兹最大的公共广场,经常举办各种文化和娱乐活动。1872年,有着“罗兹棉花大王”称号的波兰犹太企业家以色列·波兹南斯基建立起一片占地近30公顷的“城中城”——不仅包含纺织厂与各类生产车间,也建有工人住宅以及配套生活设施,全盛时拥有工人7000多名。富有的波兹南斯基家族还紧邻厂区建造了极尽奢华的波兹南斯基宫。有研究认为,《福地》中很多人物、建筑都能在罗兹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找到原型,其中就包括以色列·波兹南斯基和他的工厂以及私宅。
在罗兹,富人们精致地生活,穷人们艰难求生。资本家恩德尔曼的豪宅“如同一座佛罗伦萨式的宫殿”。室内的墙上挂着镶了边的珍贵图画,下面“还挂着几套路易十六式的缀上了金丝边的白外衣”。客厅里摆放着“嵌上了各种珍宝的小桌”和“用许多金边竹片做成的中国竹椅”,“椅子上也钉着色彩鲜艳的绸布”。“金丝编成的篮子里装满了鲜花,在用标准的大理石砌的壁炉里,火烧得正旺”。客厅的一角,还“立着狄爱娜的娇嗔动人的铜雕像”。恩德尔曼的家可谓是兼具了奢华、审美与舒适性。工人们的住所,环境则十分恶劣:昏暗的工人宿舍盖在一处背街的“没有铺砖的小巷子里”,“看起来十分凄凉和鄙陋”,一排枯萎的、骷髅般的白杨树将宿舍区与工厂隔绝。作者通过制造这种居住空间的割裂与对比,展现出这座城市的典型特征: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巨大的阶级鸿沟无法填补,富人与穷人的生活质量走向两个极端。空间成为阶级分化的可视标签。
除了居住空间,莱蒙特对于剧院、酒馆、公园等城市休闲空间的构建,同样暗藏深意。以剧院为例,在小说中,它不再是艺术的殿堂,而是资本家们彰显财富、巩固关系的“高端名利场”。富人们穿着华丽,在堆满钻石首饰与天鹅绒座椅的包厢里进行“上流社交”,他们关心的不是戏剧内容,而是利益和财富,“看戏”不过是塑造高雅形象的工具。当经济危机的消息传入剧院,普通观众沉浸在剧情中,富人们则纷纷离席,由此可见他们的虚伪。莱蒙特对于剧院的描写揭示了罗兹社会的虚假文明:资本家们极力扮演的高雅文明形象,在利益和金钱面前迅速崩塌。
耐人寻味的是,《福地》的城市构建中还存在很多空间缺位:在土地交易、工厂烧毁、权益受损事件频发的罗兹,难寻政府、法院、警察局等城市管理机构的身影。通过这种看似不完整、反现实的空间设计,莱蒙特构建了一个纯粹由资本与利益主导的经济社会,雇主完全成为工人的支配者,工人则沦为劳动的执行者。这种新经济关系的本质,是由生产关系而非法律规章所决定的,道德、文化的功能则更加微乎其微。金钱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了难以逾越的阶级高墙,甚至凌驾于法律与良知之上,不断塑造着这座城市的规则与面貌。
莱蒙特的城市空间书写
正如开篇所述,19世纪中后期的罗兹经历了一场罕见的工业化加速:在短短数十年间,这座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城被改造为密布工厂和烟囱的纺织中心,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都在快速滑向一种新的“工业社会”形态。位于皮奥特科夫斯卡大街南端的“白色工厂”,正是昔日罗兹工业转型的重要见证之一。这座由德国资本家路德维克·盖耶于1835年出资兴建的建筑群,因其独特的浅色灰泥墙面而得名。整个工厂由四座翼楼围合而成,中庭中央矗立着“老锅炉房”,高耸的烟囱以及两座除尘塔和两座水塔,这样的布局在工业建筑史上难以见到,是一种极为独特的构造。这里诞生了罗兹第一家机械化的棉纺、棉织工厂,启动了罗兹第一台蒸汽机,标志着这座城市纺织业机械化进程的开启。作为工业化的先驱之地,如今的“白色工厂”被改造为罗兹中央纺织博物馆,以崭新的姿态继续讲述着罗兹工业时代的故事。
然而,工业化在推动罗兹城市发展的同时,也暴露了其消极的一面。莱蒙特立足于社会现实,在《福地》中通过多层次的空间书写,深刻揭示了工业化光环背后潜藏的社会问题。
工厂作为罗兹工业属性的核心符号,是莱蒙特空间书写的重点对象。从外部形态来看,罗兹的工厂有着“黑魆魆”的躯体和“白雾萦绕”的烟囱脖颈。它黎明即醒,用自己“嘶哑的”“尖厉的”汽笛声呼唤工人们去上工。工厂内部的工作环境同样恶劣,过道被车子、人和货物挤得水泄不通。从莱蒙特的书写中,读者不难感受到,工厂的运作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还危及人类健康。作家笔下被“工业黑”和“烟雾白”笼罩的工厂,暗含着他对于工业发展竭泽而渔、漠视自然生态与人类健康的深刻批判。
工业化带来的弊病不仅体现在生态层面,更体现在传统与现代性的撕扯之中。工业机器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生产效率,却也对依赖于人力和技艺的传统手工业造成了毁灭性冲击。小说中的手工业者以及老巴乌姆、特拉文斯基等人的旧式工厂,由于生产工具落后、管理方式不灵活,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同蒸汽巨人的搏斗中将要倒闭是无疑的”。这种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也在莱蒙特的空间书写中得以具象化。
手工纺织者们住在泥泞的小街上,“低小的小房屋的窗子里射出金黄色的灯光”,透过每个窗户,都可以看到“活动着的机床和人们”,阁楼里“也可以听到劳动的声音”。整个小街上都“充溢着机器单调的响声”,“纺织机也在嘎达嘎达地响着”。然而,就在这“浮动于泥泞上的地区”旁,屹立着工厂主米勒现代化的四层楼厂房——“它的许许多多窗子和电灯似乎以胜利者自居的姿态放射着万丈光芒”。现代工厂如同一个强大的对手,“仿佛一次呼吸就能将旁边简陋、歪斜的房子推倒”。
现代化的工厂与机器不仅影响了传统手工业者,也沉重打击了缺乏革新和效率的旧式工厂。特拉文斯基的工厂与米勒的工厂只隔着一个小果园,相比之下,特拉文斯基的工厂显得十分简陋,“点燃着一排排黄色的汽灯”,与米勒工厂的电灯比起来“就像蜡烛似的”。莱蒙特展示的并不只是技术上的陈旧,而是一个正在失去主导权的生产世界:机器仿佛要挣脱人的驾驭,预示着工业资本逻辑将反过来统治乃至吞噬那些仍抱守旧制的厂主和工人。
在莱蒙特的叙述中,机器战胜手工并不是单纯的技术升级,而是一道残酷的筛选机制:那些固守旧式生产方式的工人和厂主,成为罗兹迈向工业化与现代化道路上的“牺牲品”。站在青年波兰时期的历史节点上,莱蒙特并没有把工业化简单书写为“进步的胜利”,而是以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空间描写,将生态破坏、传统手工业的崩溃以及人的尊严被蚕食这一系列现代性难题,具象为罗兹城市肌理上的裂口与阴影。
2025年正值伏瓦迪斯瓦夫·莱蒙特逝世百年。回望这部创作于百余年前的名篇巨著,我们再次审视罗兹这一历史文化空间中的现代性经验与资本记忆。在莱蒙特的笔下,我们既能直观感受到这座城市发展中的蓬勃生命力,也能窥见其工业化与资本化进程中滋生的种种问题。值得高兴的是,在后工业时代老牌工业城市普遍面临转型困境的今天,罗兹没有被历史的巨浪淹没,依然在波兰乃至欧洲的版图上熠熠生辉。今日的罗兹,一方面依靠物流、信息技术、电影等新兴产业实现了“复兴”,另一方面,它没有摒弃自己的工业基因,而是将昔日的工厂、烟囱与工人街区转化为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新动能,在寻求转型的同时始终记得自身的来路。
(李怡楠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波兰研究中心副教授,韦思锐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