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掌门人”故事里的故宫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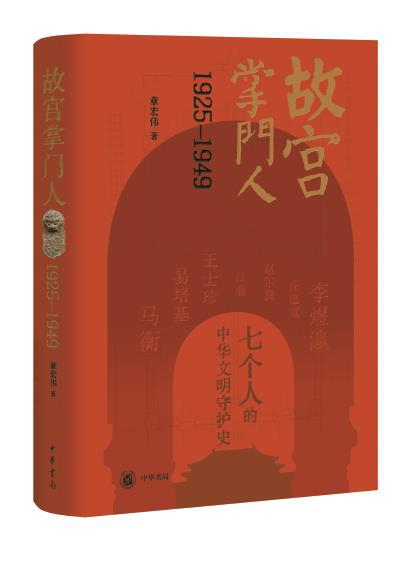
《故宫掌门人1925—1949》 章宏伟 著 中华书局出版
20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迎来了建院百年之庆。从1925到2025,百年时光流转中,故宫不仅镌刻下自身从皇宫到博物院的转型印记,更成为中华文明在时代浪潮中坚守本源、开拓新篇的精神坐标——它承载的不仅是文物,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与精神基因。
章宏伟所著的《故宫掌门人1925—1949》,便以厚重的笔墨为我们打开了理解这一精神坐标的窗口。作者跳出传统故宫研究的文物视角,转而聚焦“掌门人”这一核心群体,填补了故宫早期管理史研究的空白,让我们得以透过亲历者的眼睛,触摸那段动荡岁月里文物守护与文脉赓续的真实温度。
岁月经纬中的文化坚守
全书结构严谨,体系完整。第一至第七章为主体,以时间为轴,系统评述了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至1949年间七位核心行政负责人的作为。从时局动荡中文物的颠沛流离,到人事变迁里故宫的艰难存续,再到一代故宫人对文化的执着坚守,百年故宫的早期命运,皆浓缩于这七章文字之中。其中第七章尤为动人,字里行间尽显故宫人在绝境中的职业操守与不屈风骨,堪称全书精神内核之所在。
附录《故宫博物院组织架构(1924—1949)》是全书的重要补充,足见作者考证之功力。这份附录并非简单的资料罗列,而是对故宫博物院早期管理体制、机构名称演变的系统梳理,既印证了作者深耕史料的付出,也为读者厘清了书中历史线索,让百年前的故宫管理脉络清晰可见。
该书的前言与后记形成巧妙呼应,共同勾勒出故宫的文化坐标。前言清晰追溯了故宫从皇家禁苑到公共博物院的历史转折,为全书奠定“文明转型”的基调;后记《于宫阙之间寻绎中华文化的栖居之地》则是对全书主旨的升华——它不仅延伸了文本内容,更提炼出故宫与中华文化的深层联结,同时对掌门人的分类与价值做了正文之外的补充阐释,让人物形象更趋丰满。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图片设计。正文已穿插诸多插图以佐史实,作者仍将部分核心图片单独排版,且打破“图片置于书前”的惯例,将其放在卷末。这种设计绝非刻意标新,而是希望读者在读完文字后,能通过图像与历史形成二次对话,进一步深化对“文物守护”主题的认知。
现代文明的中国样本
这部著作看似是“写人”,实则是“以人写史、以史见文”——它的核心,是揭示故宫与中华文明的共生关系,以及故宫人作为“文化守护者”的使命担当。正如封面所题“七个人的中华文明守护史”,短短11个字,精准点出了全书的灵魂:七位掌门人的故事,本质上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守护史。
作者对故宫的认知,深植于“文明转型”的宏大视野。他指出:“紫禁城由皇宫转向博物院,不仅塑造了现代文明的中国样板,更开辟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新纪元——这一转型在当时的社会与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文化传承与公共文明建设注入了持久活力。”这一判断,正是全书立论的逻辑起点,也让掌门人的故事有了更广阔的历史维度。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始终带着清醒的问题意识展开研究。他不盲从主流观点,敢于对历史细节提出辨析:序章中,他重新审视“驱逐溥仪出宫”的历史意义,厘清“故宫建立是否为政府行为”的争议;第四章中,他考证“故宫维持动议是否出自李石曾”,还原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作者善于从被忽略的细节中挖掘文化价值——每一章都能提出关乎故宫命运的关键问题,并以扎实的史料给出有温度的答案,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事件堆砌。
作者的见解更具突破性与人文关怀。例如,他客观评价张作霖在故宫保护中的作用:“正是他力阻故宫博物院对所藏金砂银锭的‘处分’,避免了文物因经费短缺而被挪用的命运。”对于战前“反对文物南迁”的一派,他亦给出中肯评价:“奋力护送文物南迁的先贤值得铭记,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守护者同样值得钦敬——尽管主张相异,他们的初心始终一致:守护故宫,便是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这种不偏不倚的视角,让历史人物的形象更显立体。
百年故宫的“文化守门人”
这既是一部故宫掌门人的合传,也是一部故宫早期的“生存史”。1925至1949年的24年间,七位掌门人在不同时局中接过“守护之责”,虽任期有长有短、贡献各有侧重,却共同撑起了故宫的存续之路。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几位掌门人,因政局动荡,任期多不足一年,但正是他们的接力坚守,才让故宫博物院在初创期站稳脚跟,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北洋政府时期的五位掌门人,各有其“使命坐标”:
李石曾是“奠基者”。留法经历让他最早意识到故宫文物的世界价值,也最早提出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构想。正是他牵头推动,不仅让故宫博物院从构想变为现实,更初步建立了“董事会与理事会并行”的管理体制——这一双轨体系,成为后来故宫管理模式的雏形。
庄蕴宽是“守护者”。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政权更迭如走马灯,庄蕴宽却以一己之力守住故宫:他两度拒绝军队占用故宫的要求,一句“我们都有责任,万不能拱手相让”,道尽对文化的敬畏;他更以灵活的策略制止军阀侵占,形成“故宫非军事禁地”的惯例,为故宫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赵尔巽是“失意的接管者”。1926年7月,吴佩孚扶持的杜锡圭内阁秘密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任命清朝遗老赵尔巽、孙宝琦为故宫博物院正副委员长。同年8月,二人以“参观”为名赴故宫接任,却遭遇庄蕴宽等人的坚决抵制——庄蕴宽坚持按规逐项点交,拒绝随意交接职权,最终赵尔巽等人无奈辞职,这场“接管风波”也成为故宫早期管理史上的一段特殊记忆。
江瀚是“民间护院人”。70岁高龄的他,并非由政府任命,而是在故宫保管委员会流产、故宫陷入“无人管理”的混乱时,由各方文化名流共同推举为“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会长。他以民间力量整合资源,平息混乱,最终获得政府认可;任内,他坚持“文物留京”的主张,背后是对“文化根脉不宜轻动”的深层考量。
王士珍是“北洋系的守护者”。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故宫博物院一度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北洋系核心人物王士珍挺身而出,于同年10月出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长。他凭借自身影响力,多次阻止奉军对故宫珍藏的掠夺,为文物安全筑起了关键防线。
国民政府时期的两位掌门人,则推动故宫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易培基是“转型期的开拓者”。1929年2月,他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首位“院长”,却因时局所限,直至1931年3月才正式到任。上任之初,他便面临“废除故宫博物院”的提案,以坚定立场保住了这一文化机构;此后,他推动故宫物品系统清理、完善公众参观制度、组织文献整理出版,更在平津危急之际,牵头启动文物南迁——这场“文化长征”,让百万文物免遭战火损毁。然而,他的一生却与“故宫盗宝案”的争议相伴:案件曾引发全国关注,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开庭审理,最终却因时势变迁与证据不足不了了之,直至易培基离世,这一争议仍未盖棺定论。但作者以客观史料为依据,充分肯定了他对故宫转型的开创性贡献,让这位“争议院长”的文化功绩得以彰显。
马衡是“稳定期的掌舵者”。他与故宫的渊源早在1925年便已开启——彼时他以北京大学教授身份兼职参与院务,1933年7月正式投身故宫管理,先任代理院长,三个月后转正,成为故宫博物院史上首位长期任职的正式院长。在他主导的“马衡时代”,尽管时局依旧动荡,但凭借蔡元培等理事会成员的支持,他推动故宫建立了更系统的管理机制,让文物保护、学术研究与公众开放同步推进,为故宫博物院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故宫精神”得以进一步传承。
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
“故宫掌门人”,看似通俗的称谓,背后是沉甸甸的文化责任——他们是故宫的行政管理者,更是中华文明的“守门人”。
透过这本书,作者向我们揭示了两个深刻的事实。其一,1925至1949年的24年,是故宫最艰难的“求生期”——它历经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日伪政权的更迭,多次面临“关张”危机:北洋时期的经费匮乏、政权动荡自不必说,即便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废除故宫博物院”的提案也曾摆上议程。其二,故宫能在如此绝境中存续,核心在于一代故宫人的坚守——七位掌门人与全体故宫人以“视国宝为生命”的信念,将个人命运与文物命运紧紧捆绑,才让这份文化遗产得以完整传承。
当然,这七位掌门人的文化功绩,仍有更多细节待发掘;但《故宫掌门人1925—1949》的价值在于,它首次为我们留住了对这群“文化守护者”的集体记忆——当我们在2025年回望故宫百年时,不应只看到宏伟的宫墙与珍贵的文物,更应记得:百年故宫的背后,是一群人用一生守护文化根脉的故事。而这,正是该书最动人的力量。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