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苹果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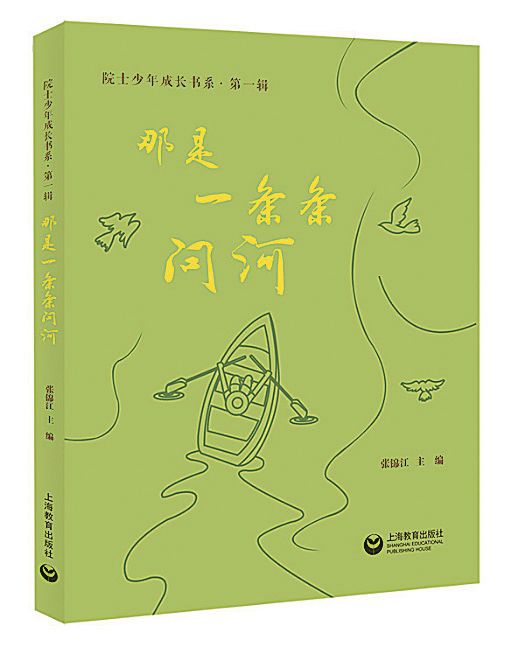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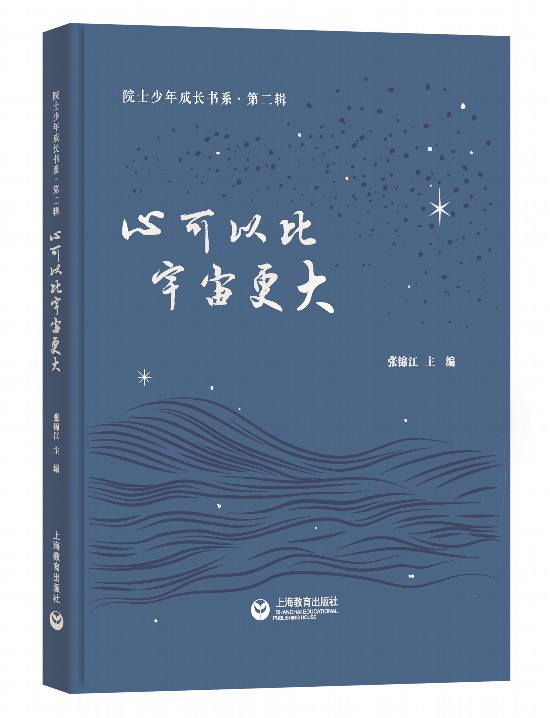
初夏,我在一块典雅的草坪上见到一株苹果树,倘若不去注意那个木牌上的解读,就是一株平常的树,假设在旷野之中,它也会孤独、寂寞、无声地活着,与所有原始森林中的树一样,谁也不会特意关注它。不过,这是在上海名声显赫的科学会堂,洁白色的木栅栏护着这棵小树,一块蓝色的木铭牌上写着:“牛顿苹果树 2024年3月25日 落户上海科学会堂”。
我曾在英国剑桥大学,从国王大道步行至三一街,见过三一学院的大门,迎门的墙面和窗沿都已斑驳呈苍老的土灰色,那里有一棵低矮的苹果树,枝叶翠翠的,主干与分枝并不强大,但这是“牛顿苹果树”。当年我见到的也不是原株,原株在牛顿家乡英国伍尔斯索普庄园,已有差不多400年树龄,在三一学院所见的苹果树是从原处嫁接移植而来。
而“牛顿苹果树”来到中国,始于2014年以杨福家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们发起了“引种牛顿苹果树”的倡议。10年之后,“牛顿苹果树”嫁接成功,落户上海科学会堂,并拥有双重身份验证,一份是英国国家信托基金会给予的“出生证”,一张是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颁发的“身份证”。有幸在上海科学会堂重见“牛顿苹果树”,我的眼前一片光亮与豪迈。满坪的绿草摇曳着,葱茏的香樟树在沙沙作响,仿佛一种亲切而热情的中国式的问候——“‘牛顿苹果树’中国欢迎您!”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精神没有国界,科学传承没有国界,科学友谊是永存的!
我们一群人欣喜地围拢在“牛顿苹果树”四周,我们是编撰“院士少年成长书系”的编者与作者,为少年儿童传递科学精神而汇聚在一起,深知“牛顿苹果树”在上海科学会堂落户的意义。科学需要有童心有幻想,然后把童心的幻想变为真正的现实。当我站在科学会堂一幅爱因斯坦的相片前,想起爱因斯坦老年之后还葆有童心。当我站着科学会堂的一面院士墙下,满目院士星光中,有多少童年的幻想,变成了今天令人赞叹的成就。“院士少年成长书系”编创人员按照这个思路、构想去规划、努力、实现着。我多次见过这套书系的科学总顾问樊春海院士,在他那朴实而简洁的办公室中,我向他介绍了这套书的构想,是每辑采访10位院士,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形象、生动、真实地再现院士少年时代的日常生活,展示院士少年时代的优秀品格和闪光的理想轨迹,给少年儿童以尊崇科学、热爱科学、敬畏科学的教育和启示。院士对这套书系寄予热切的期望,他分批次地推荐了院士名单,并介绍他们的杰出科学成就,还郑重其事地说:“科学与文学学科的交流与融合是很有意义。”科学需要幻想。我们的幻想点燃了。
编创者们怀着对少年儿童负责的使命感,怀着对科学院士们的敬崇的心情,极其认真、一丝不苟地投入采访中,接受采访的院士们严谨的科学作风,让人叹服。每位作者都对敬仰的院士们用恰到好处的语言画像,肯定他们对国家科学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现在,我们完成了第一辑和第二辑,后面还会有第三辑……一辑一辑地编写下去。
在我们即将离开草坪上“牛顿苹果树”时,惊奇地发现树的枝杈上花苞绽放了,花色粉白中浅红,娇柔迷人。我们蘸一滴“牛顿苹果树”的花色,像是给孩子们的未来种上一颗科学的种子!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