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售40万的爆火小说《泥潭》,读起来怎么样? 越过山丘,看到人性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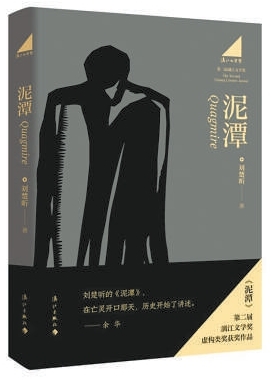
《泥潭》 刘楚昕 漓江出版社

刘楚昕,博士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院,现为湖北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其首部长篇小说作品《泥潭》于今年5月获“漓江文学奖”,在颁奖典礼的演讲上,他讲述了自己追逐文学梦想的心路历程,以及与女友的感人故事。刘楚昕女友一心鼓励支持他进行创作,却不幸因身患癌症去世,未能看到其小说的获奖、出版。演讲引发大众广泛关注和共鸣,《泥潭》正式上市前,预售达40万册,对于纯文学作品而言堪称现象级。漓江出版社供图
当我翻开《泥潭》的开头,“如您所见,我死了”。我就知道它一定会是一部口碑严重两极分化的作品。那些因为作者刘楚昕动人爱情故事“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而激情下单的人,大概率会大呼“看不懂”“上当了”,因为它压根不是一部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沉重的历史小说,爱情在整部小说中可有可无。
让我意外的是,扉页上并没有“献给×××”字样,在后记中,作者也没有提到亡故的女友。也许是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纯靠爱情故事出圈的“流量作家”?但不可否认的是,漓江文学奖颁奖现场的动情演讲,以及余华的推荐,让这位一部作品都未公开发表的新人作家,一跃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让《泥潭》创下了40万册的文学作品预售新纪录。
但是,客观来说,这却不是一本面向大众的通俗小说,刘楚昕在这部写了十几年的著作中注入了很大的野心,动用了很多花哨华丽的文学技巧,表达的主题也极其复杂宏大沉重。全书以辛亥革命前后为背景,分为三个部分。三个部分相互独立,但又暗含联结。分别从满人军官、革命党、中立神父的三方视角,来记录这场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动荡,以及在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人的命运如何随历史飘荡沉浮。
正如刘楚昕自己所说,创作这部小说的灵感源于雨果的“人类进步源于革命之后对暴行的反思”。在革命的暴力中,先前所有的秩序、所有的法律都荡然无存了,革命中有理性的建设者,也有非理性的杀戮。像小说中所展示的那样,旗人杀革命党,革命党反过来报复旗人,甚至一些无辜妇孺也未能幸免,再之后旗人又组织宗社党试图报复革命党……构成了无休止的泥潭。
如何走出这种泥潭?刘楚昕在扉页中把希望寄托于道德与良知——“迷失在黑夜中时,不妨抬头看看星空。如果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人应当面对自己的良知”。这段脱胎于康德的话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主旋律。
整部小说中,你很难看到传统意义上的“反派主角”,甚至传统观念中被认为腐朽堕落至无药可救的旗人,作者在落笔到具体的角色时,也赋予了不少温情色彩。旗人中也分三六九等,也有政治上的开明派,也有不谙政治、只求生存的普通人。但是,恶行和暴行却在一个个无名氏手中发生,读起来沉重且让人深思。
作为新人作家,第一部作品就挑战如此宏大厚重的题材,这种野心和愿景无疑是令人称道的。
作为“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刘楚昕还在《泥潭》中展现了出色的文笔和优秀的场景描写能力,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在第二部分中得到了充分的升华。你可以透过一个清末留日学生的视角,一步步看他从对政治的疏淡,到如何演变成激进的革命党,乃至成为武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再到他目睹革命的暴力后,又如何产生剧烈的心理波动和反思。常规叙事的第二部分也成为全书最出彩的部分。
不过,可能刘楚昕为了充分展现自己对不同文风和写作技巧的驾驭能力,在这部17万字的中体量作品中塞入了过多元素:魔幻现实主义、非线性叙事、意识流、日记书信体等。你能看到很多名作家的影子,比如余华、马尔克斯、福克纳、帕慕克、托马斯·品钦等。作者在后记中也感慨像是“不同风格的文字在打架”,使得自身也陷入了写作的“泥潭”。但是,如果放弃这些过多炫技的元素,用更常规的叙事方法来展现这部作品,也许会更容易让读者理解。
比如小说第一部分是以一个已死去的亡灵视角“我”来展开,对于读过余华《第七天》或者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的人来说,这样的开头并不陌生。但是,当读者以为接下来是亡灵视角的讲述时,作者又切回了“现实”视角。也就是现实中的“我”和变成鬼魂的“我”是并行存在的,成为鬼魂的“我”还会穿越到过去,看到过去的活着的“我”。其中还插入了大量的回忆和梦境,成为鬼魂的“我”还会出现记忆错乱,时间顺序也完全被颠倒打乱。这不免会导致普通读者难以分清书中的“我”到底是哪个“我”,是死去的“我”还是现实的“我”?是回忆中的“我”抑或是梦境中的“我”?比如在一段死去的“我”对妹妹的回忆中,出现了四段时间线被打乱的不同回忆,中间没有任何分隔和提示,需要反复阅读几遍,才能把一幕幕记忆碎片拼凑完整。有的时候你会怀疑自己到底是在读一本历史小说,还是在读一本变格推理小说。
为了致敬福克纳,《泥潭》多处出现了类似《喧哗与骚动》的不打标点长句。在某些段落,这样的长句可以展现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狂乱,如主人公目睹到残酷的暴行时,但在某些段落,这样的长句似乎意义不明,比如这句“您是咱们荆州旗人的骄傲将军对父亲说转头指着我说他将来也会和您一样”,反而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
此外,有可能是出版编辑仓促的原因,这版《泥潭》没有序言也没有注释,一些脏话如“他妈的”变成了“他□的”,属实有些矫枉过正。还有一些非常用词汇,比如文中多次出现的“戈什”,是满语中护卫的意思,读者如果不专门查阅会影响理解,若编辑时加上注释显然更好。
《泥潭》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出现了大量历史名词和事件,比如同盟会、光复会、哥老会、共进会、文学社、宗社党。这对熟悉辛亥革命这段历史的人来说可能不算陌生,但大部分读者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可能仅停留在中学的一两章课文,难免会一头雾水,也分不清这些派别的差异和内部存在的矛盾。这就更需要做好注释,或者在小说中加入对这些组织的介绍。当然,如果在文本中加入这部分内容,小说17万字的体量还有进一步扩充的空间。
如果能够越过文学门槛和史学门槛这两道“山丘”,你会发现这是一部不乏闪光之处的作品,在暴力和仇恨的泥潭中,仍然有人坚守自己的内心,在困惑和迷乱中闪耀人性的光辉。
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修订和再版中,作者和编辑能够对上述一些问题做出更好的调整,让它成为一本更优秀、更具传播力度的作品。
可能有不少人的确是因为营销号的“爱情宣传”而买书,泼天的流量让《泥潭》获得了更高的销量和关注,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视为一个普通读者接触严肃文学尤其是复杂文学的机会,让读者能够对辛亥革命产生新的认知和研究兴趣,那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