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玲小说《我和我的小尾巴》:天真烂漫的情感拓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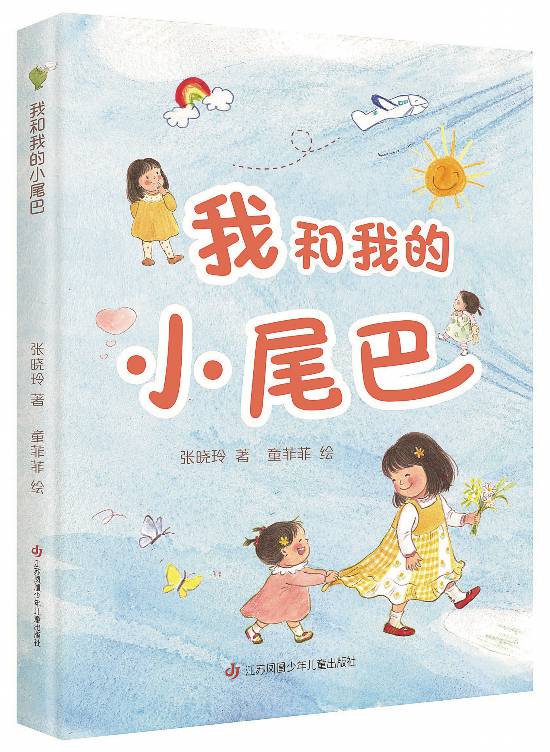
《我和我的小尾巴》,张晓玲著,童菲菲绘,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5年7月
儿童文学是“浅语的艺术”,追求“轻逸”品格,这已成为创作者的共识。然而,真正能将“深入浅出”这一艺术命题表现得炉火纯青的高手,仍是凤毛麟角。棘手之处往往不在如何“深”,而在怎样“浅”——要“浅”得贴合儿童的生活本真与生命绽放,且浅中寓深知、纳深情、藏深意、含深味。尤其以儿童视角叙事的作品,行文需如童言自述,却无刻意放低身段的矫揉造作之气。这对作者无疑是极大考验。
张晓玲的小说《我和我的小尾巴》,讲述二胎家庭的有趣生活,字里行间满是天真气息。书名既点明第一人称儿童叙事者的身份,也揭示了角色关系,暗喻家庭结构从“恒星中心”到“双星并峙”的秩序变化。小说中的“我”从自己将满4岁时开始讲起,诉说了从妈妈孕育妹妹到妹妹长至4岁间的生活变迁。小姐姐“我”发现并经历的“奇奇怪怪”的点滴,构成一则则可爱有趣的小故事。每个故事均可独立成篇,有完整的前因后果与高潮起伏。全书以“我”和妹妹的成长为线索,以幼儿口吻自述的方式,将这些氤氲着时光与情意的小珠子串联成串,映照着一路跌跌撞撞却逐渐自洽的成长身影。
身为家有二宝的妈妈与才情横溢的作家,张晓玲对生活中孩子的趣事信手拈来。她熟稔孩子的语言、情态、行为与心理,落笔时总饱含深情,字里行间满是生活的温度。比如大宝“我”对新来的妹妹——这个看似“夺爱”的家庭成员,态度几经起伏。在《记得还》中,“我”絮絮叨叨地说,自己用过的物品可以送给妹妹,不用还,“但这个抱着你的妈妈是我暂时借给你的,你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记得还”。这样的铺陈与对比,以率真稚拙的口吻,既展现了孩子的大度,也流露了源于对妈妈强烈爱意的“小气”,鲜活又动人。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记录孩子们的言行心理,描绘出一幕幕姐妹纷争与日渐深厚的手足情谊。
构筑亲情与反映成长,是这部小说的主旨。家人间虽难免有波澜,亲情却始终坚不可摧。姐姐因妹妹到来不得不事事“让着”,妹妹学会告状后,姐姐常会受到批评,承受了不少委屈与愤怒。原本是家庭“唯一恒星”的孩子,必须学着适应“双星系统”的新格局。正视这些“负面情绪”的存在与合理性,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治愈意义。所幸父母的智慧劝导与意外之喜,化解了诸多矛盾与委屈,让姐妹关系愈发亲密。动物园里,姐姐为让妹妹看到孔雀开屏,不厌其烦地亲自逗引。长大后分房睡,姐姐心甘情愿忍受妹妹的蛮横睡姿。当发现彼此想法诸多契合,姐姐甚至愿将妹妹当作“闺蜜”。这一路的转变,清晰展现了手足间从“对抗”到“共生”的和谐生态。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中的父母形象同样鲜活可爱,他们在摸索中学习如何更好地爱孩子、教育孩子。父母敏锐捕捉到姐姐的状态,用心调和家庭关系。他们愿意早起陪孩子看日出,全家相拥观日出的场景,定格成温馨动人的家庭剪影。
“天真”成为作者独特的认知方法与哲学立场。当成人作者放下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将叙事权力真正让渡给儿童,经由天真视角的观照,一些被日常经验和成人思维固化的问题,便会显露出本真面貌:有时,儿童未经污染的“直觉”,比经过规训的“常识”更接近事物本质。
《我想当妹妹》中,“我”发出这样的“天问”:“我的爸爸和妈妈总是固执地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大的要让着小的。可是,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平等意识,是孩子在与成人世界的博弈中逐渐萌生并强化的独立精神标志,这源于其对被尊重的深层需求。孩子的成长环境从未是隔绝现实的“真空”或“无菌舱”,他们会直面并思考各种看似“奇怪”的现象与规则,并尝试形成自己的应对策略。随着年龄增长,其思考也渐趋理性,比如关于“变大还是变小”的思索:“这世界已经向我展现出越来越多有趣的事物,原来模模糊糊的东西渐渐清晰,吸引了我更多注意力。我知道只有长得更大,才能看到更多、知道更多,所以,如果有人问我想变大还是变小,我……我想想,还是变大好了。”这虽是稚嫩的想法,却包含对生活命题的辩证思考。
小说中最动人的教育哲学时刻,出现在《妹妹的小树》这个异想天开的小故事里:姐姐没有用科学理性去戳穿妹妹拿竹签当树苗种的荒谬,而是选择维护这个美丽的错误,呵护妹妹的天真信念。姐姐虽不相信竹签会长成树,却依然相信世界总会带来意外惊喜,这一态度体现了包容、欣赏与合作:“谁知道这两根竹签子种进泥土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个世界有多奇妙,我们人类啊,根本不知道。”儿童是天生的现象学家,常会悬置判断,让事物如其所示地呈现。小说以此结尾格外美妙,既自然展现了儿童认知的珍贵品质——对可能性的开放态度,也表达了对成长的未知性与丰富性的理解和拥抱。
小说尾声《写在后面的话》,是长成小学生的“我”(也是作家自身)的心语表白:“不管我们是不想长大,还是希望快点长大,日子都会这样不紧不慢、不长不短地过去,谁也不能拖着我们往后退,谁也不能拉着我们往前跑,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我们都只能用自己的速度前行。”至此,关于成长的思考既有了日常的平稳感,也有了存在论的哲理深度。
文学具有镜子与窗户的功能:作为镜子,这部小说让儿童读者看到自己的影子;作为窗口,这部小说让成人读者看见并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或许还能促使他们以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成长关乎每一个“个体”,是个体在每个瞬间与周围世界及自我内心协商的动态过程,因此有着独特的方向、速度与节奏。《我和我的小尾巴》不回避家庭结构变化给儿童成长带来的心理裂痕,以平实的笔触,描绘了从这些裂痕中生长出的新的情感可能。它用趣味丰沛的故事呈现童年生命的情感轨迹,也以天真视角刷新我们对世界和成长的固有认知,完成了一场由儿童主导的认知革新。如此清浅,又如此通透。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