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如何“长编”——读李扬《沈从文年谱长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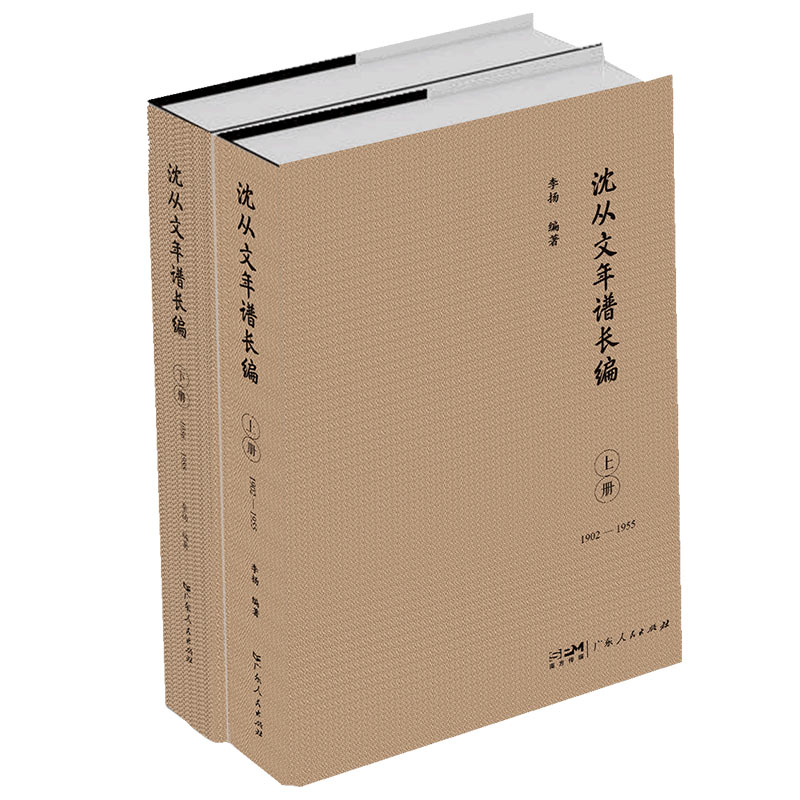
引言
2016年,针对近几十年来的“年谱长编热”,陈福康表达了一定的批评意见。[1]三年后,桑兵撰文回应,认为陈福康“同样并未自觉分别年谱之后再做长编的价值和意义,只能回到长编的本义自我反省,未能进而探究发掘长编体裁的潜力”,并倡导借鉴陈寅恪等人关于“长编考异法”的论述,将“长编”建设为一种不可取替的学术体裁。[2]100笔者对此深以为然。由此回看《沈从文年谱长编》(李扬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以下简称《长编》),就有了别样的欣喜:一方面,《长编》可谓近十几年来沈从文研究史料工作的集大成者,弥补了《沈从文年谱》(吴世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简称《年谱》)出版较早、材料遗漏较多的缺憾,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沈从文理应有“长编”行世;另一方面,《长编》也是“长编”体裁建设过程中的可贵尝试,虽非尽善尽美,却已足够丰硕,探讨其得、失,自然大有裨益。
一、“资料求全”:《沈从文年谱长编》的史料准备
“年谱”修撰力求“竭泽而渔”,“长编”当然更是如此。想实现这一点,相关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系统性、持续性必不可少。作为深耕多年的沈从文专家,李扬无疑具备这项条件:从《沈从文的最后4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到《沈从文的家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再到《长编》,时间跨度达二十年。在《后记》中,编著者自述:最初只是“为《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和国家社科项目‘沈从文后期思想、创作研究’做初步的资料整理工作”,但“《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和项目结项后,发现已经积累了30多万字的材料”,又率多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沈从文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失收或异于现有结论的材料,“对作家的行止、文章出处、版本流变等方面的表述多有补充”,便于2013年以“沈从文年谱长编”为题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并获准立项,自此正式启动撰写工作。为使《长编》“更加系统、科学、准确”,编著者“先从核校沈从文文章的原始出处、版本入手,而沈从文又与文艺副刊联系密切”,于是“陷入了报纸文献的海洋中”,“遂向教育部社科司申请延期,社科司同意延期至2019年12月结项”。此后,编著者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艺副刊文献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的研究工作,“遂利用还在建设、完善中的‘中国文艺副刊数据库’,不断增补材料,从结项时的100万字突破至120万字”,故而《长编》姗姗来迟。[3]1231有趣的是,因为编著者长期浸淫于“后期沈从文”研究,在这一方面积累尤多,所以1946年之后的内容在《长编》中比重偏高,总计78万字左右,较诸《年谱》对应部分,增加逾50万字。
总的说来,“沈从文研究文献保障体系”的构建起步较早,并在渐次完善中:1982-1984年,《沈从文文集》(12卷)由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书店联合出版;2002年,《沈从文全集》(32卷)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于2009年推出修订本;2006年,《沈从文年谱》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沈从文研究资料》(2册)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2020年,《沈从文全集·补遗卷》(4卷)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4]70-72……其间还有许多集外文陆续披露出来。因此,《长编》的意义首先在于公开文献的系统整合(包括搜集、甄别、校雠、考异、勘误、注释等),尤其是散落在各类报刊、图书(如《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收获》《中国社会科学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王献唐师友书札》等,还有地方资料如《云南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刊物如《舞蹈论丛》)中的佚作及其他史料;此所谓“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陈垣语)也。
除了“索引”“目录”功能,新资料占有量也是衡估“年谱”“长编”价值的重要尺度。在修撰过程中,李扬发掘了若干重要材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47年1月18日天津《大公报》(另载1月21日沪版《大公报》)刊出的《新书业和作家》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印刷厂1944年4月初版《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根据前者,李扬撰写了《从佚文〈新书业和作家〉看沈从文与郭沫若关系》,通过文本细读、版本校勘、论争史爬梳,还原了沈、郭交恶“迭次累加”的过程[5];根据后者,李扬撰写了《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的一个独特版本》,经由一系列逻辑缜密的勘考,指出此书系“沈从文的一部自编文集,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6]160事实上,有鉴于“无论是沈从文全集的编纂,还是各种沈从文年谱、传记,尚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沈从文作品的版本变迁”的现状,编著者在着手《长编》近20年的时间里,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沈从文作品诸版本的搜集、汇校工作上[7]153,仅就其系统性而言,《长编》的版本学贡献已不容忽视。
所谓新资料之“新”,不仅显现为“辑佚”(包括谱主撰写的小说、诗歌、散文、杂论、书信、批语或其他档案文献),更指向一种考察视野的拓宽、取材范围的扩大,诸如《年谱》未收、《全集》难收而《长编》“择要采撷”的“访问记”或“访问纪要”,无论是1933年11月30日《庸报》刊登的《素描——北大国文学生茶话会上巴金、沈从文、杨振声剪影》,还是《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4期发表的《文联旧档案:老舍、张恨水、沈从文访问纪要》,都是“能反映谱主的思想发展、精神状况和心理动态的材料”,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谱主生活的世界。”(《长编·编写说明》)《长编》取材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周边史料、非谱主文字的征引中,如各类报刊上的编者按语、编辑余话、出版预告/广告、文艺消息等,及蔡元培、胡适、杨振声、丁玲、巴金、施蛰存、赵家璧、张家姊弟、常风、萧乾、卞之琳、季羡林、汪曾祺等人的日记、书信、回忆,通过丰富史料的“聚合反应”,以求重建历史“原境”及其“感觉结构”,尤其是风云激荡的20世纪中国历史语境中多面、多变、色彩驳杂的人物形象。有关这一点,只要你翻开《长编》的“主要参考文献”,即可直观地感受到后者取材何其“广”,编纂何其“苦”了。
二、“识断求精”:《沈从文年谱长编》的编撰追求
毋庸置疑,“一部年谱的成功与否,水平高下,首先看作者处理史料的能力”[8]131,而“长编”尤其需要这种“识断力”。所谓“识断之精”,语出陈寅恪《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这种境界,“宁失之繁,无失之略”(司马光语)的“长编”如何抵达呢?就《长编》而言,其“精”主要体现为材料引用的详略合宜,因为“所有材料都要入谱,只是根据材料的重要性对其内容做多寡的处理”,要先“判断出材料于谱主的意义,再根据这些意义处理材料”,“引用材料之详略,即取决于该材料在谱主生平、事业中的重要性”。[9]132正是编著者的“识断之精”,决定了《长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史料扩张”或“资料长编”,而是种别开生面的“学术文体”。
在《编写说明》中,李扬自述其编撰原则:“谱主撰写的文学作品、书信、档案文献等,凡未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沈从文全集》者,为反映谱主生活、思想、精神全貌,凡属书信、诗歌、杂论等篇幅较短的文字,均原文照引;篇幅较长的小说、论文类散佚文献,则加以考订后,注明出处。”此处,“引”与“不引”的分梳标准,一个是史料性质(是否集外),一个是篇幅长短。换言之,已入《全集》的作品一般不引,只写明文体、标题、原始出处及卷期数、署名、《全集》收录情况等基本信息,例如1924年12月22日条:“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发表于《晨报副镌》1924年第306号,署名休芸芸。这是沈从文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收入《全集》第11卷《遥夜集》。”[10]31未入《全集》的“短”文献勘误后全篇引录,如1931年6月30日《文艺月刊》第2卷第5-6期合刊上的诗歌《给一个医生》、1957年4月10日《新闻与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第13号上的《我如何编大公报星期文艺》、《收获》2013年第1期上的《沈从文书简》等。未入《全集》的“长”文献考订后注明出处,如1971年6月1日条:“完成《来的是谁》。这是作者拟写的家史兼地方志类型小说的‘引子’部分。……本文未收入《全集》。收入刘一友著《文星街大哥》(漓江出版社2007年版)。”[11]871你不难看出,这一层面的资格认定,暗含了编著者对文献史料价值梯度的判断;散佚文献、稀见史料,在价值光谱中一向位置较高。但《长编》并非“为辑佚而辑佚”,首先是因为《男女谈》“对理解沈从文的性别观有重要作用”,《我如何编大公报星期文艺》系“沈从文专门讨论文艺副刊的一篇长文,对理解沈从文的副刊编辑理念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才全文征引;而这些佚文的“作用”“意义”,又必须在沈从文研究的总体视野中加以把握,这就对编著者的“识断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应该说,以珍稀程度来裁决引录与否,并不难办。“识断之精”的更高一维,在于一般性文献(已入《全集》者)的价值估定,凡是能够反映谱主写作史、生活史、交游史、精神史、情感史、生命史的基本面貌、迁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材料,均应视其意义大小而予以不同篇幅的摘引,乃至全录。如1929年6月沈从文“为中国公学教职事”致胡适信,已收入《全集》第18卷,但因其“关涉沈从文生平重要史实”,“特录全文如下”。[12]82再如1951年9月2日沈从文致青年记者信,已收入《全集》第19卷,但因其“贯注着沈从文对文学创作、政治时局、个体生命的不同流俗的理解”,故“摘引如下”。[13]583在此意义上,《长编》仍然发挥着“资料书”的作用,使读者不必通读《全集》《补遗卷》即可了解沈从文的人生历程与思想脉络,使研究者能够更直观、连贯地感受沈从文某些内在参数的“变”与“常”,同时也方便其引用文本。总体上,《长编》很少征引谱主的文学类文本(如小说、诗歌等)而较多征引实用类文本(如杂论、序跋、题识、书信等),因为后者更具现实性、直接性,构筑了我们探讨特定历史语境下沈从文的文学生产、生命体验、思想观念及其流变的坚实基础。
此外,“周边史料”的征引与否、摘录多少、聚焦什么,也将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比如1936年10月25日“《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第237期”条后面,编著者不仅征引了《大公报》的“编者按”,对《清华周刊》《希望》《通俗文化》《文化动向》上甄奚、乔木、林珂、北鸥的文章标题进行著录,还引录了1937年1月15日《书人》创刊号上重点推介该文的《中国文化界两个重要的宣言》,又在1937年2月21日“《一封信》同时发表于天津、上海《大公报·文艺》301期”条后面介绍道:“沈从文的《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发表后,引发了强烈反响,编者为此特意在本期组织了‘讨论:反差不多运动’专刊,《一封信》是沈从文对‘反差不多’运动讨论文章的回应,表明自己的态度”。[14]276从谱主的文章到编者的态度再到引起的反响,从分散的“反应”到集中的讨论再到谱主的态度,层层递进,构成了“接受史”与“思潮史”的基本面目。美中不足的是,以上种种均系公共空间内的言说,缺乏私人场域(日记、书信或私人间交谈)的参照,而后者或许携带着历史深处的更多复杂性、模糊性。
三、“长编考异”:《沈从文年谱长编》的“众声喧哗”
提到“长编考异”,不由得想起洪子诚在《材料与注释》中的试验:“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15]2而“长编”体裁所追求的,不仅是“某一时间、问题”的多重互证,还要在“时间、问题”的连缀中贯彻这一原则。
前面说过,《长编》取材开放,征引了大量非谱主文字。编著者或许意在丰富历史细节,但不同主体、视点的引入,却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叙事的张力,也避免了以谱主的是非为是非。如1933年6月14日条:“因沈从文不守时,张兆和颇为生气。”支撑这一叙述的,并非沈从文、张兆和中的某一方,而是旁观者张宗和的日记,其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沈先生就夸他自己怎样的威吓她,要她吃饭,又说她本来就想吃饭了,但又不得不下台……三姐也不辞,我猜其中一定有假话。后来我问三姐,她说‘他本事大么’。”[16]177日常生活、家庭关系中的谱主形象便在一种三维结构中立体化了。再如1935年2月1日“巴金的散文《沉落》发表于《文学》第4卷第2号”条后面,编著者援引巴金的一段回忆来说明两人的分歧所在:“从文读了《沉落》非常生气,写信来质问我……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从文不理解他。可能我们两人对周都不理解,但事实是:他终于做了为侵略者服务的汉奸。”[17]235还有1949年4月8日卞之琳致巴金信中所说的“私交上讲他太对不起我”[18]552,虽不知其所指,也不确定孰是孰非,编著者还是将这样一条可能“不利于”谱主的“待考”材料照录无遗。不溢美,不隐恶,此史家之所为也。
最能体现《长编》问题意识、对话意识的,是对丁玲、萧乾的反面意见的征引。丁玲、萧乾同沈从文的交恶,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两桩公案,对于我们透视沈从文生命史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不同侧面,乃是一种特殊存在。《长编》的处理办法,便是“陈述事实、征引文献,不作主观阐发和议论”,“偶有按语,只是对相关问题的分析、对比。”(《长编·编写说明》)如1931年2月9日“上午,为营救胡也频事,与左恭一起去面见陈立夫”条后面,《长编》分别引用了沈从文《记丁玲续集》(1939年)和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1950年)的不同叙述,观点、态度、倾向多有不同,而《年谱》仅列出“见陈立夫”这一事实,多少缺乏心灵史的参照与历史纵深感;再如1936年6月14日条:“《京报》第7版发表消息《传闻失踪之丁玲女士现已来平寓于沈从文处,平妇女团体将开会欢迎》……《丁玲年谱长编》中的记载与此消息不同,丁玲后来未提及此次北平之行见过沈从文,但据张兆和、刘祖春回忆,丁玲此次来平,到过沈从文家。何者为确,待考。”[19]261不动声色的表述背后,似乎有大的隐含,但编著者的主体意识并未溢出、越轨,不致左右读者判断。美中不足的是,1980年代丁玲对沈从文的批评(如1980年《诗刊》第3期上的《也频与革命》)被遗漏了;在笔者看来,《长编》不仅需要摘录相关内容,甚至该全文征引,以存其真。由此亦可见出,“长编考异”的书写实践,需要更多时间才能臻于成熟。
相较而言,《长编》对沈、萧失和中“杨振声事件”的交代更全面、细致,也更凸显出一种内在于学科的问题自觉。相关内容集中于1978年11月15日“写作《我所知道的杨振声先生》”条与1982年3月“赴荆州参观前,写了几段回忆杨振声先生的文字,无标题”条,“由于这些文字均曾引起非议,而又未曾收入《全集》”,兼以“萧乾对沈从文晚年对待杨振声的态度颇有微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这桩公案的理解”,“为使读者了解真相”,编著者从《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黄河出版社,2007年)中全文著录了三篇稿件,又通过摘引张兆和、萧乾、杨起的书信、文章,基本厘清了这桩公案的来龙去脉。[20]1015-1017,1133-1137相关文本及其来源并置一处,判断权就交到了读者手中,所谓“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陈寅恪语)。似乎稍有“出格”的是,在材料爬梳之后,编著者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从这些文字来看,显然不是先生为《杨振声文集》出版而作的序,只能是为写杨振声先生传记提供材料。”“萧乾信写于1991年2月1日,从当时的政治情势而言,似不应引出那么严重的断语,显然,萧乾带有他自己对沈从文的成见。”“且不说上述文字是否为‘序’而写,虽然沈从文的这篇文章确实有些问题,但结合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思潮,所谓‘牵连’‘大批判’‘恶毒’之语,似乎与实际情况不符。”[21]1137可在笔者看来,这正是“长编”体裁区别于一般性“资料长编”的特出之处,即事实上的叙述主体(编著者)的位置、姿态,即如余英时所言:“每个人既然不能避免主观,那么最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主观的问题,把基本的假定提到一个明确的境地来,提到一种自觉的状态来。”[22]87一方面,编著者的叙述相对克制,且以“注释”的形式明确和限定了自身位置;另一方面,叙述主体也参与着“众声喧哗”的形构,为我们理解这桩公案提供了一重视角,而研究者本就掌握较当事人为多的材料,有着相对超脱的心境,更可能在整体观照中超越具体的纠葛、缠绕,为一团乱麻捋出线索,使一团混沌显出澄明,其意见同样值得参考。
结语
毋庸置疑,《沈从文年谱长编》是近十几年来沈从文研究史料工作的重要收获,并在“长编”体裁的建设过程中迈出了坚实一步。如果说白璧微瑕,问题主要出现在校对上;因其体量之大,字体、排版偶有错置,但也无伤大雅。作为“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樊骏语),沈从文研究史料工作难有止境,因此《沈从文年谱长编》的出版,并非沈从文相关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终点”,而是“沈从文研究文献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与“沈从文研究”不断深化的新“起点”,一条新的历史地平线。
注释:
[1]陈福康.“年谱长编”的“长编”是什么意思?[N].中华读书报,2016-3-23.
[2]桑兵.长编考异法与编年体的演进[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00.
[3]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1231.
[4]此处仅举其要者,详参邱仪.从文学到历史到心灵的探寻——沈从文研究与书写的当代进路[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70-72.
[5]李扬.从佚文《新书业和作家》看沈从文与郭沫若关系[J].新文学史料,2012(1).
[6]李扬.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的一个独特版本[J].新文学史料,2024(1):160.
[7]李扬.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的一个独特版本[J].新文学史料,2024(1):153.
[8]宋广波.对年谱、年谱编撰的新思考[J].东吴学术,2024(2):131.
[9]宋广波.对年谱、年谱编撰的新思考[J].东吴学术,2024(2):132.
[10]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31.
[11]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871.
[12]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82.
[13]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583.
[14]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276.
[15]洪子诚.材料与注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
[16]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177.
[17]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235.
[18]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552.
[19]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261.
[20]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1015-1017,1133-1137.
[21]李扬编著.沈从文年谱长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1137.
[22]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新亚书院研究所、新亚书院文学院联合举办中国文化讲座第二讲记录(1973年12月2日)[A].余英时文集(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7.
(注:本文是山东大学首届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1930年代以来山东大学中国现当代作家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SDU-QM-B2024047]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