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叙事中的精神回响 ——论作为情感社会学样本的《万川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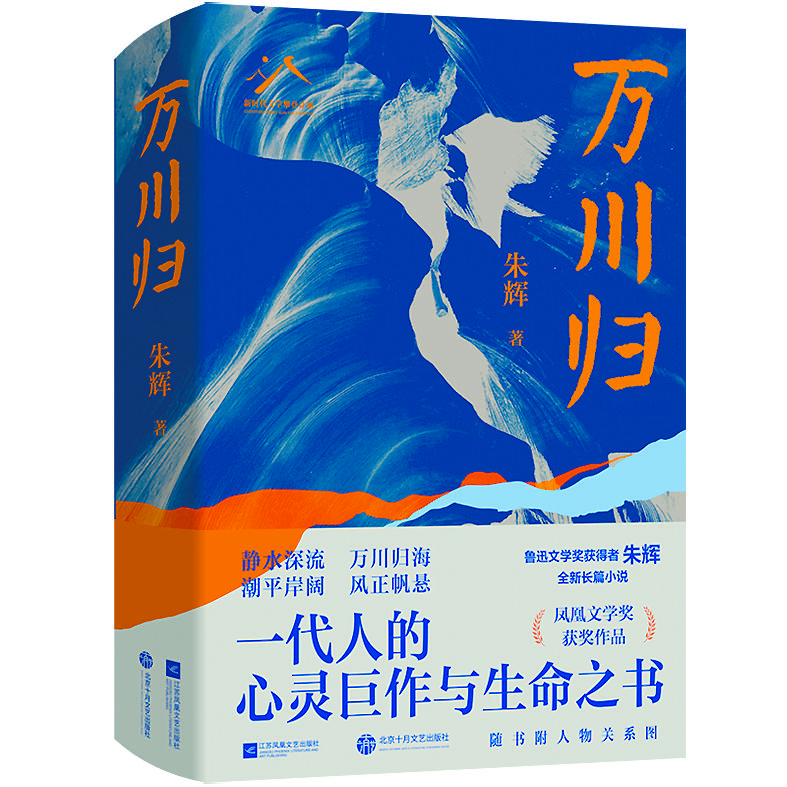
在朱辉的五部长篇小说中,《万川归》显然独标一格,这不但因为它是朱辉的近作,是积累了二十余年的厚积薄发之作,更在于它是一部总括之作,一部力图用“显微镜”和“透视镜”两种视角去呈现“60后”一代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心史,它内蕴着有关时间与命运的宏大叙事,但又细致地以个体经验为承载,超越了类似题材小说情节铺陈为主的模式,转而深入探索人物的情感结构和生命感悟,体现出一种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深度叙事”。关注情感的社会学家指出,个体的情绪与感受不只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它也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规制,因此,捕捉个体具有意义的生活瞬间和人们彼此相连的共通情感,展现个体在驳杂世界中特别又富有意味的生命体验,有助于从感受或情绪的角度提供对社会变迁的结构性洞察,这就是一种“深度叙事”,就像米尔斯说的那样:“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旅程。”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以史诗书写为抱负的文学作品。
而《万川归》的特别正在于此。小说的三位主人公“万(风和)”“(丁恩)川”“归(霞)”虽然遭遇的都是偶遇性的个体事件,比如万风和先是得知儿子并非亲生后又知晓自己也是抱养、归霞遭遇到的绑架等等,但这些个体事件依然带有巨变时代的社会讯息。又如万风和从农村到大学、从教师到商人的身份转换,归霞从水利专业高材生到机关闲人的蜕变,丁恩川坚守专业却边缘化的处境,小说提取了时代浪潮渗透进日常生活毛细血管的几个典型样本,并以这些“生命故事中的细节”为基础,“通过近距离和整体性的观察”,揭示了“生命历程本身及其与社会历史进程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将社会结构性的压力转化为具体的情感体验,铭刻了他们在时代转型中的希望、恐惧与骄傲,忠实记录了他们在时代的列车上那些脱序和脱轨的时刻。
万风和是小说中着墨最重的人物,他的人生轨迹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小说既肯定了他把握时代机遇的能力,也揭示他机会主义的人生选择暗含的潜在代价。作为平民子弟,他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留校任教,后下海经商,迅速积累财富,堪称改开一代“阶层跃升”的范例。然而,成功光环之下的精神危机才是小说聚焦的重心。亲子鉴定显示儿子万杜松并非亲生,自己又被证实是养子,两段婚姻相继失败,身体健康亮起红灯,房地产投资岌岌可危——这些接踵而至的打击使万风和陷入严重的情感内耗,却也意外获得了深刻自省的契机,开始晓悟“生活如海”,它渊默如斯、狂暴如斯,也宽阔如斯、包容如斯。他在洞彻中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特殊的救赎之路,接纳非血缘的儿子,大方承认自己的养子身份,从血亲伦理的迷思中走出,通过对器官捐献者李弘毅的感恩和对建设者丁恩川的称颂,为个体、社会和人类的情感找到了更宽广的归处。
归霞对自我的寻找则呈现出另一种轨迹。作为功利地放弃专业追求的知识女性,她的精神危机实际源于自我价值的失落,精于计算固然带来生活的优渥,却也悄然损耗着真实的生命感觉,她不得不面对那个被自己一直雪藏的问题:当生活被简化为风险规避和安逸的退缩,它还值得经历吗?她的失眠、抑郁和崩溃的肾脏给出了答案,而她艰难的自救也就此开始。
作为归霞的大学同学,丁恩川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的路——投身西北水利建设,成为业内顶尖的专家。他是万风和与归霞的另一面,是小说在辽阔的生活之海里一个醒目的精神锚点,明显带有理想的光环,也处处显露了作者在专业和性情上的双重偏爱。但这个“国之重器”建设的栋梁却并不给人说教气,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在道德的诘问和探索上,《万川归》同样呈现出深层叙事的追求。小说并没有提供简单的道德判断,而是通过不同人物的选择,展现了人生抉择的多种面向,以追溯个体生命传记的方式来揭示选择的意义。而且小说也没有回避他细微的纠结:对归霞未说出口的眷恋,对城市生活的隐秘向往,还有在学术尊严与现实压力间的摇摆,拒绝简单评判的叙事姿态,使小说对生活之境的呈现具有了更真实的复杂性与包容度。
《万川归》虽然容纳了巨量的时代信息,也刻画了多个人物离散跌宕的生活,但本身却并不在“故事性”上发力:一方面,它执着于对几位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度挖掘,抽丝剥茧般揭示他们的精神困境与隐秘心事;另一方面,它又刻意保留了许多情节上的空白,不对所有悬念提供明确解答。这种精神深掘与叙事留白的艺术平衡,使小说既具有心理现实的深刻性,又保持了生活本身的开放性与神秘感。小说不停在全知叙述和内视角的潜入间转换,把细微的心理悸动和当它们被投入生活之海所激起的情感涟漪细腻又宽绰地呈现出来。以万风和为例,小说完整描写了他从发现儿子非亲生到最终接纳这一事实的心理过程:最初的震惊与愤怒甚至想到自尽、对妻子的怨恨、对儿子的矛盾、对自我的怀疑,以及最后的释然与接纳。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心理演变并非直线进行,而是伴随着万风和的事业史、情感史的起伏还有个人身体由康泰到衰朽的变化,充满了辗转与震荡,也真正勾画出一个“筋疲力尽的业绩主体”在面对家庭危机的复杂反应以及重建坍塌的精神世界的艰难。
与对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形成对比的是,小说在情节发展上却保留了大量空白。许多同题小说会详尽交代的悬念,在《万川归》中始终悬而未决:绑架归霞的罪犯究竟是谁?万风和第一任妻子杜衡为何会有外遇,万杜松的生父到底何许人也?第二任妻子璟然为何不辞而别,她口中遇到的“他”是谁?这些情节线索本可延伸出更多的戏剧性冲突,但朱辉却有意不予解答,让它们成为叙事的“缺失”。现实生活中本就充满无解之谜,人与人之间永远存在着无法完全沟通的隔阂。试图解释一切、揭示一切的写作,反而会失去生活的真实质感。朱辉像一位精准的外科医生,知道在何处下刀能触及灵魂的隐秘,也明白哪些伤口和病灶不必完全剖开。这种克制的叙事艺术,最终指向小说的主题——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解开所有谜团,而在于接纳生活的不确定性,在有限的理解中寻找无限的共鸣。
小说的叙事结构也很值得探究。“万川归”三位主人公看似独立的人生轨迹,借由一系列巧妙的机缘联系起来,这不仅突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局限,更在形式与主题上形成深刻呼应。小说开篇,三条线索平行展开:万风和的商业奋斗与家庭危机、归霞的婚姻困境与精神崩溃、李弘毅的底层生活与意外死亡。这些人物之间本无密切关联,仅有偶然交集——万风和与归霞是同年代大学生但原本并无交往,李弘毅曾是万风和公司所在写字楼的保安,但也仅此而已。这种疏离的人物关系,正像小说所言:“生活如流水。但一条河里的鱼不认识另一条河里的鱼,一滴水不认识另一滴水。”然而,李弘毅车祸身亡后将所有器官捐赠,将原本陌生的生命紧密联结在了一起。可以说,李弘毅在小说中具有特殊的结构功能,他死后仍以另一种形式活着,成为聚合各个人物的隐形纽带,并提供了一种超越个体的精神共同体想象。当不同社会阶层、生活境遇的人们因为器官捐赠而产生生命交集时,一种基于情感和信义的善开始在新的生命体中生长充盈,它滋养精神,让得益的人们跳脱地缘、血缘和学缘的画地自限,从更本质和宽广的基点上重建理想。
朱辉是水利专业出身,他很擅长将水的物理特性转化为观察人生的独特视角,“万川归”的题旨也由此获得了形而上的升华。小说中流淌着丰沛的水的意象,从开篇飞机俯瞰下的长江黄河和淮河,到贯穿始终的“生活如海”“人生如跳水”的比喻,再到归霞最终选择的江葬,水在小说中形成了完整的象征系统。尤其结尾处归霞的安葬场景,静穆的江面上流霞映空,暮色熔金,映照着“归霞”之名,她终于回到了那个辽阔之海。每个生命都是独立奔流的河水,它们有不同的生命轨迹和不同的生活选择,但最终都将融入人类共同的精神海洋,不过,必须指出,这是一个辩证的逻辑,千万条河流以不同路径奔向大海,人类的精神归处也不应被简化为单一模式,在物质主义盛行、在爱欲消失的时代,《万川归》对精神旨归的多维探索,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