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宁:述说历史的另一种视角 ——关于刘霄的长篇小说《白牛》
阅读刘霄的长篇小说《白牛》,是一次十分新奇的接受体验。其有如神来之思的创意和颖异超卓的想象力,是对当下小说创作的一次新的冲击、新的展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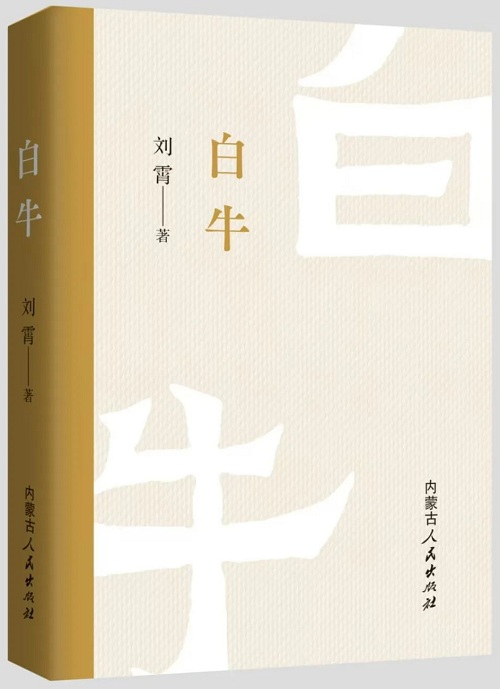
《白牛》可归类为动物小说,是以动物为主人公、讲述动物生活、表现动物命运的虚构作品。小说第一人称主人公2号,是一头夏洛莱牛,全书叙事以2号的视角回望、展开和结束。以动物为第一人称主人公,这在动物小说创作领域中虽不常见但文学史上早已有之。日本作家夏目漱石(1867年~1916)190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我是猫》,即是以一位教师家的猫为第一人称主人公,以这只拟人化的猫主人公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社会与人性。《我是猫》虽然也对动物之间即猫世界的生活有所涉及,但这并不是其重点所在,因此与其关于人类社会与人性的描写和批判相较,关于动物生活的叙事部分,并无足够的深入。《白牛》则首先是一部扎扎实实的动物小说,它对动物(夏洛莱牛)的生活、情感和命运,有十分细致的观察、揣摩与描述。诚然,这是一场想象力的驰骋与翱翔,但其间需要强烈的自我的代入与共情。小说中的主人公2号,50年前的1973年,从法国索恩-卢瓦尔省夏洛莱地区的农场被选送到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2号在故乡无忧无虑的欢乐的少年生活:“一群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伴正在宽阔平坦的草坪上急速奔跑着,像参加一场没有指挥、没有裁判、没有规则的自由短跑比赛。这样的娱乐项目在这里经常上演,有时一天会重复好几次,但大家都乐此不疲,几乎能达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效果。在那个精力过剩、情窦未开的年龄段,奔跑成了释放体内洪荒之力的最佳方式,无论是一头公牛犊,还是一头母牛犊。”作品也浓情深意地表现了2号被送往中国时与父母“生离”其实也是“死别”的惊心动魄、撕心裂肺的场面:在2号和父母的种种反抗与拖延均无效之后,2号走上卡车,“卡车发动了引擎,向前驶去,我再也没有忍住,将头扭了回来。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眼看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这也是我最后一眼看我至亲至爱的双亲。如果我错过了这一眼,此生有可能再也没有下一眼。父亲和母亲一路小跑着追赶卡车,他们笨重的身躯显得非常吃力,‘儿啊,保重身体,我们很快就会去看你。’母亲边喘着粗气边向我呼喊。父亲默默地向前跑着,没有说话,像在陪伴着母亲一样奔跑,怕母亲一个人在奔跑的路上孤独。”小说还十分令人动容地叙写了2号和1号只能克制隐忍、有爱无性的爱情。动物小说是想象力飞扬的天地,但也同样需要真实感,这种跨越人与动物边界的写作,要求作者深入的移情体验与共情思考。牛也是与人相伴的动物,人对牛比对虎豹等动物要了解和熟悉得多,这种了解和熟悉为以牛为表现对象的动物小说的写作提供了一种逻辑,《白牛》的创作在充分放飞想象力的同时,显然也遵循着这一逻辑构思故事、组织情节和塑造形象,因此能够唤起读者感同身受的共鸣。
《白牛》又不止是一部动物小说,它还是一部讲述历史的小说。2号来到中国至今已50年,它和内蒙古草原人民一起经历和体验了半个世纪的历史。2号和她的同伴们来到中国,是命运的偶然性,亦是历史的必然性。1973年9月,应中国政府邀请,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中国。蓬皮杜是第一位访华的西欧国家元首,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程陪同,并将山西大同工匠精心打造的雕有“九龙奋月”图案的铜火锅作为国礼赠送给蓬皮杜。同年10月,蓬皮杜回赠周恩来总理50头夏洛莱牛,其中十七头被送到内蒙古培育。《白牛》以此历史事件为背景,展现了叙说历史的宏图。小说中的2号因为参加法国全国性种畜大赛获得第三名,所以作为50头夏洛莱牛之一被选送到中国。2号不再只是一头普通的、生物学和动物学意义的牛,而且是一个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是一头“国家牛”“政治牛”和“文化牛”。这是《白牛》这部小说叙事的立意重心。作为宝贵的种牛,2号和同伴们的到来,使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和锡林郭勒盟获得了先进的冻精和冷配技术,使中国获得了五万八千头纯种的夏洛莱牛后代,并形成了独特品种的本土化改良牛群体——乌珠穆沁白牛。2号也见证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打倒四人帮”“草畜双承包”生产责任制、国营牧场的改制、通信技术的发展等历史事件和历史变迁,目睹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等标语所标志的治国理念的落实,还看到了“内蒙古的五大任务”的提出和贯彻……这些标语和理念,“浓缩了时代”,也凝结着历史。《白牛》的写作不仅着眼于白牛们作为动物吃喝拉撒的日常时间,更着眼于它们与人类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时间,通过对历史时间的观照和把握,使小说具有历史的质感与重量。
《白牛》则是一部“突破尺度”之作。2号和同伴1号,被作者赋予超能力,像人类的智者一样通天彻地,生活哲理头头是道,古今诗词倒背如流。作者如此大胆地塑造动物形象,是为了实现述说历史的意图,《白牛》成为一部半个世纪内蒙古草原发展变迁史的文学呈现,而它的独到的叙事方式,包括对历史的是是非非的评判,便是采取动物的视角。关于这一视角的价值,小说借1号和2号的对话予以揭示:“咱们这是牛眼看世界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就是那些拥有雪亮眼睛的群众,尽管我们是一头牛。”“还有一句话叫‘旁观者清’。我们就是那些看得很清的旁观者,尽管我们还是一头牛。”这几段牛的“对话”,即是人的对话,是人对动物进行换位思考,是对草原治理理念、政策是否符合草原实际,是否有利于草原生产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发挥牧业优势、发展生态牧业等等的一个新异角度的观察。而小说中“牛的视角”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还作出了对某些时期决策的评判,如关于夏洛莱牛所属的达青宝拉格牧场改制,2号和同伴们从国营牛变成了个体牛,2号认为这一改制“对纯种夏洛莱牛的繁衍以及夏洛莱牛与本地牛的改良工作冲击之大,是有目共睹且无可争议的”。对历史的直言,使《白牛》获得了一种勇于担当的文学品格。
《白牛》的历史叙述的意义,不仅是对内蒙古草原半个世纪发展历程的回眸与梳理,还是关于中法关系和中法友谊的珍贵记忆和存照。小说对这一意义也进行了充分的开掘,2号和同伴们乘着从巴黎夏尔·戴高乐机场前往中国上海的飞机,念着故乡的父母,想着无法自己把握的命运,不禁伤心欲绝。接着,2号也想起了从故乡动身前农场主人与那三个来接它的陌生人的谈话:“他们说,我是肩负着法中两国友谊的使命出发的,要做一头有家国情怀的牛,怎么能计较个人得失呢?”而1号在临终前感言:“日久生情,我早已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我觉得,我就是中国的一头牛。当然了,我们最初是肩负着法中友谊的使命来到这里的。我们终究不辱使命,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中法友谊将会地久天长。”诚然,在人类的常识中,一头牛是绝无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和认识的,但小说中2号和1号的这些“思索”和“话语”,提醒着读者在国际风云激烈动荡、中国和西方合作又竞争的今天,保留这一段感人肺腑的记忆,体会这些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大地的夏洛莱牛,为中法友谊作出的贡献与付出的代价,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领悟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