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荣尧:替古老的涛声召唤聆听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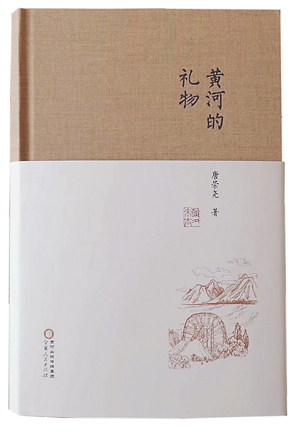
《黄河的礼物》 唐荣尧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23年8月出版
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与“摇篮”、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乳汁”等赞誉,让黄河在中国人心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席位。万里大河两岸滋育的黄河文化,无疑是中华五千年文明长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大禹治水的民间传说到时下的诸多文艺作品,中国人一直存续着讲述黄河故事的传统,以文学创作讲述“黄河故事”更是这种文脉流传的重要赓续。
黄河,一直是中国文学创作鲜活的文学母题,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富矿。
1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20多年时间里,我的职业是一名记者,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和中国新闻都带着理想蓬勃生长的时代,大批沉思式的、带着积极心态的批判性新闻稿件问世,可以说是衡量一张报纸或一个记者良知与勇气的标准。我在一次次的采访中,见证了黄河的“病痛期”:彼时,全球变暖带来的青藏高原的雪线上升导致源头水量减少,河源地带出现沙漠;大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埋伏”在腾格里沙漠的造纸企业往黄河里直接排污、宁蒙交界处重污染企业区内森林般的烟囱排出的工业酸雾落在河面上,滨河大道上疾驶而过的汽车和大桥上轰鸣而过的列车声,惊扰着水边栖居动物的休眠,巡扫在河面上的一束束光、喷洒在庄稼和蔬菜、果树上的农药,等等,带来的噪声污染、光污染和环境污染成了河流的杀手,让我像一个能诊断出病情却开不出药方的医生。
我出生在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从离开家乡去黄河边的县城读书,从在黄河穿城而过的兰州读大学到寓居银川23年,我完全是一个黄河的儿子娃。水光波影如镜,照见时光的指缝间渗漏的水声草音透过耳膜,把一个荡舟河上的少年,变成了河阔云低里听取雁声一片的中年。
不是每个人都能出生在河流边的村子或城市,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长期生活在一条大河边。我幸运的是出生在这样气势伟岸的大河边,也幸运地从未走出它慈悲的注视与深情的召唤。
河流是一本在大地上打开的书,有人从中看到的是曲线,有人看到的是恩赐,也有人会从中看出它的抱负,河边出生且在河边生活的人,无疑是幸福的,能够为河流写出一本书,是一个作家的勇气,也是福气。
2
黄河流出黑山峡后,在腾格里沙漠南缘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这是它和沙漠第一次相遇,随即和宁夏平原相遇,像一位书法家毫不节制地甩出一道大写意,在贺兰山、阴山和横山之间画出了一个巨大的“几”字型。
河流是自私与平庸的天敌,黄河既无私地赐给这片土地“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荣誉及与之匹应的物产,也像一位拒绝平庸的画家,开始向高纬度地区努力“爬升”,在和山峦、沙漠、湿地的相遇中,塑造出了渠、湾、湖、淖等水的子语,绘制出了一幅“新天府”的烟火画卷。当然,黄河也在接受着人类对它的新型介入与反塑造:拦河大坝、滴灌工程、滨河公路、城乡排水、跨河大桥、修筑河堤、光照辐射、河底隧道等科技时代的各种工程,就像一支如椽大笔,在黄河这部古老的书稿上,不停地书写、涂改、修订,甚至将不合自身所在时代要求的内容加以删改,试图将新的内容填写进去。
河流不仅穿过大地,滋润着沿岸的庄稼与人心,还流过空间,为人类留下一部文明诗卷。秦汉时期对宁夏平原的征服以及设立郡县,改变了此前“圣人疆理之制,固不在荒远矣”的局面,也使这片土地从此走进中原王朝的文明体系中,使这里及其北部、西部众多游牧部族掌控地区结束了“荒远”的地理角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黄河流经两岸的香山、照壁山、贺兰山、马鞍山、桌子山地区时,那些在山里放牧的先民以岩石为纸、尖石为笔,将自己的想象和生活凿刻在石头上,让黄河在淌过宁夏平原时听到了动物以另一种方式在石头里永生的声音;岩画最早的主人掌握了当时先进的造车技术,逐渐成为先秦最大的边患,给后者倒逼出了一道军事建筑:长城!一千多年后,动不动就将黄河当镜子来照照自己勇猛模样的瓦剌、鞑靼等蒙元残余势力,也逼得大明王朝的万千驻军在黄河两岸构筑长城,留下一脸的羞愧之色与被动应对;匈奴、突厥、铁勒、珲部、吐蕃、回纥、党项、蒙古等游牧部族的铁骑,穿过黄河的嗓道,吼出了这片土地的硬朗与底气。大河上最后一次飘过筏子客的“花儿”时,筏影成了水中的绝唱,两岸群山竖起的双耳,“大河唱”里翻滚着火车、汽车的轰鸣与工厂的呼吸。
黄河在万里流程中,不仅以“万物生”滋养两岸不同时期的生民,在他们中间还滋育出了历史故事、民间传奇、野史艳史,尽管更多的文字之外、“正史”之外的各种文明痕迹随着涛声,或积淀于历史深处,或烟云般飘散而远,一部真正能书写其辉煌和真实的书籍,就是一次打捞历史的救场。
黄河,一直在呼唤着这样的书。生活在大河边的作家,有什么理由不遍览藏着大河气息的群书?不聆听那古老的涛声发出的召唤?不探测那流淌万年的浪花里翻滚的文明温度?以脚进、身进、心进和情进的状态,进入大河的怀抱,既在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也注重反映时代风貌;既书写千年文明中的人文历史,也注重生态文学对“讲述黄河故事”的要求;既凸显非虚构文学创作的真实和权威,也遵循文艺创作的审美规律,让想象的马蹄声响彻河面;既有与黄河匹应的宏大叙事、历史叙事的视角,也有文学自身要求的日常叙事、当下叙事的细节。
3
峡谷,呈现的不仅是一种地理单元,还有独特的花事、物产与民俗,有搁置的历史的争议;“阿尔泰郭勒”的拇指,摁下成吉思汗生命临终前期的按钮时,黄河成了这位伟人生命中遇到的最后一条河;渡口,一旦失去功效,就变成了河流的墓碑;陇山腹地和鄂尔多斯高原腹地流来的三条支流,是三条奔赴黄河的岔路,清水河是其中最敞亮的、人流与车辆最多的一条;绛红色的涛声,则是铺设在黄河边的一条看不见的和平与安详之道;现代滴灌技术驯服了黄河水,让后者跳起几百米高后,钻进输水管道、渠道,在几百里外的高地上驯服了黄土旱塬,让百万移民有了新的家园;河流不仅能为城市提供用水、吸纳城市排水,更能滋润城市的性格,河流在滋育乡村风情的同时,也塑造出城市的面貌与性格。上述这些,是如魔术箱般的这本书的道具。
我无法确定对河流与土地相遇的一方土地的最好书写是怎样的,但我知道沉闷的历史文献堆积、规范的学术著作或夹杂个人小情怀的游记绝对是不理想的。大山河与大题材需要大视野,对一条大河丰沛的人文资源,真正在历史地理视野下书写河流的作品,应该是将文学、地学、史学、经学、民俗、宗教、人文等融为一体的综合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抒情散文或时下流行的“非虚构”,是跳出单纯的地貌解读、导游词式的风俗描述和对地理环境进行机械解说的;也应摆脱将某一地区或地理单元范围内的历史按时间顺序进行简单排列的所谓某某地区通史、简史的窠臼;更应排除将人文地理粗暴地理解为“某一地区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地理地貌”的做法。真正书写黄河的作品,应该是站在自然环境和地理风貌的基础上,以某一地理单元为载体的自然生态环境演变、文化地理演变、重大历史事件、社会或行政地理更迭、人与空间的关系(地理环境下的战争、开发、利益驱动下的较量、人类对环境的干预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立体、多元地挖掘、展现出来的作品,是敬献给黄河的一份礼物。
完成这样的书写黄河后,方能告慰自己:这万里大河中一段,我真正地爱过、走过、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