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戏走进上海话剧史 ——读《上海都市与文明戏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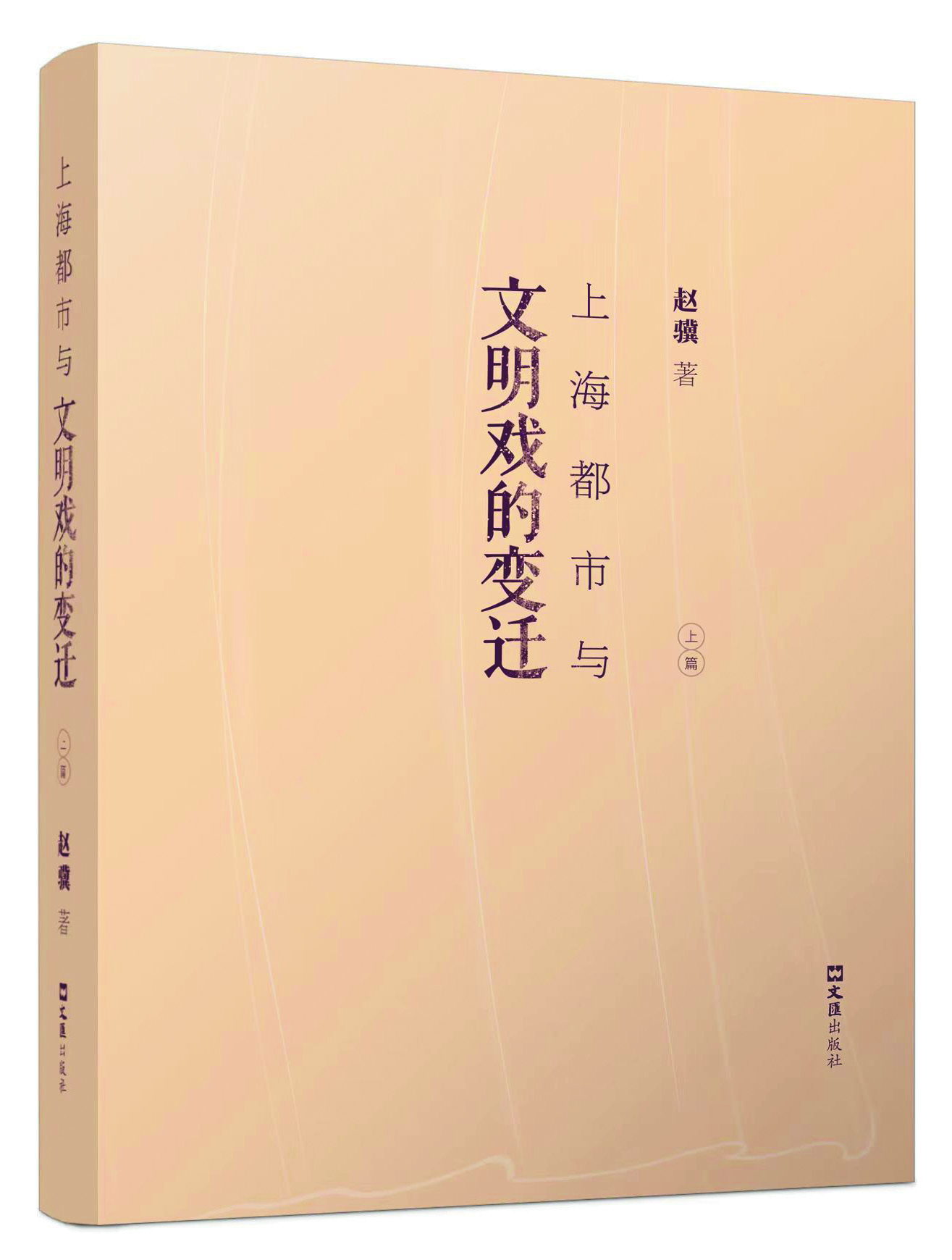
《上海都市与文明戏的变迁》,赵骥著,文汇出版社2021年出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热演的“文明戏”因为从欧美输入,在演剧观念与形态上与旧剧不同,起初还被视为“进步的新的戏剧”(欧阳予倩)。后来,“文明戏”却成为了对“新剧”颇具贬义色彩的称呼。文明戏被话剧史学家和研究者诟病,主要是因为其曾在商业资本驱使下畸形发展,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将粗制滥造的演出呈现在舞台上,最终“极剧而盛,急速而衰”(田本相)。2021年,赵骥的《上海都市与文明戏的变迁》(上、下册)由文汇出版社出版。该著上册以论为主,下册附有上海话剧演出史部分史料长编,结合上海商品经济和多元文化混杂的城市氛围,多方位细致描摹了文明戏的演剧活动,恢宏展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明戏发展史。
作者首先从“中国话剧起源之争出发”,重新审视“文明戏”在话剧发生阶段的意义。关于中国话剧的起源问题,向来是话剧研究者争议的热点,较为集中的一次讨论可参见傅谨、袁国兴编的《新潮演剧与新剧的发生》(2015年)。在话剧史的著述当中,通常将春柳社看作中国话剧的开端,或者中国话剧成熟的标志。另有不少学者对“话剧始于春柳社”(1907年)的说法产生疑问,将中国话剧的起点提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生演剧。赵骥认为,将春柳社曾孝谷改编的《黑奴吁天录》当作中国第一个话剧剧本缺乏文献依据,其演出形式也并非全是对白而是保留了唱腔,春柳社在日本的演出是上海学生演剧形式在留日学生中的延续,“上海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话剧的发源地,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源于上海的学生演剧”。但与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同,在他看来,是否可以将圣约翰教会学校的学生演剧作为话剧的开端还有待商榷。他依据鸿年的《二十年来新剧变迁史》、朱双云的《三十年前之学生演剧》等文章,提出“南洋公学的学生演剧,开启了中国新式学校的学生以中文演剧之先河”。近些年关于中国话剧起源的论争,既深化了上海学生演剧的研究,又重新评价了文明戏的历史意义,将新潮演剧推向了更开阔多元的研究视野。究竟如何定义中国话剧的“开端”“诞生”“发生”或是“起源”?依托于史料的新发现,也体现出话剧史研究者戏剧观念的差异性。
在文明戏发展史上,有的剧团不过是昙花一现,但也有一些剧团延续时间长、影响力极大,成为见证上海都市变迁的缩影。难能可贵的是,赵骥没有局限于剧团来龙去脉的简单介绍,而是基于扎实的文献资料基础,对新民社、民鸣社、启民社、移风社、民兴社等剧团,以及笑舞台、大世界、绿宝剧场、红宝剧场等演艺空间的跨时代、跨地域、跨社团流动现象进行翔实的爬梳整理,高度还原了上海早期演剧活动现场。这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人员的流动。朱双云、郑正秋、张石川、顾无为、汪优游等担任管理者、编剧、演员、剧评家的新剧人,乃是作者论述的焦点。他们在不同的剧团间辗转,延续了特殊历史时代当中文明戏的生命力。比如曾任民鸣社编演部主任的顾无为,早年因反对洪宪帝制、上演新剧《皇帝梦》遭遇逮捕,直到释放后重返民鸣社,才一改辍演的局面,使得民鸣社再度恢复演剧活动。后来,顾无为在后期文明戏时代又创办了导社,流转于多个地域之间,在上海完成了重要的发展阶段,期间努力践行“真性情”“真学诚”和“真艺术”的创社理念,在话剧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外,剧评的价值得到重视。在没有任何影像视频资料的基础上,对文明戏的研究是相当困难的。不过,通过马二先生、丁悚、钝根、玉儿、觉迷、病夫等剧评人对人物、情节、场面、表演、舞美、观众等多方面的立体化评介,呈现了文明戏演出的诸多细枝末节,也表达了新剧人的评剧观念和态度,值得研究者重视。作者从复杂交错的细节着眼,重视历史发展的过程,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和事件穿针引线般地生动解释了文明戏在上海早期话剧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如上所述,该著的亮点还在于展现了上海演艺空间当中丰富的文明戏演剧活动史料。除了对笑舞台、大世界演剧活动的呈现外,赵骥还特别提到了绿宝剧场。绿宝剧场是活跃在上海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中期的重要演出场所。但与上海剧艺社的话剧史地位相比,绿宝剧场显然少有涉及。当然,剧团剧社研究已日渐成熟,但演艺空间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赵骥重点考察了绿宝剧场诞生的历史背景、剧场空间设计、内部的组织架构、前后期发展脉络、演出剧目等,且在全书附录中附上了《绿宝剧场开幕纪念特刊》,并在下册罗列了绿宝剧场的演出剧目表和说明书,为全面了解绿宝剧场提供了依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见,作者没有止步于20世纪20年代,而是将文明戏的历史延伸至上世纪三四十甚至是五六十年代。他认为,上海滑稽戏、通俗话剧在演出内容和形式上都与文明戏有较深的渊源。比如文明戏的滑稽角色成为上海滑稽剧的滥觞,笑舞台等上海游艺场演出通俗话剧保留了文明戏的演剧形式等。作者在第五章“新剧在上海的余绪”当中,结合新剧家的论述,也展现了“文明戏”“滑稽文明戏”“通俗新剧”等名称的变更史。
新剧家徐半梅说过:“上海一处,不但爱好戏剧的人较多,并且是个通商口岸,与各国人士的接触亦繁,于是这话剧的种子,当然落在上海的土地上了。”赵骥的立论基础正是徐半梅的后半句,也就是从上海的本土性出发,将舶来的话剧种子怎样在上海生根发芽、壮大延伸作为论述的视点。在此基础上,他也试图在上海话剧史的版图上重绘文明戏的图像,进而从边缘出发,为文明戏正名,让我们看到了上海话剧的另一个侧影。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