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 ——评吴洲星的《碗灯》和“水巷人家”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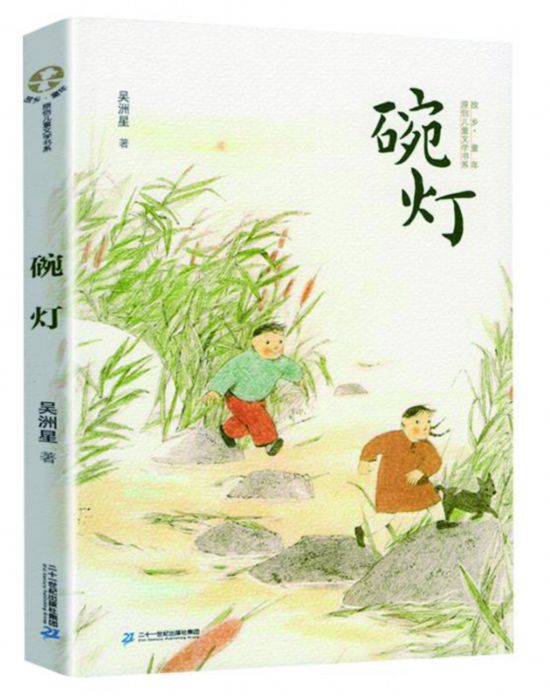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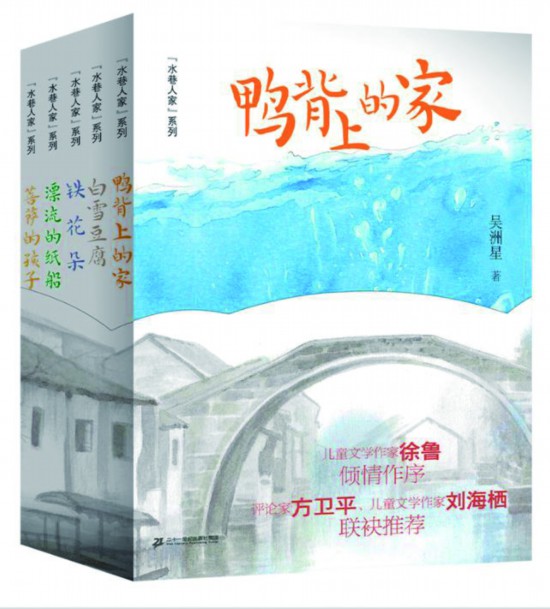
自吴洲星大学毕业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到现在,11年时间出版了三十余种作品,其中差不多一半是长篇,这样的数量十分了得。
作家有不同类型,但概而言之无非是两类,一类作家只写自己熟悉的、与自己心性相近的故事,另一类作家却不仅限于此。借用戏剧术语,即分为“本色”和“性格”两类。“本色”和“性格”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本色演员和性格演员都可以产生经典作品,作家也一样。我乐意用“性格作家”或“职业作家”来定义吴洲星。她虽然年轻,但已称得上是一位视写作为事业的执著的写作人了。
吴洲星此次推出的《碗灯》和“水巷人家”系列五册,故事发生的背景都在江南水巷。时间上,《碗灯》讲述的是民国故事,“水巷人家”系列则相对比较模糊,总的来说,都可以“过去的”江南水巷故事称之。《碗灯》里的小碗、灯儿,《白雪豆腐》里的小龄、《菩萨的孩子》里的宝寿、《鸭背上的家》里的草生、《漂流的纸船》里的小满、《铁花朵》里的铛子,都是过去年代江南水巷再寻常不过的人物。乞讨、挨饿、学戏、念书、与流浪狗相伴、狂庙会、做豆腐、卖豆腐、养鸭、放鸭、游泳、摇船、瞎子算命、拜菩萨,去铁匠铺学徒、把无力抚养的孩子送往尼姑庵等等,都是过去年代江南水巷随处可见的寻常故事。唯其寻常,唯其普通,所以可信。在这些寻常故事里,我们又总能看到小主人公们面对磨难、坎坷、困境时的勇气和担当。
而这中间,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散溢在字里行间的人间温暖,有小伙伴之间的彼此温暖、亲人之间的彼此温暖,还有非族类非血缘两代人之间的彼此温暖。点点滴滴,隐隐显显,无处不在。这种温暖是普通人生存和生活下去的信心、动力和希望。
为了孩子的未来,瞎子爸爸下决心将小满送到周老师家寄养。“小满一听,一下子就哭了:‘爸爸,你不要我了?’瞎子脸上笑着,心里却一阵阵发疼,说:‘爸爸怎么可能不要阿满?只是爸爸老了,不能再照顾你了。’‘那我照顾爸爸。’小满眼泪汪汪地说。‘阿满要上学,要去念书,’瞎子摸摸小满的头,‘阿满,你不想上学吗?’小满不作声了。”第二天,瞎子外出算命,忽然听到有人叫爸爸。“小满‘啪嗒啪嗒’地跑过来,她跑得很急,天一亮她就跑回水巷来了。她回来的时候瞎子已经出门了,小满就一直等着,等了一天好不容易才等来了瞎子。‘阿满……’瞎子的声音有抑制不住的激动。‘爸爸爸爸……’小满扑到瞎子的怀里。‘爸爸,我好想你。’小满声音哽咽地说。‘爸爸也想阿满。’瞎子说。”瞎子爸爸再次把女儿小满送回到周老师家,从此便消失了踪影,整个水巷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父女情深,感天动地。这是《漂流的纸船》(“水巷人家”之一)中的寻常故事。
流浪儿哑巴小碗被独居剃头匠老秦收留领养,两个孤独的人走到了一起,彼此关心,彼此帮助,彼此抚慰,让昏暗困苦的生活有了一抹亮色。小碗在老秦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学会了剃头,学会了生计,学会了感恩。老秦病后初愈想洗个热水澡,小碗烧好热水,为老秦剃头、浇水、搓背。老秦好不享受,不由想到自己小时候给父亲洗澡挠背的情景。小碗换上了第三桶热水,轻轻地推了推老秦。“‘小碗,你要跟我说什么?’‘嗯……’一个小小的手指头在他的背上游下来。‘这是什么挠法?’老秦觉得有点痒,咯咯笑起来。手指头继续在背上游走。‘哟,你这是在我的背上写字呀?’老秦明白过来了,笑起来,‘今天学堂里学了什么字呀?’小手在老秦的背上继续画,似乎一直在重复着两个单调的笔画。‘你这写的是同一个字吧?’老秦也感觉出来了。小手固执又单调地在老秦的背上画同样一个字。一撇,竖弯钩。老秦摊开掌心,也写起来。一撇,竖弯钩。写完,老秦的手指头悬在了那里。‘小碗,’老秦顿一顿,‘你莫不是……你刚才在喊我?’老秦屏住了呼吸,听到背后传来一个声音,声音小小的,有些害羞:‘嗯——’老秦终于明白过来了,原来小碗一直在喊他,可他没听懂,小碗就在他的背上写了这么个字。老秦的眼睛湿润了。”整个故事直至最后,也始终没有说出“爸爸”两个字,但这两个字谁都知道。没有血缘关系的小碗和老秦,不是父子,胜似父子,这是《碗灯》中的寻常故事。
人间温暖是“水巷人家”系列的底色。
吴洲星的作品很少有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又总能引导、把握读者的阅读,她比较注重人物的性格发展、故事的逻辑和细节的把握处理,这恰是小说写作者最不可忽略的基本功。吴洲星的小说创作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就是写人物及其性格发展。这使得她的创作与不少只关注故事、不关注人物性格发展的同龄作者拉开了距离。《碗灯》中写了小碗、灯儿、老秦、慧心等人物,小碗和灯儿是流浪儿,老秦是独居剃头匠,慧心是滴水庵的尼姑。作品中的小碗和老秦、灯儿和尼姑分别走到了一起,而小碗、老秦和灯儿、慧心之间又彼此有了来往和交集。从本质上说,这四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是孤独孤寂的,都是缺乏抚慰关爱的个体存在,都是社会底层的讨生活者。当孤独孤寂的人遇到同类,他们的内心世界会产生怎样的变化?这样的设定为人物的性格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探求、刻画和塑造的空间。
故事的逻辑就是故事的合理性。对读者而言,故事合不合理,意味着故事是否真实可信,是否符合特定空间里“就该如此”的艺术设定。前面提到的《漂流的纸船》中,瞎子爸爸与女儿小满的别离故事之所以触动人,就在于这个故事有合理性,符合逻辑。瞎子爸爸再次送女儿小满回周老师家后不辞而别,这样做是因为自己是瞎子,年老体弱,没有文化,无法为女儿提供一个丰衣足食、接受良好教育的美好未来。尽管万分不舍,但又只能如此。而自己所没有的,周老师都能提供。周老师有文化有知识,膝下无儿无女,视小满如己出,很乐意领养、培养可爱懂事的小满。对于小满,她不知晓爸爸的真实想法和动机,只知道周老师夫妇对她很好,但那是老师的好。她当然不能没有爸爸,所以才从周老师家跑出来寻找自己的爸爸。这里的情感冲突和高潮点在于,小满不知道这是自己与爸爸的最后见面,而爸爸则知道这是自己与女儿最后的见面,可自己偏偏又不能把这一切告诉女儿。在知情与不知情、隐忍与呼号之间,父女情深久久弥漫。
细节的挑选及精准把握,从来都是衡量作品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吴洲星作品中的很多细节都可圈可点,前面提到的《碗灯》中,小碗帮老秦洗热水澡,又在老秦背上写字这个细节,就让人过目不忘。由于自己是哑巴,他无法用自己的嘴说出“爸爸”这两个字,只能在老秦的背上反复写两个字。老秦说,小碗帮他挠背让他想起了小时候自己帮父亲挠背,小碗只是用“嗯”来回应他。小碗轻轻推了推老秦,老秦问小碗想说什么,他感觉到小碗在自己背上不停地写着相同笔画的字,问小碗是不是在喊自己,他说再喊一声、再大声点,无论怎么说,小碗都反复用“嗯”的一声来作回答,坚定而意味深长。那一刻,老秦的心里“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铁花朵》(“水巷人家”之一)中,铛子给铁匠师父当学徒,一开始感觉很新鲜好玩,后来才知道这活计太累太苦,打铁铺一天到晚炉子都是旺的,待的时间长了,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镐头钝了,加热后抻长一些,叫“拍”;拿钢片贴在镬头面上,烧成熟火后趋热捶打黏合,叫“钢”;锄头磨薄了,将钢片烧得蜡样几近熔化,趋热涂抹在同样红热的锄面上增加厚度,叫“渗”。学会这些以后,铛子以为自己能打铁了,师父却让他先学拉风箱。师父说:“不是让你学拉风箱,是让你掌握火候。什么时候打热铁,什么时候打红铁,都讲究个火候。火候掌握好了,能把两块铁板粘贴得天衣无缝;掌握不了,铁板虽然粘上了,可终是两张皮。”铛子这才知道打铁有打熟铁和打红铁之分。有趣的是,师父有时还一边打铁,一边唱《十女夸夫》:“世上不如打铁汉,钳子锤子来抖威。先打大姐锛刨与斧锯,后打二姐凿子锤……”这是一个铁匠铺学徒眼中的打铁情景,又何尝不是底层民众在艰难困苦环境下的职业操守、自我约束和乐观面对世界的人生态度,同样是细节的力量。
吴洲星的写作正在路上,路虽漫长,但天地宽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