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埃克苏佩里的星辰与玫瑰 “中间时代”的高空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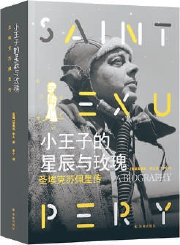
2002年,我买到了一本中英法三种语言合一刊印的《小王子》,是其问世60周年的纪念版。让一个中二时期的文学少女阅读“童话”是灾难性的,童真世界的大门在被我拼命闭合,又尚不懂何为豪华落尽见真淳。那时我倒像炫技一样记住了“圣埃克苏佩里”这个长长的名字,并在地理课上以同样的目的记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2012年《小王子》问世70周年时,我凑巧经由法国飞赴拉美,忙着品尝马卡龙和计算里程积分,却从未想过为何要坐法航飞机、经由巴黎——而法航与《小王子》和拉美的关联,圣埃克苏佩里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关联,是将近又一个10年之后,在这本圣埃克苏佩里的传记中,我才找到了答案。
“小王子”不是他的全部
如果按照“《小王子》诞生记”的预期来阅读本书,起初无疑将是失望的:算上序言和后记,本书共有20个章节,而专门讲述《小王子》成书过程的内容迟至第16章方才出现;只知道和关注“小王子”,显现了如我一般的普通读者的、可能也是文学史书写的某种偏狭。
圣埃克苏佩里的重要作品远不止《小王子》,但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又处处都是《小王子》的成书过程:在飞行中对责任、仁爱、友谊等崇高母题的探索,在人生中对孤独和“随时追忆童年”的体悟,在写作中对星球等意象和寓言般的叙事方式的熟稔,加之与其合作的美国出版商成功的童书出版经验等等,使得《小王子》在1942年水到渠成、应运而生。
阅读预期的误差也许还源于本书的命名。它的英文原名朴实至极:“圣埃克苏佩里传”;而中文版则又加上了“小王子的星辰与玫瑰”。我能理解译者与出版方的用心,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小王子”(顶多加上“飞行员”)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唯一标签;而本书着力于对传主(或“小王子”)所珍视的、所困惑的种种事物的探求,用“星辰”“玫瑰”这两个意象来代表内容,也比较准确。
作者通过大量的研读与调研走访,为我们详尽展示了圣埃克苏佩里作为“航空游吟诗人”的一生。斯泰西·希夫,这位普利策奖得主以新闻报道般的严谨和热忱为我们还原着历史,对于传主其人和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在占有大量当时的和后来的资料之上,有着极为理性深刻的剖析。对于一个有持续影响的事件,往往又以“当时他不知道”“很多年以后”这样明晰有趣的后设来进行交代。可以说,斯泰西·希夫用魔幻现实主义笔法与“纪事本末”,在大的年代顺序框架下拿捏着非虚构书写的时间节奏。
对人物的刻画、关键事件的还原和作品与评论的分析细致而扼要,使得本书不仅是一本传记,也是一部集大成的圣埃克苏佩里作家作品评论资料;以圣埃克苏佩里身份的特殊,以及作者的更为宏大的思考与功夫了得的笔力,本书亦可看成一部探究20世纪初中叶法国文学史、航空史乃至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民族精神的著作。
在贵族与工装之间
圣埃克苏佩里出生在1900年,本书却以1927—1928年他在摩洛哥朱比角担任航空公司中途站站长的经历开篇,取名“无垠高空之王”。在这里,他8岁时即被莱特兄弟点燃的对飞行的向往,由母亲和圣让庄园精心培育的文学热情,被分离的寂寞与孤独放大的随时能回到童年的天分,摩尔人、黑奴、相爱相杀的西班牙人与法国人,以及沙漠中的动植物构成的世界,为飞行员和后来的“小王子”提供了星辰、玫瑰、沙漠等重要意象,也开始真正领悟了友谊和责任的重要。
在朱比角同时承当飞行员、大使、探险家的身份——相当于二十世纪的“游吟诗人、十字军战士和游侠骑士”,是圣埃克苏佩里一生经历的注脚。希夫敏锐地抓住了他身上的两重属性:一是“矛盾”,二是他生长的土壤——一个“中间时代”的法国和世界。
圣埃克苏佩里身上的矛盾性,与性格及成长环境紧密相关。他是来自外省、家道中落的“赤贫贵族”,曾试图以“啃老”拥抱上流社会,可一无所有的他又对由财富和头衔构成的社会产生怀疑。他日后反思“咖啡馆里的社会什么都没教给我”,直到辗转成为运送邮件的民用航空飞行员。他细腻敏感,又控制欲强。他时而成熟懂事,时而又任性得像个孩子,把错误归给别人。正如他所生长的法兰西,在美国作者的犀利笔触下,我们发现,这个国家一方面以《马赛曲》和大革命著称,另一方面又常常陷入分歧、内斗、以思考为名的观望,直接导致了它在二战中的分裂与耻辱,并使流亡美国的圣埃克苏佩里腹背受敌。
书中用“中间时代”这个词,概括了圣埃克苏佩里所生长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从旧的君主制度到新的共和制度之间、从贵族式生活到新社会分工的时代。他所生长的法国,人们尚未被大工业时代和现代信息技术裹挟,仍保留着高贵的文学传统,并保有写信的习惯;飞行——尤其是得以穿梭于作为“异邦”想象的北非及拉美——尚是少数人的特权,这也是航空邮政得以繁荣、以及这位作家飞行员(或曰飞行员作家)得以受到注目的基础之一。亲历法国航空业的由盛转衰,给圣埃克苏佩里的个人记忆、集体情感乃至民族感情留下了许多伤痕。
因为开飞机和研究机械,圣埃克苏佩里这个“穿着工装的贵族”敏锐地发现了未来世界的动向——技术会越发先进,心灵会越发荒芜。他还从德、美在航空领域的领先,预感到法国在不可避免的战争中的处境:要被德国人打败,需要美国人支援。可如此富有预见性的他,却渐渐地活在过去,复述从前。他对世界和国家局势有如此深刻的洞见,却在人人需要“站队”、表态的战争年代孩童般地坚持中立;但这个以珍视全人类文明为名的“中立者”,却又不顾超龄、多病的风险,两度奔赴前线,是二战期间法国为数不多的直接参战的作家之一,直至葬身云端,至今无寻……
在作家与飞行员之间
令人惊讶的是,圣埃克苏佩里几乎全程参与了巴尔扎克之后20世纪法国文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自1926年被冠以“一位航空和机械方面的专家”的身份(其实远远不是)发表《飞行员》以来,他逐渐跻身“奥登河畔斯特拉特福”文学圈,与海明威、乔伊斯、艾略特、菲茨杰拉德、纪德、吉尔伯特等闪耀的名字交汇、并列,将文学成就的荣光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法国和美国都获过重要的文学大奖,每本书都有相当可观的销量和讨论。可不论是当时的在场者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还是多年后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我们都很难从对文学黄金时代的追忆谱系中找到圣埃克苏佩里的名字。甚至他和纪德一样去过苏联,和海明威一样去过西班牙内战前线,但一提起同时代作家们的相关行动与文字,文学史也习惯性地忽略了他。
我想这一部分源于圣埃克苏佩里世界观与思想的特立独行:去苏联,他的着眼点都在波兰工人以及滞留在苏联的法国家庭教师等“个人”;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边境线上,他最留意的则是两派士兵作为同胞在战壕里互道晚安……而这种特立独行,则源于他的高空视角,他是在飞行的宇宙中、在朱比角的大漠里慈悲地看待地球和人类,而这也直接导致了他在战时话语中的格格不入——他不愿站队于哪种主义、哪个派别、哪位领袖,在意祖国命运的同时,他认为战争毁灭着整个人类的文明。数次出现的不合时宜、因言获罪让他在生前身后不断被误解和诟病,以及身在美国语言不通的苦闷等等,也在一次次中伤或寂寞中逐渐将他推向“小王子”的世界。也许人类的悲欢有时相通,差不多同一时期,身体、思想及情感都饱负伤痕的东北流亡作家萧红,来到了香港这块战争“飞地”,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公主”的“星球”,那便是《呼兰河传》中的“祖父的花园”。
成名后的圣埃克苏佩里的身份也是“中间”式的,这构成了对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某种冒犯:在一些专业作家和评论家眼中,他仅是一名飞行员,顶多算是本雅明定义的、传统的依靠自身经验来讲故事的“水手”式的人;可偏巧这飞行员竟然深爱波德莱尔,不仅有托马斯·曼所说的“现实”,而且熟谙叙事技巧的“魔法”。于是,连飞行员夜航中靠星星定位、寻找“星球”的意象都被苛责为“做作”,这种敌意一直延续到他死后多年,《小王子》却一路畅销,以至于评论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篇“童话”。
与此同时,靠书写飞行经历和书写同事的历险来写作、出名、获奖,也使得圣埃克苏佩里在飞行员间一度众叛亲离。这种痛苦起码延续到了他因为爱情决定离开空中邮政队伍,而与飞行员们共担使命责任、历经生死考验的情谊,则成为他一生珍视的星辰。但这份荣耀和使命感却随着盛极一时的空中邮政公司被污蔑被瓦解收归国有,随着法国航空逐渐衰落,随着圣埃克苏佩里的年龄渐长、疾病缠身,随着最好战友或因疾病或因战争的相继离世,也随着他与“玫瑰”——妻子龚苏罗渐行渐远心力交瘁,而被一次次地狠狠摔打在地。
1959年,在圣埃克苏佩里确认死亡15年后,时任法国元首、曾被圣埃克苏佩里批评为“机会主义者”而拒绝合作的戴高乐曾不无遗憾地表示,1943年他(当时已经夺权得势)一度拒绝飞行员与之见面的请求,是出于男人和领袖的无奈;但其实天真如圣埃克苏佩里都已明晓“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的危险气息。我们的飞行员显然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飞行、战斗乃至战死成了他更强烈的意愿与实践。而至少从1942年开始,圣埃克苏佩里就开始了与亲人朋友的“漫长的告别”。源于贵族血统加现代飞行员的根深蒂固的责任感,以及小王子般不切实际的纯真和一种近似于“必也正名乎”的决心,造就了圣埃克苏佩里的最终选择与命运。在诸多“中间”的意义层面之上,也许我们才能更好地解读“小王子”和他的“星辰与玫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