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兵过》:记录东北乡村的百年沧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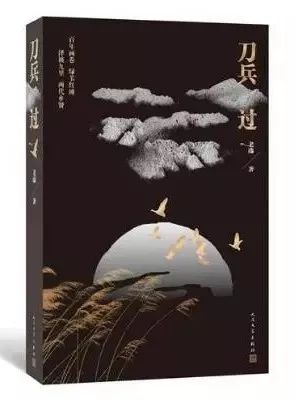
《刀兵过》

俞胜(中国作家编辑部主任 责编):
老藤的长篇小说《刀兵过》从清朝末年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之后,小说以王克笙、王明鹤父子谋求恢复祖姓为经线,以清末、民国、伪满等不同历史时期一次次的过刀兵为纬线,编织出一幅20世纪中国乡村波谲云诡的历史变迁图。小说不仅记录了东北乡村的百年沧桑, 也是一部记录乡村人物家族史和心灵史的力作。
王家原本姓“朱”,世代从医,因祖上曾被迫在大周朝任医官而埋下了灭族之患。为了使子嗣绵延,为了使家门免遭涂炭,只得骨肉分离,远走他乡,并易“朱”姓为“王”。当年,王克笙远走白山黑水间时,母亲曾叮嘱:“恢复祖姓,应当从长计议,大周非善朝, 朱家易姓也非光彩事,不到河清海晏之时,不可草率为之。”于是,寻求河清海晏之象就成为王氏父子矢志不渝的追求。清朝灭亡了,民国不见河清海晏,日伪时期更不见,国民党统治时期也不见……不但不见,且一次次的过刀兵让世外桃源般的九里弥漫起战争的硝烟,村民的日常生活遭到战争的蹂躏,人性也在战争的夹缝中被反复碾压、揉搓、重塑。
《刀兵过》中人物形象众多,两代乡贤王氏父子,韵致天成、道行高洁的道姑塔溪、止玉 ,面善心恶的黑木,狡诈、坚忍的“苇地之獾”尉黑子等等,这些人物形神兼备、惟妙惟肖,交织出一组异彩纷呈的人物群像。其中,王氏父子凭借自身的威望、品行、才学让九 里有了道德楷模和淳美乡风的引导者。在老先生王克笙、小先生王明鹤两代乡贤的规范和引导下,九里最终成为“世外桃源”,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福地、仁义之乡。村民人人知大义、识大体。小说为两代乡贤树碑立传,也呼应了当下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思潮。
作家老藤潜入民族精神的秘境,揭示宗教和信仰在民间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在九里,“三圣祠”无疑是村民们最重要的精神家园,是村民们的精神依归地。“智仁勇三德,儒释道一家”,因为共同的信仰,三圣祠也庇佑着九里免遭义和团乃至日军的蹂躏。三圣祠流贯在小说的始终,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文眼。“文革”期间,三圣祠被毁,王明鹤一下子颓废苍老了,甚至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而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三圣祠终于得以重建,也重建了小先生的精气神,让80多岁的老人“脚步稳健,腰背挺直,完全换了一个模样”。三圣祠的重建也让王明鹤老人感觉终于到了河清海晏之时,于是宣布恢复祖姓。作家老藤以一支游刃有余的笔,既高歌了我们今天的盛世,也潜行进民族精神的秘境中,点触民族精神和信仰的伟大。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这部作品的内容、故事、人物,总的看是写乡绅家族,写乡情人事,写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很丰富,其丰富性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比如关于儒家文明、乡土文明、儒释道,以及医和茶。医和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与儒释道又有内在的勾连,所以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把一个世家身上所凝聚的各种文化因素,写出了一种民族和民间精神的传承,以及这种精神传承对一方水土的滋养和支撑。王家两代人就是九里的支撑,没有他们,九里这个地方怎么生存、怎么发展都要大打问号,而有了这种滋养和支撑,尽管百年间过了多少次刀兵,但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活了下来。
作品确实写出了中国文化很特别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以软对硬、以柔克刚。写乡贤写乡绅,能把作品写出这样丰厚的文化内涵,确实不多。作品通过这样一个角度解读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民间社会的很多奥秘,它有自己的小秩序——由乡贤和乡绅带来的秩序,这样的秩序有很强的转化能力,在不同的时代它都能转化成各种正面的和积极的能量。在写乡贤乡绅这样一些家族文化的作品中,这部小说是集大成者。
王家两代人是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性格魅力的。在作品的写法和叙述方面,老藤表现了一种非常充分的中和之美。非常内敛,非常节制,非常干净。所有的恋爱都是情和精神的交融,甚至太中和了太干净了——这既是作品的长处,可能也是作品的短处。生活还要有点杂质、杂音,要毛茸茸、湿漉漉的。
此外,老藤对传统的、民间的文化吃得很透,拿捏得非常准,非常少见。写具体的事和人时,有一条线是能看到的生活层面、现实层面,还有一条线是精神层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较量,都是精神在起作用,很厚重。
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
写乡村文化、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刀兵过》给人一种静水深流的感觉,特别扎实和蕴藉。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传统、人的活法、人与外来力量的相互拒斥过程,看完觉得中国文化的混沌气,知白守黑,以少胜多,都在里面了。
作品的核心,是表现两代堂主在九里这个地区肩负着文化的传承和维系。按中国的秩序和社会进化来讲,如果不受到外力的入侵,会有一种天然的秩序。但是,一方面外敌入侵了,民族对立,搏杀,较量;同时,另一种文化也在对这块土地、人心和秩序进行改造,这两种力量都在发挥着作用。
《刀兵过》对中国人的了解还是理想化的——中国人非常有智慧,非常蕴藉,讲礼仪,识大体,以理服人,不拼体力而拼智慧,不是蛮干的、不讲究策略,不是在外力下易屈服的。
此外,它还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印记的作品。显然老藤对中国文化有非常深的体悟和热爱,才能写出有这种气象的作品。在小说中,中医是两代人的职业,他们在疗救人的同时,也在疗救秩序、人心和国民性。
小说有完整的对乡村社会和自然的认识。比如写驴,除了刘亮程特别擅长,我看老藤是第二个。小说中出现了很多东北的器物,还写到了婚丧嫁娶时的讲究,这些都能够抵抗时间的冲刷。过一二百年再考察东北民俗,考察非物质文化的痕迹时,可以到《刀兵过》里去寻找。
小说里还能看出中国文化中个体和整体的关系,有很多让人联想的东西。人们对世上的事物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社会秩序是由领袖、特定的人来缔造和维护着;而中国文化讲究整体,三圣祠,酪奴堂,是个人代表群体的,议事时韩马姚姜陶一起来,代表金木水火土,回到了中国文化的解释上,非常有意思。陈忠实写《白鹿原》时,我认为他没有考虑这么全。老藤对东北传统文化的挖掘和认识非常深刻。
这部长篇小说的时间跨度非常大,因此很难避免气息缓慢和平均使力。但是到了王克笙,特别是在他结婚之后,读起来还是很享受的。关于长篇小说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爱情和性。《繁花》也好,《朝霞》也好,都是上海的作品,推动故事还是靠异性相吸的过程,或靠爱情故事,但《刀兵过》在这方面却有点意外,而且竟然能够进展到这种地步。
《刀兵过》写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跨度这么大,字数又不特别多,这种稳健特别令人肃然起敬,显然有很长时间的储备,它的不瘟不火和文化的气息需要深入的解读和了解,熟悉东北黑土地文化的人对它的了解会更深一些。另外,小说的写法上,一方面是想象力,另一方面还有地方性知识的考证和相互印证,这些都提供了有力的借鉴。老藤一定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他还有多种可能,希望在今后的创作中多写好作品。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刀兵过》是一个有思想有厚度的小说,读了很震惊。写历史,特别是近代百年来的革命史,有的是通过家族来反映百年的发展,有的是用革命传奇的方法,都是想以此来反映百年风云变化。这些小说一般在情节和故事上有所变化,但对历史的认知没有太大变化。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是能够对世界、对历史提出独到的看法,《刀兵过》就有这样的效果。《刀兵过》完全跳出了我们习惯的建立于暴力美学基础之上的历史观,去重新反思我们的历史,看到了暴力的革命性和破坏性在带来历史的进步,也带来了副作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也破坏了珍贵的东西。暴力革命的摧枯拉朽带来了社会的进步,这是从宏观而言,但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把我们传统的精神也伤害了。
《刀兵过》有很多寓意。主人公祖上姓朱,为避祸改姓王,因先人叮嘱“不到河清海晏之时,不可草率为之”,因此直到1981年才最终恢复了祖姓。这体现了老藤对历史、对中国革命和对改革开放的认识——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不再以暴力革命为基本路线思路。而1981年也是我们政治路线进行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从这个角度讲,小说的题目很有深意:“过刀兵”是带来祸患——我们一直在过刀兵,一直处于暴力革命中,一直停留在过刀兵的思想状态中,还用那种暴力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今天的事情。五六十年代为什么一直在折腾,就是在用过刀兵的思路来处理和平建设时期的事情,因此就有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这些都是对历史的反思。《刀兵过》中最体现中庸之美的,是三圣祠,是民间信仰,它代表了民间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理解,它强调了传统文化的作用,表达了对历史新的认识,作品的确提供了新的东西,这一点非常难得。我们的历史小说越来越多,但真正能够提供新的历史观的非常少。从“过刀兵”和“刀兵过”,评价历史抓住了关键点。
陈福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小说中的酪奴堂是有深刻的文化象征的,有隐喻性。中国近代百多年来,文化上就是酪奴,是处在低的位置上,一直被打。鲁迅说“一首诗吓不跑孙传芳,一声炮响就把孙传芳轰跑了”,鲁迅说得太明白了。
“五四”一代人或者说“五四”之前的仁人志士,把中国失败的原因找到了船坚炮利,后来发现不仅是船坚炮利,后来又找到文化上,这等于是此一时彼一时地翻烙饼,对文化传统和整个世界局面的理解,始终是在一个相对主义的层面上,偏一下,正一下。我觉得整个一百年来,中国人缺乏一个对整个世界的理解能力,要么就说洋人特别好,要么就说我们自己特别好。
我听前面几位老师的发言,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儒释道,包括乡村理想主义,理想国,乌托邦,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当然是同意的,但是我也有一个担忧:最后你何以对面世界?这还是一个问题。
酪奴堂深刻地隐喻了中国百多年来愈挫愈勇,靠植根于我们的文化,同时又善于向别人学习,才走到了今天这个局面。我觉得“酪奴”代表一个文化冲突,我们应该正视这样一个文化冲突,轻易地把票选在哪一边可能都不是一个正确的语态。当我们被别人打得特别惨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就愤发,然后又觉得道德沦丧,人欲横流,又觉得我们自己这一套好。我们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应该是趋于综合的,是需要有一个像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的螺旋式上升的态度,而不是偏执于一方。当年讲文化偏执论没办法,不偏执就没法冲破旧的文化,所以不得不偏执。但我们今天真的需要一种极端的偏执吗?我自己是没有把握的。但我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来。老藤在这部小说里塑造了典型的文化人物,一个几平方公里的圣土,在一个来势汹汹的世界性的大潮中(这个大潮也不仅仅是外来的,也包含着包括着我们自己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内部变化),这样一种文化理想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这都是需要考量的。老藤的小说给了我们特别好的考察这些问题的机会。而且老藤的进入,他对小说人物的塑造,他对中国乡村社会这样一个经济关系的想象和描述,在很深的程度上给我们提出了问题。
仓廪足终知礼节,不足怎么办?外部的秩序和礼仪的规驯就特别重要。九里是没有原住民的,都是流民,只有王克笙是有文化的,他的初民管理是带着文化记忆去重建(九里参与议事都是“元老院的贵族”,世袭制,非常像初民的治理),去诉诸于那几个家庭,如果没有一种理想化的建构和植入,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但是文学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个世界一如既往地贫困,无序,肮脏,混乱,残暴,而我们的文学也一如既往地去肮脏、残暴的话,我们还要文学干什么?所以,一定程度的理想化是应该被我们所原谅和接受的。
对于《刀兵过》的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各抒己见,但是有一点大家应该是认同的,就是它印证了老藤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文学能力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小说的语言,一般写到20万字就撑不住了,就开始粗针大线了,但这部小说,里面的文化含量,器物,规约的那种仪式,细节的考究,都是一个写作者超群的文学能力的表征,没有这种能力是达不到的。
翟永明(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
《刀把兵》不是一个外部的历史进程的描写,更多的是它超脱于历史和现实之外的一种精神的力量。人物身上带有儒家的仁、义、礼,比如发乎情止于礼,又包括了道家的文化。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建构一个是解构,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但在小说里同时出现了。他是怎么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我想是一个“善”字。
“善”在儒家里可能表现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孝悌忠信,那种对父母对兄弟对自然对鬼神对天地的良知,包括外在的笃定,刚毅,隐忍,坚忍不拔,在小说里都有很多表现,是儒家外向的善,对世间苦难产生了非常大的力量;而道家的善更多的是一种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大巧若拙,大悲若喜,大音稀声,大象无形,是这样一种特质,就像那两位道姑,那种世间罕见的纯净无邪,完全超越了俗世,而且对于世事是完全洞悉的,是一种内向的善。这个小说最好的点是能将这种外向的儒家的善与内向的道家的善结合,形成更完整的一个善的文本,传达出一种人性的美,甚至是一种带有神性的美。那种美好的感情确实不能逾轨,否则作品所构建出的那种很和谐的秩序或者美可能要被破坏掉。这种美还表现在那种外在的结构上,结构跨度这么大,作家绵绵不绝地控制得这么好,能协调起来,也是源于一种由善结合起来的美。
- 本文节选自: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刀兵过》研讨会专家发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