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评选结果揭晓 《冬虫夏草》获金收藏奖;林超民获终身成就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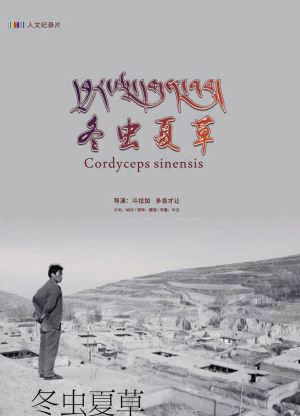
11月12日,“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志纪录片永久收藏奖”评选结果揭晓,斗拉加的入围作品《冬虫夏草》获得金收藏奖;林超民获得“中国民族志纪录片终身成就奖”。
在当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闭幕式暨颁奖仪式上,斗拉加的入围作品《冬虫夏草》获得金收藏奖,欧阳斌的入围作品《六搬村》,余海波、余天琦的入围作品《中国梵高》获得银收藏奖;郭净和此里卓玛的入围作品《卡瓦格博》、杨洋的入围作品《司公》,以及陈学礼的入围作品《照片里的她》获得铜收藏奖。中国民族博物馆还为42部入围作品颁发了永久收藏证书和永久收藏奖奖杯。
为尊重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中国节日志》知识产权,中国民族博物馆为9部入围“节日志”作品单设的“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奖”,授予了鬼叔中、朱靖江的作品《七圣庙》。
为推动中国民族志创作与影视人类学研究的长远发展而特设的“中国民族志纪录片终身成就奖”,授予了创办亚洲第一个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的著名学者林超民。早在20世纪末,林超民就凭借历史学家的敏锐眼光和远见卓识,率先在中国学术界推动了影视人类学学科建设,培养出了一批数字音像时代的民族志电影专业人才。
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由中国民族博物馆发起主办,以双年展的形式每两年举办一届,选取国内优秀民族志纪录片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致力于多角度记录我国各民族的真实生活样貌,深层次呈现我国各民族的文化遗存与历史变迁。
[评论]
民族志纪录片的社会责任与日常视角
——评斗拉加的《冬虫夏草》
□ 朱晶进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电视台导演斗拉加,通过为期3年的扎实拍摄,向影视圈和学术界贡献了一部民族地区现实主义题材的优秀作品《冬虫夏草》。该片以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还俗僧人宗智前往果洛州玛沁县采挖虫草为线索,使用自下而上的日常视角,揭示了虫草经济对当地社会各个群体的影响。它不仅是一部有学术档案价值的民族志,更是一部体现了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者电影”,足以引发观众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农牧经济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深思和讨论。
民族志纪录片的社会责任
斗拉加在7月的一次映后访谈中曾提到,他拍摄民族志纪录片,首先是社会责任,即如何用纪录片拍摄来体现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并希望引起观众特别是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关注。
在《冬虫夏草》中,导演以丰富的细节告诉我们:农牧民收入因虫草而迅速增加,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如何能跟上。虫草价格上涨后,一人采挖一斤虫草就能抵得上3年打工收入。农作物种植的成本以及与其他收入来源的巨大差距,是推动很多农区群众于春末夏初前往虫草产地采挖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每年虫草季来临之际,有的农户将原来饲养的奶牛、猪、鸡、鸭全部卖出;半农半牧地区则将牛羊交给他人代放,甚至有因为虫草收入较好而撂荒自家农田者。牧区部分草场主在收取数百万草皮费后一夜暴富。有的在县城买房保值,有的使孩子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很好地利用多余的收入。对此,《冬虫夏草》在客观纪录背后隐含了深深的担忧。导演斗拉加在映后访谈中提到,有草场主将草皮费竞相用于购买高档越野车,一掷千金,引发了当地的攀比之风。
《冬虫夏草》的社会责任感,还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上。该片的众多支线中,有一条呈现了草场主一家的生活。传统的游牧生活与农区的种植生活看似相隔遥远,却因为虫草而紧紧地连在一起。问题在于,牧场的泉水因为虫草采挖而干涸或遭污染,土地营养流失致使牧草生长不力,从而影响到了牛羊的出栏。牧民还担心外地采挖者给当地带来传染病。导演借虫草专家之口,从专业角度提出了虫草经济的可持续问题。
民族志纪录片的日常视角
作为贯穿现实主义拍摄手法的民族志纪录片,与讲述民族史、民族神话的影视片有所不同。史诗中的英雄和帝王将相指点江山,是民族影视片所长;农田、牧场和场镇中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则是民族志纪录片所长。与所记录对象交朋友,将照相机、摄像机、笔记本电脑所代表的权力分享给拍摄对象,才能深入到某一群体内部,深入到某一个人内心。这一点,既是社会学家、民族学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导则,又是民族志纪录片创作者通往优秀作品的必经之路。
《冬虫夏草》在90多分钟的时长内,成功涵盖了几乎所有与虫草经济有关的人群。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该片共涉及如下5类“虫草人”,青海民族地区的多样生活方式因此得到了丰富的展现:
一是采挖者。包括宗智、他的同乡以及其他自外地前往果洛采挖虫草的人员。我们也可以从宗智的个人理想和感情生活中窥见青海农区藏族群众的典型心态。
二是草场主一家。他们的传统游牧生活在该片中是牧歌式的,令人陶醉。而穿插其中的虫草采挖镜头,以无声的画面讲述了虫草经济对牧区的影响。
三是虫草商人。该片对这一群体的表现令人惊喜。导演通过深入西宁及果洛大武虫草市场,对从小到大不同交易类型、甚至包括交易中间人都予以展示,特别是对虫草交易中用手势谈价的风俗进行了特写和解释。数根数根的小本买卖与成箱成箱的大宗收购之间的对比,在用真实画面形成视觉冲击力的同时,也全面覆盖了具有复杂层级的虫草经济体系。
四是限采政策执行者。虫草采挖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零散——开放——限采”不同政策阶段。主人公宗智口中的“清山人员”就是当今限采政策的执行者,他们往往是当地多个部门联合组成的执法队,其目的是杜绝虫草乱采滥挖,实现这一资源可持续发展。作品通过视听语言告诉观众,由于果洛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这种执法工作亦并非易事。虫草利润实在太大,外地采挖者偶尔遇到的“清山”行动并不影响他们当年的总体收入。
五是果洛大武镇上的乞讨者。他们是虫草经济带来的社会后果之一。影片展现了对其中一个乞讨者家庭的采访过程;被访者也明白虫草比黄金更昂贵的价值,惋惜自己没有采挖能力,希望从这短时间内涌入果洛大武的几万人中分享到虫草带来的经济果实。
斗拉加谈到,他在《冬虫夏草》3年的拍摄历程之中,第一年并无计划,仍然按照“为解说词配画面”的电视专题片制作方式“乱拍、瞎拍”,但效果不佳。当第二个虫草季到来时,导演发现该片主人公宗智能说会道,而且有着因为感情生活而还俗的生动经历,于是进入跟拍阶段。第三年,宗智不仅习惯了摄像机的在场,而且期待在电视机上看到自己,于是主动联系导演要求再次跟拍自己采挖虫草的过程,形成了一种参与、交互和分享性的拍摄。当拍摄对象与拍摄者在互相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充分合作时,拍摄者才能将摄像机带入一些特定的场合,记录下最具主位视角的地方知识。尽管该片个别地方使用了情景再现手法,但仍然掩盖不了导演镜头下的一部民族志纪录片对社会现实的强烈责任感,令人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