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骏:用文字丈量山河故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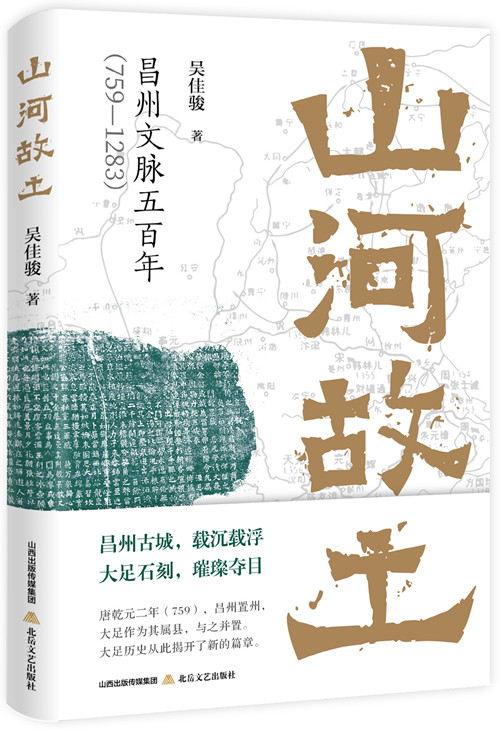
屈指算来,我从17岁开始写作至今,已逾廿年。这廿余年来,我虽先后出版了近20部书,却没有好好为故乡大足写一部书。十年前,我倒是写过一本关于大足石刻的小册子,书名叫《莲花的盛宴》,但该书远不能涵括大足的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和人文风俗等内容。
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知道,作家需有一个写作“根据地”,如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周、阿来的藏地、毕飞宇的苏北、苏童的枫杨树村……有了“根据地”,写出的作品才会有血有肉,厚重而深刻,不打滑、不发飘。换句话说,唯有找到“根据地”的作家,才能拥有创作的“母题”。否则,写得再多,都是瞎写。东一榔头,西一榔头,没有个靶心。借老百姓的说法,叫“破棉絮裹脑壳——乱撞”。
那么,我有创作“根据地”吗?不知道。说没有吧,好像不确切;说有吧,好像又没有建立。若干年来,我就这么在似有似无、似真似幻中蹉跎了岁月。时间真是残酷啊,弹指之间,我就从一个青年变成了中年。谚语云:“月过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这是大实话,听后让人心生悲凉。但于我而言,又似乎还不到“万事休”的时候。连桑榆之人尚且“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更何况我这样的中年人呢。《金刚经》上说:“众生皆苦,万相本无,唯有自渡”,诚哉斯言。人活于世,归根结底还在于“自渡”。当然,倘若在“自渡”的同时,又能“渡人”,那就更是善莫大焉了。古往今来,这样的智者还是蛮多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赵智凤。他开凿“宝顶山石刻”,初衷是为“自渡”,但直到如今,他所留下的这笔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依然在“渡人”。因此,赵智凤是不死的,他活在历史长河中,活在文化史册中,也活在后来者的心中。
我生为大足人,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我生活的地方,曾经诞生过赵智凤。可别小瞧了这个问题,一个地方,出过什么人和没出过什么人,是大不一样的。就像一个人,出生在什么环境,也是大不一样的。有的人从小就有追求、有教养、有担当,明是非,讲正义,成年后对社会贡献大;有的人自幼就顽劣成性,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甚至偷鸡摸狗,纸醉金迷,为非作歹,成年后危害社会,做人做事都没有底线。究其原因,皆可从生长环境中找到根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便是佛家所谓的因果。好因结福果,坏因结恶果,概莫能外。
扯远了,还是说回这本书。数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学者熊培云先生的著作《追故乡的人》。翻阅书中的图片和文字,我如遭电击,那一张张拍自作者故乡的黑白照片,勾起了我对过往生活的无限回忆,心底的潮水汹涌澎湃。合上书页后,我陷入了沉思。置身于当下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人的步伐已很难跟上时代发展的进程。只要我们打开手机,瞬间就会被互联网所包围。一机在手,遍览全球。哪怕你身处偏僻的村落,也好似站在世界的中心。我们所了解到的资讯,是赵智凤无法想象的,也是赵智凤的先辈们无法想象的。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们每个人都被网络安装上了无形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为何却丧失了赵智凤那样的理想和激情,缺乏赵智凤那样的愿力和创造力?我们发明、制造了那么多先进的东西,有几样是经得起时间淘洗的?我们的大脑中充塞了海量的信息,有几条是有价值、有营养的,对人的审美建构和人格提升是有益处的?当代人貌似博学,个个都是知识分子,可又有几人的知识是成体系的,有建设性和思想性的?碎片、碎片,一切都是碎片。碎片的布料可以缝制出一件“百衲衣”,但碎片化的信息却绝难修补一颗千疮百孔的灵魂。
就拿我来说,我虽以出生于大足而自豪,但我真正知晓大足吗?我能说出大足的一条河流、一条小巷、一段城墙的历史吗?不能。我的自豪不过是沾了老祖宗的光。认清这点,我的自豪瞬间转成了自卑。于是乎,我有了要深入探寻大足文脉的强烈冲动。我可不想当外地友人向我问及大足石刻的问题时,我能告知对方的,仅仅是解说词上的那点套话。
生而为人,是要知羞耻,懂敬畏的。不然,你有什么资格大言不惭地自称文化人。退一步讲,即使不谈文化,仅从职业而论,不管你是从政、从商、从教,假如对自己故乡的历史一问三不知,又怎能做到脸不红、心不跳地向他人侃侃而谈,俨然老僧说法,仙人说道。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好似回到了唐宋时期,整日在昌州的白天和夜晚游走,我听见过战乱声、哀鸣声、求告声,也听见过读书声、风雨声、念佛声。我与韦君靖和赵智凤对话,与严逊和冯楫聊天,与杨甲和赵昂发漫步,与文氏和伏氏工匠握手,与逃荒者和供养人座谈……跟他们在纸上的交往中,我收获满满。他们不但让我窥探到昌州五百年的峥嵘岁月,还让我洞悉了人类社会的隐秘变迁。在唐宋广阔的疆域版图上,昌州不过是个弹丸之地,但华夏民族不就是由无数的弹丸之地组合而成的吗?任何一个边地小城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发一场铺天盖地的飓风或海啸。
只是,本书关注的重心仅为昌州时期这段历史,书中涉及的大足人文,也限定在伴随昌州兴衰的时间范围之内。对于昌州撤销,大足归入元朝后,以及它在明朝、清朝、民国,直至当下的历史,并未涉及。今后若有契机,兴许我会再写一部书,专门探究大足从明朝到民国这段时期的风云变幻、跌宕时局和烟火民生。
实事求是地讲,写一部书不易,写好一部书更不易。由于记载昌州的史料阙如,要想全面而详尽地反映昌州的人文状貌,几乎不大可能。细查已出版的县志,以及唐宋时期关涉昌州的各种文史资料,所载也是只言片语,里面的信息模棱两可,这给我的写作带来了难度。目前,收录资料最全的,当数《大足历史文化大观》(重庆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一书,本书中涉及的部分事件和人物,依赖该书为据,在此说明并向编纂者致谢!
近几年,颇为流行为一座城市作传。自从英国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创作的《伦敦传》问世以来,好评如潮,其影响覆盖世界各国。中国作家受此启发,纷纷提笔,或自发或受邀为某座城市写传,如《南京传》《北京传》《上海传》《成都传》等。我无意跟风,挤进这支作传队伍中来凑热闹,博人眼球,赚取流量。况且,像大足这个地方,即便有蜚声中外的大足石刻,也未必人尽皆知。生活在这个花花绿绿、瞬息万变的时代,牵人目光和使人分心的事情委实太多了,谁会对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小城感兴趣呢?故我写昌州和大足,是真心想写,无关乎其他。作为一个喝着大足的水、吃着大足的饭长大的文学写作者,如果我不去写它,难道还指望其他人去写它吗?
最后,我想再啰嗦几句,谈谈本书的写作手法。在决定动笔之前,我的脑子里都是一团雾水,只有写作的念头,却不明确具体该用哪种文体来书写。究竟是采用小说、散文,还是采用诗、纪实文学,抑或时下大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不得而知。直到在那个下着小雨的午夜,我坐在电脑前,用键盘敲下“我沿着龙岗山拾级而上,漫漶的记忆日渐清晰”这句话时,我一下子找到了感觉,灵感的泉水汩汩涌出。那夜之后,我越写越顺畅,也几乎没有考虑自己写下的是什么文体。我唯一的驱动力就是写,写下自己对故乡的触探、体认和感知……当然,这写的前提,全都是基于爱。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文学也是“我思”的艺术,更是“我在”的艺术。只要我写出的文字,能搭建起一条通向故乡的路,至于它是何种文体,已然不那么重要了。为此,敬请读者诸君谅解,假如你们从本书中读出了诗、散文、小说的味道,皆属正常。其实,我真正渴望的,并不是读到本书的人,能从中读出什么文体,而是从我书写的故乡中,能读出或辨认出你们的故乡。从广义上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拥有同一个故乡。
已故著名作家陈忠实健在时,曾发誓要写一本能给自己死后垫枕头的书,他做到了,写出了《白鹿原》。我没有他那样的野心和雄心,只想今生能写出一本对自己有所交代的书。不然,纵使写作一辈子,哪怕著作等身,也是遗憾。现在,有了这本《山河故土——昌州文脉五百年》,我的心踏实了许多,宽慰了许多。至少,当我行走在故乡的大地上时,我的脚步将不再踯躅,身子将不再摇摆,心灵将不再空虚。
面对故土,我永怀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