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跑过去,就是新天地” ——访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祁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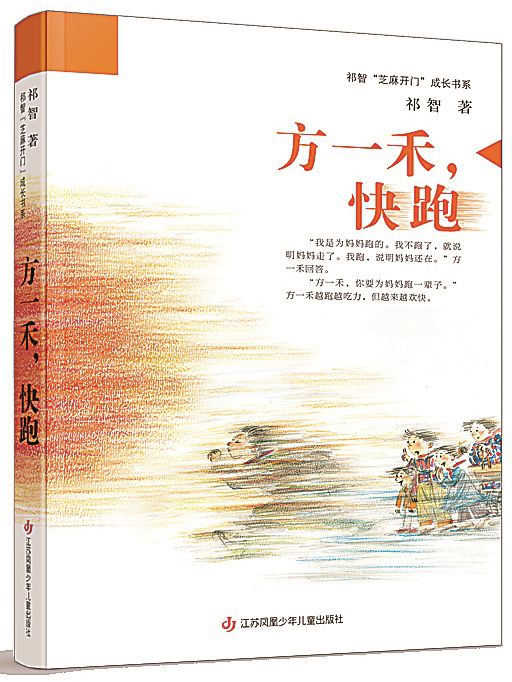
《方一禾,快跑》,祁智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4月
记 者:祁老师好,祝贺您的作品获得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方一禾,快跑》面对的是儿童文学很难处理的“疾病”和“死亡”主题。您认为,儿童文学作家该如何向孩子描述这类主题?
祁 智:感谢您的祝贺。我借此机会,感谢关注《方一禾,快跑》的师友,感谢读者朋友。
面对如同花蕾、如同朝阳的生命,儿童文学处理“疾病”和“死亡”的主题确实难度不小。但是,不涉及这一主题,儿童文学有“缺项”;这一主题涉及得不妥当,儿童文学有“缺失”。
我创作《方一禾,快跑》坚持两点。第一点,不刻意去涉及“疾病”和“死亡”的主题,而是当成写作的日常。《方一禾,快跑》中,爸爸在一个中午去世,虽然“突然”,但是我把这一情节处理成一天生活的一部分,而妈妈生病在床更是一家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以为,生活如此,“责任”不在我。第二点,创作之前,我用30年的时间在思考,我涉及这一主题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是对“疾病”的同情、对“死亡”的恐惧?显然不是。在“疾病”面前,同情是浅显的;在“死亡”面前,恐惧是简单的。那么,是想表达方一禾的自强不息、全社会对方一禾的爱心援助?更不是——如果这样写,可能是通讯报道,但肯定不是小说。小说应该进入更深刻、更复杂,又更明朗、更宏大的层面。爸爸的“死”、妈妈的“病”、方一禾的“跑”、大家的“帮”,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以为,生命如此,“责任”在我。
记 者:您在后记《生命如歌》中写道,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30年前在北方的一次采访,“方一禾”的原型是一位父亲去世、母亲患病、年仅八九岁的小女孩。您为何会选择在创作的时候,把叙事的主人公改为男孩?
祁 智:30年前的一个早春,我去青岛采访一个叫杜瑶瑶的小女孩。她的爸爸突然去世,妈妈重病卧床。她没有时间悲伤,因为家庭需要她支撑。她每天早上狂奔去医院拿盐水瓶,再狂奔回家喂妈妈吃饭、给妈妈输液,然后狂奔去学校。我问她累不累,她说:“不累。我跑,说明妈妈还在。哪天不要我跑了,说明我妈妈没了。我要为妈妈跑一辈子!”我刹那间泪水奔涌,在蒙眬中看到了我曾经的狂奔。
小时候,我妈妈经常被救护车拉走抢救。妈妈回来的第二天,我第一节课下课,要狂奔到街上的肉案拿一对猪腰子,狂奔回家交给外婆,再狂奔回学校。我不知道什么是“速度”,只知道耳边跑出风声就是最快。我每天都要跑到最快。结果是我能在上课铃响之前进校门,后果是我蹲在教室的墙边口吐白沫。我吐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喜悦和幸福:我是为妈妈跑的。那一刻,我又非常害怕,害怕哪天不再需要我狂奔。我想:妈妈,我愿意为你跑一辈子。
小说的主人公一般都有原型。我采访杜瑶瑶后写了长篇报道《微笑着面对生活》。在《方一禾,快跑》中,我把“方一禾”写成男孩子,是想尽可能把小说主人公与原型区别开来。作家优先考虑的是怎样便于创作,我在1997年就写过短篇小说《狂奔》,主人公“李祥”就是男孩子。何况“方一禾”也有我的影子。其实,“方一禾”有许多人的影子——我们多少人因为各种原因奔跑过,甚至还在奔跑中,耳边呼呼生风。
记 者:《方一禾,快跑》中用宋体和楷体两种字体对不同内容加以区分,宋体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楷体是在当下的叙事插入回忆、心理活动、对话或其他场景,让人联想起威廉·福克纳等作家的作品。这种“插叙”的设计是出于什么考虑?
祁 智:我交给出版社的《方一禾,快跑》都是宋体。编辑老师经验丰富,他们提出来,如果都是宋体,不停地出现的时空转换,会给读者尤其是小读者带来阅读的障碍,建议把“当下”用宋体,把“过往”用楷体区别。我非常赞同并且感激这一技术处理。
福克纳的小说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和多角度叙事,我曾经喜欢过。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如果福克纳的小说也按《方一禾,快跑》这种方法处理,可能阅读得要顺畅一些。我说,福克纳不会答应,因为跳跃、混乱、纠缠、拼凑、模糊应该是他想要的。
记 者:作品的题目特别生动,充满儿童趣味和游戏感。原本只是方一禾和同班同学追逐打闹的时候,出自班长马斯原之口的一句话:“方一禾,你快跑,我掩护。”但用作标题以后,又具有了新的引申含义。让人不禁思考是谁在催促方一禾快跑,他因何而跑,又将跑向何处?能不能请您谈谈是如何设计作品标题的?
祁 智:我有四点考虑。第一点,“方一禾”确实在快跑。我见过杜瑶瑶有三种快跑的姿势:早上狂奔去医院拿盐水瓶,双臂前后摆动;拎盐水瓶狂奔回家,双臂低垂;狂奔去学校,一手划动,一手按住背上跳跃的书包。不仅如此,我记忆里还有耳边的风声。让情节有画面感,是我小说的追求。第二点,正如您所说,“让人不禁思考是谁在催促方一禾快跑,他因何而跑,又将跑向何处”,有悬念——我以为,儿童文学应该调动一切因素,激发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所以“悬念”也是我的追求。第三点,“方一禾,快跑”朝气蓬勃,既有动感也有感染力,在沉重中有轻扬、在灰色中有亮光。不少读者朋友告诉我,读到最后,会情不自禁地喊“方一禾,快跑”,甚至不希望他停下来。第四点,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不幸、不测、不顺是常态,唯一的办法就是“快跑”。快跑过去,就是新天地。新的生活永远需要我们风雨兼程。
记 者:故事里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次要角色”,有天真烂漫的小小少年罗小盼、程璐璐、谢菲、马斯原等同龄人,还有如韩老师、岳老师、薛老师、公交司机马叔叔、社区王阿姨等成年人。尤其让人感动的部分是王阿姨建的微信群里的一条条信息:“方一禾起床了。方一禾点煤气灶了。方一禾门没关跑出去了……”方一禾不是一个人“负重前行”,有很多关心他的人,在他的背后默默无闻地付出。而且,直至故事结尾,方一禾都没有发现这些“无名英雄”。您为何选择把他人的付出,写在主人公成长的背后?
祁 智:30年前,人们对“弱势”个人或群体的关心比较简单、直接,甚至有些“粗暴”,不怎么在乎他们的接受,考虑更多的是怎么给予。后来,人们的关心逐渐变得得体、合适,甚至不留痕迹,充分考虑到接受者的尊严。这是时代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具体表现。当年的杜瑶瑶虽然想独自担当、不想麻烦别人,但事实是,离开了众人的帮助,她举步维艰。我当年每次都能在上课铃响之前狂奔进校门,后来才知道,哪里是我准时,是校长让门房师傅等我进了校园才敲响预备铃。不仅如此,时代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具体表现还在于,人们不再以为对“弱势”个人或群体的关心是单向的给予,人们在给予中也获得了力量、温暖和升华。这本书的背景是社会、时代,是悲悯、博大。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我们互为主角,也互为背景。
记 者:以成年人的心态来读这本儿童小说,会感到特别沉重,直至故事的结尾,方一禾感到“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在酣梦中踏上了莫比乌斯带。我听过一种说法,如果某个人站在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带的表面上沿着他能看到的“路”一直走下去,就永远不会停下来。这种拓扑学的概念对应的是“无穷”,可以解读为主人公的苦难永无止境,也可以解读为生活和希望永无止境。故事结尾的艺术处理背后有何深意?
祁 智:莫比乌斯带是“神来之笔”。故事原本是,妈妈睡觉前在孩子手腕拴了一个铃铛,绳子拉在自己手上。妈妈需要孩子的帮助时就拉响铃铛,铃铛不响孩子就安心睡觉。但是我总觉得这个结尾弱了,这个结尾甚至是我一直不能动笔的原因之一。后来,我给一位数学特级教师打电话,希望听听数学课。老师很快安排了“学科+”的数学公开课。我听到一位老师讲“莫比乌斯带”,立刻想到了在妈妈和孩子之间的那根绳子,想到了方一禾在夜深人静中对爸爸的思念,热泪盈眶。当天晚上,我写了一章,请老师看看有没有专业问题。老师说,虽然不知道整部小说是什么内容,但看了这一章有“说不出的难受和欣慰”。我知道“成了”。我在定稿的时候又审视了“莫比乌斯带”的结尾,我看到了“相逢”,当然也看到了“无穷”。生活之路难免曲折坎坷,但是生命必定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记 者:您曾在中学当过多年老师,后来又在出版社从事童书出版工作。文学专业的学术训练、语文教育的实践经验和童书出版的现场观察,都为您“儿童本位”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您认为,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要怎样才能贴近儿童生活?
祁 智:不要以为写到了儿童和动物,就是儿童文学。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要发自内心地热爱生活、敬畏文学、崇尚经典、深入孩子、永葆童心、感谢读者,做好素材储备、精神准备。作品永远不注水稀释、不胡编乱造、不哗众取宠、不低级趣味、不潦草急就。我们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