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娃娃》:历史暗夜中的星光与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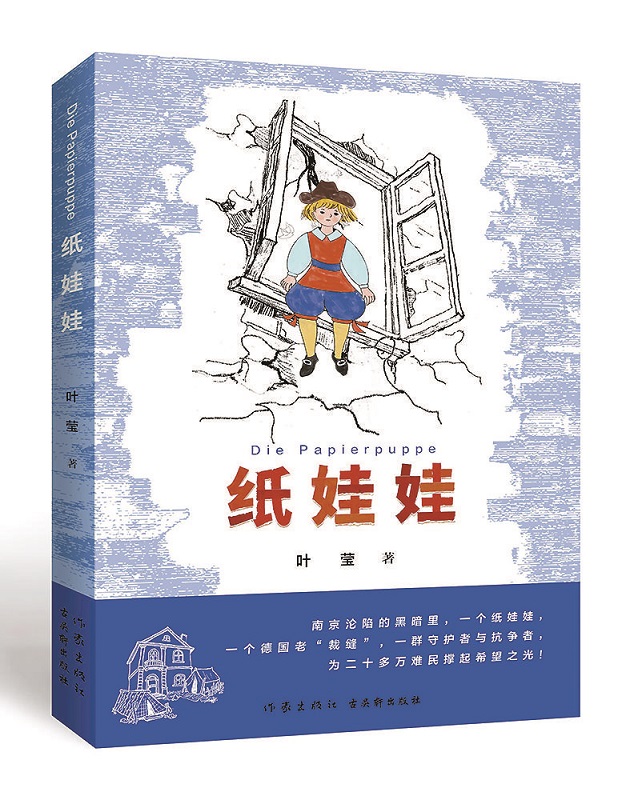
每年12月13日上午10点,一声尖锐的鸣笛总会穿透南京冷冽潮湿的天空,这一刻,全国上下共同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这情景不禁勾起我儿时在南京上小学的回忆。大约在上午第三节课期间,随着鸣笛声的响起,语文老师停下了手中的板书,他沉静地望向全班,缓缓说道:“家里父母是南京人的请举手。”顿时,几十双小手齐刷刷地举起。“爷爷奶奶是南京人的请举手。”老师继续问道,这次只有零星几人举手。“爷爷奶奶的父母还是南京人的请举手。”话音刚落,教室骤然安静,所有同学的手都悄然放下。随后,老师向我们讲述了那段沉痛且残酷的历史。自那以后,年幼的我心中常怀疑问:那些在1937年的冬天,与我当时年纪相仿的孩子们,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怎样在炼狱中求生,怎样在失去一切之后,重建对世界的信任?
这个萦绕在我心头的谜团,如同一粒深埋的种子,在多年的沉寂后,终于因为旅德作家叶莹的新作《纸娃娃》而破土发芽,作品通过南京小男孩田天的视角,运用简洁而温暖的语言,托举起了那段沉重的历史,宛如暗夜中的星光,使人寻找到一种温暖而深邃的回响。
长期以来,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儿童小说并不多见,它对写作者而言是巨大的挑战:如何向心灵尚且稚嫩、世界尚未成形的孩子,讲述一场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罪行?如何在既尊重史实的严肃性基础上,又不至于用纯粹的黑暗压垮他们,而是传递出基调明亮、充满希望的价值观?这无疑是对写作者思想深度、叙事技巧和情感把控能力的考验。
《纸娃娃》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成功填补了该题材的创作空白。作品以罕见的国际救援视角切入,巧妙地将厚重的历史通过童真的视角和象征物(纸娃娃)进行转化,使青少年能够以理解和共情的方式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书中对生命的平视与尊重、对勇敢与诚信的辩证思考,以及对中德文化元素的鲜活融入,使其成为一部兼具历史深度、生命教育与国际视野的优秀作品。
《纸娃娃》以日军侵华战争为背景,依托《拉贝日记》中的真实记载,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叙事原则,细腻讲述了南京沦陷时期,男孩田天一家在日军侵略下艰难求生的故事。其间,德国邻居施耐德先生慷慨地将自家住宅提供给尽可能多的难民,并积极参与组建南京国际安全区,拯救了无数生命,谱写了一曲温情的赞歌。
“温情”是贯穿全书的核心词汇,也是叶莹处理这一沉重题材的基调,这源于一种坚定的信念:即使在最极致的黑暗中,人性的光辉也从未彻底熄灭。从主人公田天与德国小女孩乌苏告别时收到的纸娃娃“小裁缝”,到陪伴他度过孤独和恐惧的小黑猫,再到后来成为“盟友”的小老鼠“黑豆子”,作者构建了一个万物有灵的温情世界。这些意象,是与儿童读者建立情感连接的桥梁。
书中对纸娃娃的描写尤为动人。乌苏自幼与田天一同长大,南京沦陷前夕,她随外婆返回德国,临别时赠予田天一个身着大红褂、宝蓝裤子,脚蹬一双黑亮皮鞋的纸娃娃,并深情叮嘱:“如果日本人来欺负你,你也要像勇敢的小裁缝一样。”从此,这个被称作“小裁缝”的纸娃娃陪伴了田天一生,赋予他勇气,与他对话,共度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光……直至年迈,他与孙女一同翻出泛黄的纸娃娃,那段往昔岁月再度浮现心头。值得一提的是,施耐德这一姓氏在德语中意为“裁缝”。作者叶莹精通德国文化,她将格林兄弟童话《勇敢的小裁缝》中“一下打死七个”的勇气与智慧,巧妙地化用到叙事中,为本书增添了浓郁的浪漫色彩与文学互文性。
除了纸娃娃,小黑猫与小老鼠也相继陪伴田天度过了艰难的时光。最终,小黑猫为救爷爷,英勇地牺牲在日本兵的刺刀下。伤心的田天安慰被吓得不敢闭眼睡觉的弟弟:“以后老鼠会为我们守门的,我们得把老鼠当朋友了。”而在后续情节中,老鼠“黑豆子”及其同伴在日本兵闯入时,勇敢地爬上去撕咬,成功吓退了敌人。这些情节设置不仅充满童趣,易于孩子们理解和接受,更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了关于生命平等、乐观向上的人生哲学。即便面对如此灰暗的生活,作家依然能用这些温情的意象,与小读者产生情感共鸣,其中也蕴含着对勇气、生命、正义的深刻思考。
如同经典电影《辛德勒名单》或《美丽人生》一般,叶莹对那段历史的书写充满文学的克制与守护感,仿佛一位时光雕刻师,小心翼翼地用纸笔为小读者们勾勒出一个在黑暗中透着微光的世界。这里聚焦人性的光辉,并充满了对勇敢与诚信的深刻辩证思考。儿童文学对语言艺术的精确度要求极高,《纸娃娃》的语言简洁而贴切,充分契合人物性格,句子短小易读,给人一种仿佛聆听妈妈讲故事般的温情脉脉与娓娓道来的感觉。例如,田天的这段内心独白:“如水的月光挤进房间,照在纸娃娃上,纸娃娃仿佛被照得有些不好意思,害羞地低下了头。”这段细腻的描写,展现了战争背景下一个孩子诗意的内心世界,有效抚慰了小读者的心理。即便是身处灾难中的施耐德,也常以幽默的话语安抚苦难中的孩子,或自我调侃。当大家躲进阴冷潮湿的防空洞,紧张地缩着脖子迎接警报声时,他竟逗乐道:“我得把自己想象成阿里巴巴,在地下宫殿找到一堆宝藏,却正被四十大盗追杀,我该如何守住这些财宝呢?”这种苦中作乐的幽默,不仅是一种高级智慧,更是一种强大的心理防御机制。它教导小读者们,如何以一种高贵而坚韧的姿态,勇敢面对生活中的逆境。
《纸娃娃》的成功,还在于它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立体、成长变化的人物形象。德国人施耐德(老施)、中国男孩田天、朵朵,铁匠的儿子周永、中国士兵大李等,他们都不是扁平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会在苦难中思考、在挫折中改变的个体。
田天与周永的成长轨迹尤其具有教育意义。他们的父亲,因为一个是鞋匠,一个是铁匠,手上布满了劳苦的茧子,竟因此被日本人误当作士兵抓走。两个少年最初认为,只要拥有足够的勇敢,就能救回父亲。他们试图以稚嫩的肉身之躯去拼死一搏,这是一种源于本能的、纯粹的勇气。然而,他们却被沿途意外救下的受伤士兵大李劝退。最终,由朵朵说出了那个关键的道理:“要打赢坏人,光勇敢是不够的,还要机灵。”这句话,是少年们用血的教训换来的成长顿悟,它区分了鲁莽与真正的勇敢。而士兵大李的人物转变同样光彩夺目。他从一开始对德国人施耐德充满误解与戒备,到最终被田天的善良和施耐德的无私行动所感化,在施耐德的庇护下逃脱日本人的杀戮,并最终成为他的得力助手。这条人物线,深刻阐释了“真相”与“成见”的辩证关系。
最动人心弦的,是作者对少年之间复杂情感的细腻描摹。当铁匠的儿子周永被大家误会是汉奸,去讨好日本人时,田天内心充满了被背叛的痛恨。然而,在孩子纯粹的正义感与深厚的友谊驱动下,他依旧在周永生命垂危之际伸出了援手。直到最后,他才恍然大悟:周永是为了打听两位父亲的下落才不得已而为之,并且他差点为了救一个陌生的中国女孩逃脱日本人的欺辱而牺牲生命。田天最终选择了原谅。这个过程,不仅写出了战争背景下患难与共的真情,更写出了少年敏感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对正义、良知、宽容与信任的艰难求索。这对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青少年读者而言,无疑是一次深刻的品格教育。
作者叶莹常年旅居德国,深刻体察中德两国对二战历史的态度与教育方式,书中南京的血色记忆与柏林的历史忏悔相互映照,不仅引发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度思考,更以故事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当年施耐德先生守护南京难民,日后南京民众亦支援困境中的他,这份跨越国界的守望相助,正是人类共通的善意与良知的体现。
正如二战期间的自传体小说《安妮日记》中名句所言:“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我依旧相信,人的本性是善的。”《纸娃娃》亦是如此,作为一部兼具历史厚度、文学美感与教育温度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它不仅仅是一本专为孩子们——“过去历史的阅读者、行进历史的见证者、未来历史的书写者”——精心打造的图书,更是一座紧密连接中德两国文化与历史记忆的桥梁。它犹如历史长夜中的璀璨星光,将和平的种子与人性之光,深深植根于下一代的心田,久久回响。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