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指南与诗意通行证——钟代华儿童诗集《月亮开花》的审美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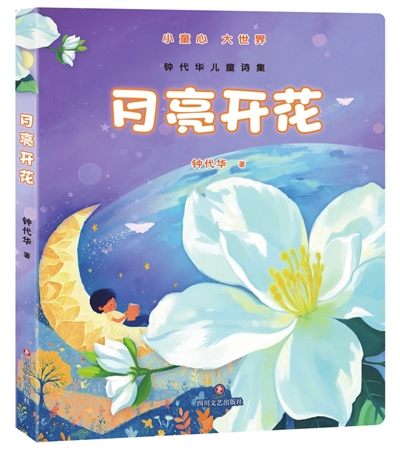
一本儿童诗集,就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心灵花园。
儿童需要清新的空气、甘甜的水、洁净的食物,还需要童诗的滋养。童诗可以悄然改变孩子认知世界的方式,打通思维的“任督二脉”,从而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奔涌的想象力、灵动的语言力与丰沛的情感力。给予孩子幸福的方式有千百种,其中至为珍贵的,莫过于和孩子一起走进一首首澄澈美好的童诗。
诗人钟代华,是一位“与童年终身签约”的童心守护者。自1983年以诗歌叩响儿童文学殿堂之门起,他四十多年勤于笔耕,追求卓越,不断地拓展童诗的疆域,不断地突破自我,摘得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诸多桂冠。如今,他捧出儿童诗集《月亮开花》。在他的诗行里,月亮开花,云朵过桥,石头说话。他用清澈如溪的语言,为孩子编织奇思妙想的诗意王国。这既是一本献给孩子的心灵之书,也是一份献给家长与教师的沟通启示录。它邀请成人在与孩子共读的时光里,重返童年的清澈源头,擦亮蒙尘的童心。成人由此能重新理解孩子,也能重新理解自我。这有助于人们构建更和谐的亲子关系与师生关系,携手去做无限趋近幸福的人。
一、看见万物之美
儿童诗意启蒙的核心,在于重塑孩子与世界对话的方式。这部诗集完全摒弃了成人化的说教与概念灌输,代之以纯粹童真视角的“惊奇诗学”——在熟悉中发现惊奇,于寻常事物之中,挖掘不寻常的光芒。它赋予孩子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让他们明白:一花一叶,一沙一石,皆蕴藏着让心灵震颤的深邃之美。
万物有灵的诗意逻辑,让自然规律散发脉脉温情。“月亮还没下班/上了整整一个通宵”(《月亮还没下班》)颠覆了天体运行的法则,将月亮拟作一位不知疲倦的守夜伙伴。“架起峰峦峡谷/连接南北东西/晃一晃/摇一摇/空中的云桥”(《云朵过桥》)将天际线幻化为奇妙的童话渡口,空间被赋予叙事的魔力与游戏的趣味。这启迪孩子认识到:万物皆有呼吸、心跳与故事。
微观世界亦有宏大的剧场。诗人引导孩子俯身细察,在细微处发掘壮阔的史诗。《狗尾草》中矮小纤细的草茎,依然可以“铺成草地上/金灿灿的一片霞”。“难道水珠/长了亮晶晶的翅膀/跟着鸟儿飞走了”(《水珠离开花儿》)将一颗露珠的滑落,演绎成一场充满依恋与憧憬的盛大告别。诗人告诉孩子,渺小并非微不足道,它同样蕴藏着震撼人心的力量。露珠轻语,野花微笑,流云足迹……诗人以细腻笔触化万物为诗。
以感官联通,做诗意训练。书中的诗行构建出一个感官交融的奇妙空间。如《月亮开花》中的“圆圆的月亮/开出一朵/好大好白的栀子花/有多亮/有多香”,诗人将视觉形象“月亮”及其光芒(亮)进行了神奇的转化:视觉的明亮、嗅觉的清新与触觉的柔美(花瓣质感)融为一体。月亮变得可感、可触、可闻,充满温馨与生命力。
当孩子学会戴上诗意的滤镜观察世界,周遭的一切便从“已知的平板”蜕变为“充满未知的立体迷宫”。这种能力的迁移,滋养着对一花一木的敬畏,对日常瞬间的珍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正是驱动孩子永葆探索热情的不竭动力。
二、以想象建造奇幻王国
想象力是童年珍贵的超能力,是创造力的火种与心理韧性的基石。这部诗集如同一座想象力的工坊,以精妙的诗性语言为催化剂,点燃孩子心中无穷的创造之火。
它构建了一套想象力系统,其核心在于挣脱现实法则的束缚。当孩童在《追大树》中骑行时,“一棵棵大树往后退”,物理世界的运动逻辑被改造为儿童感知的逻辑——静止的植物获得了自主位移的能力。在《石林》中,沉重的岩体被重新赋形,“片片石头云/朵朵石头花/坚硬的花瓣/铺成石林彩霞”,密度与重量在诗性空间中蒸发。这些诗句让重量消散、时空重构。它们昭示想象力的终极自由:诗的世界,是诗人创造的,可以御风而行,可以超越现实世界的逻辑。
因此,抽象的存在,在诗中被锻造为可感的躯体。缥缈之物凝练成可触碰的诗意实体。声音在《歌声》中展开羽翼——“流水的歌声在奔流/鸟儿的歌声在飞翔//奔流和飞翔/各有各的翅膀”,声波振翅的轨迹清晰可见。流水在《水的头发》里获得毛发质感,“风儿给水面/搓一搓头/梳一梳头发/亮亮的/头发好光滑”,液态被赋予固态的触觉体验。
儿童特有的“假如游戏”在此升华为对存在本质的哲学叩问。星星在《月亮还没下班》中也成为夜班工作者,“星星们一直在发光/疲倦不疲倦/渐渐的/纷纷跟月亮/挥手说再见”,天体运行被注入生命伦理的维度;沙滩上消失的痕迹引发存在主义沉思——“脚印呢/脚印哪去了”,赫拉克利特式的流动哲学在童声中回响。最令人动情的是《垃圾娃》中对垃圾的拟人化:“垃圾娃/流浪的娃/跌跌撞撞/开不出一朵花”,引领孩子感受被遗弃物(垃圾)所象征的困境。这是一种对边缘生命的共情启蒙,是一种关于悲悯之心的培养。
留白的艺术激活创造共同体。“冬天也有飞翔/冬天也会绽放/把冬天当作春天玩”(《冬天的水鸟》)的悖论宣言,则要求儿童调动生活经验破解寒冬的生命密码。这种留白实则是权力的让渡:诗人刻意保留的诗行空隙,正是小读者从欣赏者蜕变为创作者的仪式场。当孩子为流浪的垃圾娃构想开花之法,或为心跳的云朵编织冒险故事时,他们已在共情中习得最深刻的创造伦理:所有想象终将返回大地,为现实助力。
于是,小读者们便悄然习得了共情万物的能力。他们获得了在现实困境中重构希望的方法与力量。
三、养一座语言的花园
诗是语言的艺术。童诗是语言艺术的艺术。《月亮开花》堪称儿童汉语美学的启蒙读本,它将母语的灵动与童心的清澈熔铸成生机勃勃的表达范式。
诗人的语言炼金术,是在看似“无缘”的词语间嫁接生命的奇迹。在《月亮开花》中,“星星也开花了/朵朵小花/争着闪烁花儿的光芒”,星星与花结缘了,夜空重获生命。这种超常搭配的魔法贯穿全篇:云朵不再是气象学现象,“白云是棉花/黄云是金兰/红云是木棉”(《蓝天大花园》);冰雪剥离了寒冷的刻板标签,成为“春天的摇篮”(《冰雪是春天的摇篮》)。词语的超常搭配也带来了感官藩篱的爆破——听觉与视觉在“鸟儿唱着歌/歌声翠绿”(《歌声》)中血肉交融;光线在“阳光懒洋洋地/从林间滴漏”(《闷热有啥可怕》)里获得液体的重量与慵懒。
诗集中的拟人化并非简单的修辞,而是呼应儿童思维里的万物有灵。石林拥有社群生活:“一起晒太阳/一起看飞鸟/一起听回声/一起睡在月光下”(《石林》)。“水的头发”是一种新颖的命名——“细细的水波/一丝丝柔柔的/水的头发”——无生命的水与有生命的人,在诗性目光中彻底相融无间。诗人更以元诗性自觉反观语言自身。《缝隙》中“任何位置/都能长出春天的奇迹”的箴言,既是生命颂歌,更是对诗歌创造力的隐喻。诗歌甚至自我指涉创作过程。《森林大戏》描述“唱给大山听/山更高昂/唱给森林听/树更雄壮/唱给天空听/天更宽广”,恰是诗歌影响力的镜像。
当孩子模仿“山是地上的云/云是天上的山”(《水的头发》)这样充满想象力的表达时,他们绝不仅仅在学习修辞技巧。更是在练习一种能力:用奇妙、贴切且充满美感的方式表达内心感受。这种能力将伴随其一生,成为情感抒发、思想交流的优雅通道。
四、用诗意释放、净化情绪
这部诗集是对儿童情绪世界最温柔的回应。当成人习惯性地对孩子的眼泪说“不许哭”时,诗人用诗行宣告:请把你的情绪浇灌成诗的花园。它提供了温柔而有效的通道,将情绪具象为可对话、可理解的角色。儿童被压抑的恐惧、愤怒、孤独与焦虑,转化为月光下的花朵、会唱歌的浪花和流浪的云朵,在诗意的蒸馏瓶中完成情感净化。
过于繁重的课业,无疑对孩子的生命力是一种桎梏。《最后的月光》以奇特的意象呈现这种窒息感:孩子们“暂时被允许的逃离”到月下,笑容竟是“几朵若隐若现的/淡淡的微笑”。被补习班囚禁的心灵,连欢笑都成了稀缺资源。“那片题海/简直水深齐腰/那堆题山/怎么越来越高”——齐腰的“题海”、不断长高的“题山”,形象展现了刷题战术的压力。而月光成为温柔的港湾:“最后的月光/有点凉了/夜风在挠我们的发梢”。最具疗愈力的是结尾的拉钩约定:“明晚随叫随到”。月光下的约定成为对抗题海的秘密契约。
《谁跟我玩》则直击陪伴缺失的孤独。当父母上班、姐姐深陷作业时,“我呆呆地/望这幢楼/望那幢楼”。高楼的反光刺眼如刀刃,割裂着童年的完整性。窗外“花香的新鲜/钻进窗口”,但“姐姐依然愁眉苦脸”。这种对比揭示课业如何异化感官——当自然的美好无法抵达心灵,情绪便成为困在水泥格子里的小兽。诗人以“彩云望了她很久/才慢慢飘到天边”的云朵拟人,让自然成为沉默的陪伴者,替代缺席的亲情温暖。
儿童的恐惧心理,常被成人忽视。诗人对此却给了充分的关注,和巧妙的诗意应对之术。《打针》展现身体恐惧的诗意脱敏:“窗外的太阳/照着我的屁股/阳光怕不怕打针”。将疼痛转移到阳光身上的想象,是心理位移疗法。奇妙的想象,“云朵发烧了吗/一会儿又红又白/一会儿又黑又青”,用云的“病症”消解自身痛苦,在幽默中完成情绪宣泄。《溶洞》巧妙地化解了儿童对幽闭空间的恐惧。诗人将幽闭恐惧的黑暗洞穴转化为童话王国:“怎么不出去呢/难道是住在洞里吗/静悄悄地游戏”,未知的恐惧被“静悄悄游戏”重新赋义。而“谁不怕冷不怕黑/谁是最静的冠军”的提问,把恐惧对象转化为竞赛项目,这是游戏疗法的精髓。当孩子想象“钟乳石”与“暗河里的小鱼”正在比赛的场景,对溶洞的感情早已由惧到爱。
《海贝娃》处理的是分离焦虑。贝壳“涨潮时被扔在了沙滩/从此离开了大海的家”。当它最终被拾起“摆放成大海的玩具/大海的画”,暗示所有孤独灵魂都可能在艺术中被重新整合。还有《天边的朋友》,太阳与山头“久久不想分手”的依恋,将分离焦虑升华为温情守候:“山头还在原地/等太阳重新回来/在最高的天边招手”。这种宇宙尺度的陪伴想象,为孤独提供终极慰藉。
诗人最富特色的创造之一,是在诗中以缤纷的童趣和灵动的语言,构建了一个儿童情感的共鸣场域。儿童的所感、所想、所思都能在此找到共鸣,得到慰藉。
五、在真善美的星空下
这本诗集还有重要的启蒙价值:为童年精神世界奠定坚实基石,引领孩子奔向真、发现美、拥抱善。
真的核心之一,在于童真。童真在此非幼稚的代名词,而是灵魂未被污染的清澈泉眼。诗人守护童真的方式,是归还孩子感受世界的权利。在《谁跟我玩》中,高楼玻璃刺眼的反光里,一朵路过的彩云向写作业的姐姐招手;废弃的塑料瓶不再是“垃圾”,而是“躲藏在角落/漂浮在水面/丢弃在院坝”的回不了家的流浪娃(《垃圾娃》)。重命名的魔法,让儿童永葆童真:温柔注视一草一木。童真在游戏中重获翅膀。骑小车追树的孩子(《追大树》),跌倒了还笑哈哈,“脸上开满小花蕾”,这样纯净的笑容是童真本来的模样。(下转12版) (上接11版)
当露珠与花儿“互相问好”(《水珠离开花儿》),当“太阳是蓝天的金贝壳/慢慢滑向山那边的/哪片海滩哪个港口”(《天边的朋友》),童真在万物对话中生长出根系。孩子心灵因此种下星光:在题海沉浮时记得数野虫的乐谱,在水泥森林里为流浪的云驻足。诗人为孩子筑起一座精神堡垒,守护童真免受侵蚀。而守护童真,就是守护诸多美好的开始。
诗集的字里行间,“善意”汩汩流动。万物互联的共情启蒙,在儿童心田栽下向善的种子。《不行 不行》中,诗人将路灯点化为生命体。当成人借着灯光匆匆赶往目的地,孩子却在“都走了/谁来陪路灯/孤不孤单/可不可怜”的叩问里,拥抱到了善良。一个“陪”字,正是诗人培育善心的精妙设计——它使孩子从光的接受者蜕变为温暖的赠予者。当孩子为路灯停驻,诗人已完成最深刻的向善启蒙——善不仅是缥缈的情怀,更是行动的承诺。路灯与“衔起片片雪花”的水鸟(《冬天的水鸟》)、飘离花瓣的露珠(《水珠离开花儿》)在诗中结成生命同盟,教会孩子万物皆需温柔以待。
以童眸为棱镜,将宇宙万象折射为诗意光谱。在《看霞》中,天空被点化为动态花园:“朝霞/晚霞/天空盛开的花//是风儿擦过/还是雨水洗刷?”“盛开”一词让云霞挣脱气象范畴,成为会呼吸的生命体。“那最红的那片红/却越来越淡/越看越暗”,在消逝中领悟美的瞬逝性——这与《水珠离开花儿》中“还没玩够呢/怎么就离开了”形成互文,共同培育对美的珍视。不断地发现美,珍视美,就会形成一种对美的信仰。这种信仰会让儿童在残缺中看见圆满,在终结处相信新生的永恒契约。
当儿童将诗集中的精神养分内化,一种“诗意生存”的方式便悄然构建:以敏感捕捉事物的微光;以执着永葆童真;以柔软体恤万物悲欢。真、善、美,这三根巨柱,撑起了健全人格的穹顶。它让灵魂得以在纷繁尘世中,诗意地栖居于星空之下。
《月亮开花》是一部童年诗学启蒙读本,一部关于如何“诗意栖居”的情感地图。翻开它,就能触摸自然的脉动,感受童真的芬芳,学会以诗的方式“打开世界”。书中的每首诗都有一颗闪亮的童心,照亮世界,唤醒好奇。让诗意引领孩子发现美、奔向真、拥抱善。
当父母与孩子、教师与学生共读它之时,那些跳跃的诗行便化作双向流动的情感虹桥:向上,它输送着成人世界久已遗忘的童心露水;向下,它浇灌着儿童初萌的诗性胚芽。这不仅是亲子共读、师生共读,也是一场成人重返童心、儿童提升诗性的精神共振。当家长从“成绩监察员”变身为“童心翻译官”;当教师从“标准答案制定者”进化为“诗意催化剂”;当孩子指着天边的云雀跃道:“看!那朵云在风的作业本上写诗呢!”教育的真谛便在《月亮开花》的扉页上,签下了永恒的契约。
一片花瓣可以唤醒整个春天,一本儿童诗集可以照亮小读者整个人生。《月亮开花》是一部洋溢童真与灵性的诗集:文字如萤火般闪亮,引领孩子步入纯净、温暖的诗意世界,种下热爱自然、追求真善美的种子。它是对童心最深情的赋权——郑重地告诉每一个儿童:你有权对万物保持惊奇,有权用诗意重新命名一切。
【作者简介:南风子,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著有“红色少年诗意传奇”系列长篇儿童小说《红宝石口琴》等。曾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奖、孙犁散文奖、江苏省优秀科普作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