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气韵 生命赞歌 ——歌剧《红高粱》如何重塑新时代“红高粱精神”
当苍凉的唢呐声打破静谧,帷幕拉起,风雨如晦,高粱如火。那一刻,“第四堵墙”轰然倒塌,我们已不是看台上的观众,而成为高密东北乡的英雄儿女。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这部由国家大剧院出品,莫言编剧、郭文景作曲的原创民族歌剧的问世,无疑是对那段峥嵘岁月最深沉的致敬,也是对那群风吹雨打、雪压火烧却始终挺立的民族脊梁最炽热的礼赞,还为我们在新时代重新叩问与诠释作品中的“红高粱精神”提供了可见、可听、可感的表达方式。

一、1985到2025:四十年回望“红高粱”
回首望去,“红高粱故事”已然经历了四十年的改写与演绎。从1985年小说横空出世,到2025年歌剧响彻大剧院,四十年来的“红高粱”早已超越文本本身,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不断生长。莫言、张艺谋、郑晓龙、郭文景等一代代艺术家以各自的方式赋予其声音与形象,通过表演、音乐、唱腔将高粱地里的血性与韧性注入当代人的精神血脉。
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年轻的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完成一篇题为《红高粱》的中篇小说,它以恣意张扬、充满野性的叙事风格,讲述了“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在高粱地里轰轰烈烈的生命传奇,为抗战小说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随后出版的《红高粱家族》增添了《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四个中篇,使故事版图更为完整,彻底稳固了“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地理空间。
1987年,张艺谋根据《红高粱》小说改编执导的同名电影问世,获得1988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打破了中国电影在国际奖项上的空白,标志着中国电影正式进入全球视野。2014年,由郑晓龙导演、赵冬苓等人编剧的六十集电视连续剧《红高粱》在四大卫视联播,掀起热议。除了影视剧之外,根据《红高粱》小说改编的剧种还有京剧、豫剧、晋剧、评剧、茂腔,以及舞剧和话剧,这些剧作各具特色,表现出“红高粱故事”强大的适应性与生命力。
值得注意的是莫言本人对“红高粱故事”的“重写”:2018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戏剧剧本《高粱酒》呈现出不小的改动,他弱化了原作中的暴力渲染,强化了人物内心的道德挣扎与情感张力,尤其突出了高密儿女在民族大义面前的觉醒与担当。歌剧《红高粱》正是承续这一脉络,其旋律间流淌着土地的血脉,唱词里镌刻着牺牲的尊严,在音乐与戏剧的交融中,将唢呐声化作灵魂的呼啸,使每一株摇曳的高粱都成为不屈意志的象征,最终在舞台的光影变幻中,完成了一次对民族气韵的当代召唤与生命赞歌的庄严复调。

二、 歌剧舞台的民族气韵
歌剧《红高粱》的舞美设计是新时代“红高粱精神”最直观的载体。导演与舞美深谙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让那片“高粱地”成为全剧真正的主角——舞台的多数场景皆以其为背景,背景墙上红色的穗浪起伏涌动,使故事发生在肆意蔓延的高粱海洋之中。尤为醒目的是舞台上方悬挂的半球形LED屏,它大大拓展了视觉表达的维度:时而化作漫天夕阳,映照苍茫大地;时而提供俯视视角,在抬轿情节中呈现花轿内部如鲜血浸染的囚笼;时而又切换为仰视角度,表现出村民埋伏在高粱穗间窥敌的紧张态势;更在日军压境时,投射出倾轧而来的巨大卡车阴影,营造出逼真而骇人的压迫感与恐惧感。
较前些年的《高粱酒》而言,此次歌剧版《红高粱》的人物与情节也有不小的调整,剧作者这番匠心无疑更加契合了“红高粱精神”的当下表达。在歌剧第六场中,刘罗汉被日军审判,逼迫他说出余占鳌与九儿的下落,此时,受日军协迫的乡亲孙虎改为了戴老三,莫言本人也提到,这是十分重要的改动,有效避免了角色冗杂,同时也丰满了戴老三的形象——他虽胆小怕事、贪财嗜酒,却在面对日本人的残暴行径时拼死抵抗,与刘罗汉一同完成了从怯懦到英勇的蜕变,彰显出普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血性抉择。刘罗汉殉难之时,乐声骤寂,空灵的钟声响起,仿佛敲击在每一位在场观众的灵魂之上,此时,舞台上的乡亲们低声齐唱:“高粱红了,鬼子来了。乌云满天,九月落雪彻骨寒。白鸽子死了,百灵鸟哑了,绿叶鲜花被冻残。晶莹的白雪,落在通红的高粱穗子上,玛瑙般的颗粒,覆盖着黑色的土壤。”吟唱循环往复,间隙便是如同大地呜咽般的低沉钟声。此处的钟声设计绝妙,它既是哀悼刘罗汉、凤仙、戴老三等人生命逝去的“丧钟”,同时也是唤醒围观民众的“警钟”,预示着烈士们的死亡将唤醒华夏子孙心中的英雄血气与抗争意志。
此次对“红高粱故事”的再创作亦有意识地强化了民族音乐语言的表现力。乐队在传统西方歌剧的管弦乐基础上,巧妙融入唢呐、胡琴、锣鼓等民族乐器。尤为生动的是,九儿带领妇女备膳时,乐团竟以器乐惟妙惟肖地模拟出锅碗瓢盆的清脆撞击。这种音画交融,共同营造出植根东方土壤的审美场域,使“民族气韵”化为可感可观的舞台真实。这也正是歌剧《红高粱》成功重塑新时代“红高粱精神”的美学密钥,它生动地表明,那种深植于人民、为了家园不惜牺牲的集体意志,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今天我们面对复杂世界格局,构筑文化自信、讲述中国故事所不可或缺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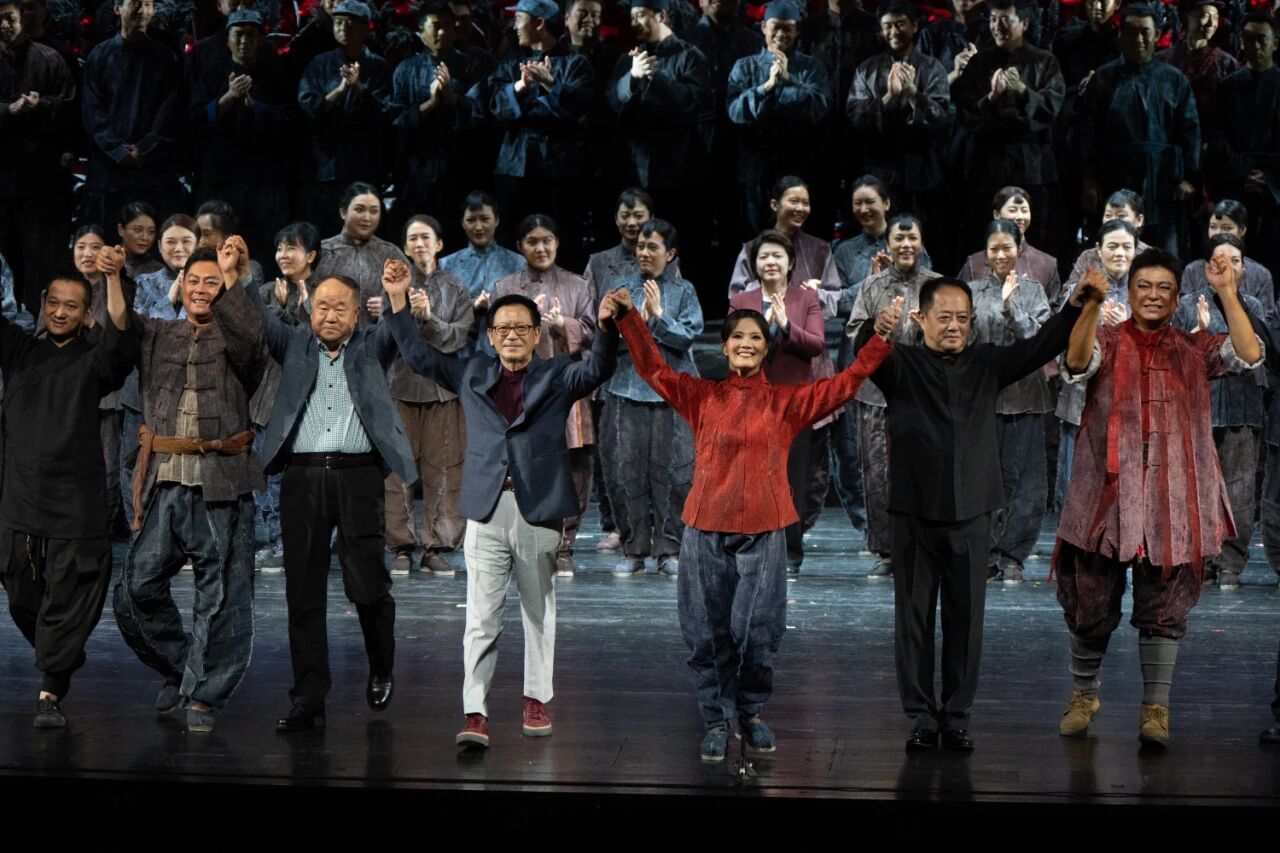
三、 “红高粱精神”的当代共鸣
诚如莫言所言:“红高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植物。”它已是一种刻入民族基因的精神意象——是绝境中捍卫尊严的呐喊,是压迫下追求自由的野火,是深植于泥土却永远朝向天空的脊梁。这种精神,既闪耀在九儿、余占鳌、刘罗汉等个体的英雄壮举中,也涌动在高密东北乡每一位父老乡亲的血脉里,更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集体人格。歌剧《红高粱》以舞台为土壤,让这株“红高粱”再次蓬勃生长,它所奏响的,正是一曲我们今日仍需高唱的“生命赞歌”。
小说的线性叙事难以展现视觉与音乐切换所产生的巨大张力,而这正是歌剧艺术的魅力所在。在第二场中,一座精雕细琢的中式婚床成为舞台核心,九儿身披红嫁衣,静坐于血色光影中,周遭的红灯笼、锦缎铺盖,共同构筑起一个华丽而压抑的封建牢笼。当患有肺痨的单扁郎踉跄闯入,在婚床上展开一场追逐时,戏剧的荒诞感油然而生。他唱腔滑稽,强调“姻缘天定”;九儿的回击则如惊雷,唱出“宁死不嫁汉奸”的决绝。二人风格迥异的唱段形成尖锐对抗:单扁郎的唱腔带着俚俗的狡黠,九儿的反击则如山崩地裂。于是,婚床化身“戏台”,上演着一场被围观的仪式。这种“台中台”的嵌套设计,极大地浓缩了冲突,让个体的反抗在与环境、命运的对抗中,迸发出悲剧性的崇高感。更加震撼人心的,是紧随其后的场景切换:舞台从压抑可怖的婚床转变为无边的高粱地。余占鳌与九儿在此深情重唱,那简单的问答“这里就是家”,与先前场面形成天壤之别。情感如野火般挣脱所有束缚,使这片高粱地化作一场对生命、自由与爱最直接、最热烈的礼赞。
此外,歌剧与小说的一大差别在于它对主角的弱化,文本中“我爷爷我奶奶”的绝对中心在《高粱酒》剧本中就被转移至刘罗汉、凤仙、九儿、余占鳌四人身上。在这版歌剧中,这种文本式的角色中心又再度遭到解构,取而代之的是群像式的叙事张力。其中,合唱队的运用在歌剧的叙述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迎亲队伍的喧闹、酿酒伙计的号子、奋起抗敌的村民们的怒吼……这些多声部的合唱,构成了红高粱故事的“人民底色”。他们不再是模糊的背景板,而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歌剧通过这种形式,将聚光灯从余占鳌、九儿、刘罗汉等少数英雄,扩展到了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集体群像,正如第七场中余占鳌与游击队员们的合唱:“我们是红高粱的子孙,我们是东北乡的儿郎。我们是东北乡的儿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用生命捍卫人的尊严,用鲜血浇灌脚下的土壤。”正是这种从“小我”到“大我”的视角转换,使得“红高粱精神”超越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方式,升华为一种扎根于人民、为家园故土不惜牺牲的、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
歌剧《红高粱》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对民族美学的意象的娴熟运用,更在于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它使“红高粱精神”继续前行,在当代艺术的阐释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它绝非尘封的旧迹,而是一簇能在不同时代被不断接棒的火炬。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坐标下,这部作品向我们昭示:那种植根于生命本真的自由渴望、不屈于压迫的坚韧顽强、为守护家园而敢于抗争、无惧牺牲的意志,早已沉淀为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而这正是我们穿越磨难而生生不息,继而在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这部歌剧的成功实践也启示着我们,真正动人的中国故事源于对自身历史、民间精神的深刻理解与自信表达。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世界的文化舞台上,发出独特而响亮的中国声音!
(作者简介:张世维,国家开放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王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