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受众层面文学等叙事艺术的现实功用
一、长叙事艺术的体验功能
本期栏目讨论的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以文学为代表的叙事艺术,在今天对于读者来说到底有什么现实功用?
前不久,在决定是否要“入坑”《博德之门3》这款游戏时,我曾遍寻知乎、B站、小红书上的经验分享,看这款游戏适不适合我。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决策之前可能都伴随着类似的搜索、浏览动作。然而就在搜索这款游戏的游玩体验时,那浩如烟海、或真或假的视频、图文对于我来说却失效了。我越搜越焦虑,越浏览越糊涂。
可能很多读到这段文字的人不知道《博德之门3》是什么,这是一款在电脑或游戏主机上运行,平均需要117小时才能通关的角色扮演游戏。如果雷打不动每天玩两个小时,差不多两个月才能玩一遍。而一遍又绝不足以穷尽这个游戏的内容,它采用了极致的“网状叙事”,你扮演的旅行者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可能会影响这个世界的生态和故事的走向,据说结局有数十上百种之多。这种长度和多义性使它比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更像现实或一段人生。在这种规模的经验面前,小红书等平台上提供的信息和几十上百年前的广告牌匾、街头传单没有区别,它们只能让我知晓其存在,却不足以让我了解它到底是什么。
此时长篇小说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作为前互联网时代的“遗老”,文学或影视,当然也包括一些叙事手段近似的游戏,它们在辅助人们认知现实的层面虽然也不完美,但因其长度和复杂性,在分享含混、厚重的经验时仍是短视频、短图文无法取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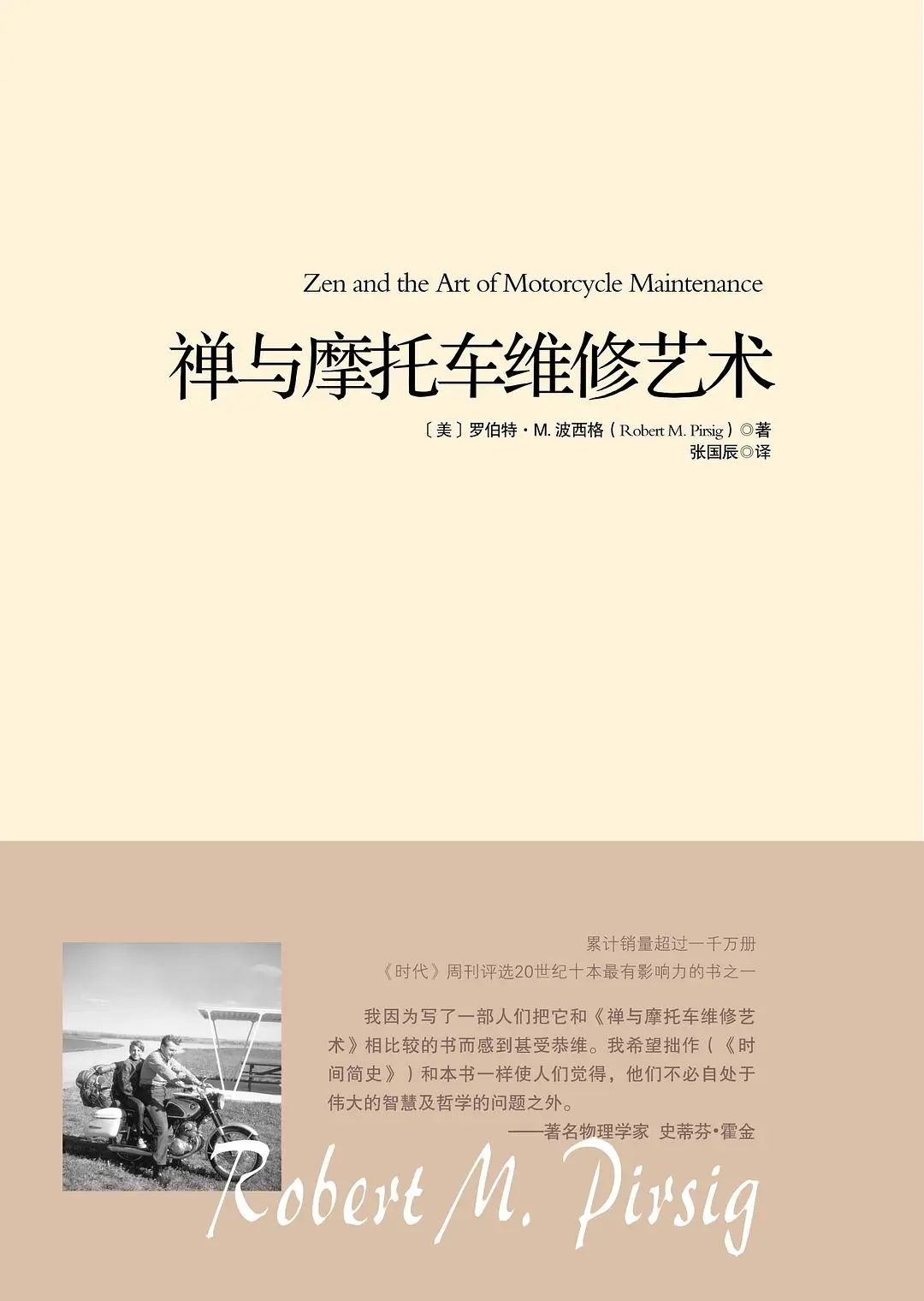
二、文学与成功学
读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既不是问题,也没有什么争议。无论“文以载道”(韩愈)还是“独抒性灵”(袁宏道),无论“神学是上帝的诗”(薄伽丘)还是“作家应该成为社会的秘书”(巴尔扎克),人们只会争论文学“怎么用”,而不会说文学“没有用”。哪怕说要把诗人赶出“理想国”的柏拉图,也正是因为意识到艺术“扭曲”现实的巨大潜力,才要以强硬的言辞防患未然。
只有在奉行经济价值至上的社会,文学才会陷入“无用”的困境,相比一本摩托车维修手册,一本小说除了消闲和带来一些思想或道德上的“包袱”,并不能很直观地解决现实问题,让人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尊重和成功。就像我会在决定玩一款游戏前仔细权衡以免浪费时间一样,对于现代人来说,重要的从来不是一本书定价几何,而是他们的时间、精力、情绪成本,能不能直观地转换成对应的收益。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看出近几十年纯文学作家多么“叛逆”,莫言、余华、王安忆、贾平凹、残雪、苏童、格非、毕飞宇、李洱……这些人们叫得上名字的作家,几乎都在写“失败者”且“非英雄”的故事。从学理角度这不是问题,学者有一万种理论和方法将其变得合理、变得意义重大,但是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这是无法理解的——读这些故事不仅不会让人获得成功,更有失败的危险,他们的故事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
作家、批评家、学者都学富五车、文思泉涌,但缺少从大众角度对这个问题的清晰言说。
三、“无用之用”是遮羞布吗?
正是因为这个问题说不明白,所以被逼问得急了,靠文字为生的人就会说上几句“无用之用”之类的话。大多数时候,这句话和孔乙己的“君子固穷”无甚差别,不过是让“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气息”。
“无用之用”出自《庄子》,指的是无论树木、动物还是人,皆有可能因为无现实之用而长久地存在——其实作为一种生存哲学,所谓无用指的仍是有用。那这个用处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从另一种角度解释这个问题。以“四大名著”为例,它们或可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代表,在我看来其共性是用最“稳妥”的方式完成最“危险”的任务。比如《西游记》,西天取经、降妖除魔,看起来多么“正能量”,可是稍一细读就会发现,里面尽是对人类社会结构性暴力的彻底失望和深刻批判。既得利益者肯定痛恨这种言论,但《西游记》一经成书其精神就再无法被磨灭。哪怕其作者已经主动或被动地销声匿迹,哪怕那些“老少咸宜”风格的电视剧、动画片再深入人心,《西游记》的原典及其精神也永远被以“名著”姿态铭刻在了民族的灵魂中,稍有风吹草动,那些批判性的力量就会卷土重来。不信就看2024年的《黑神话:悟空》,其火爆和游戏创作者继承了原著的批判精神直接相关。从这个角度看,当代文学中那些不被理解的“失败者”故事其实和“四大名著”做的是相同的事,只不过在技巧和完成度上有欠圆融。
在我看来,这才是“无用之用”最容易被理解的一面——文学不是没用,而是作用太大以至于不会被轻易使用,其存在本身就有巨大的意义,阅读文学也就相当于分享了它的意义。
说了这么多,还是为了带出本期栏目的三篇文章。赵天成的《阿多诺禁令和冬妮娅情结——也谈小说的认知》针对的是我上面讨论的第一部分内容,他的文章写出即便让渡这种体验方面的认知功能,小说仍然不可替代的既定事实。黄瀚的《“反讽现实主义”:知识分子写作的“应物”之道》,论述的则是“失败者”故事的意义。刘绍禹的《梦逐潮声去:影像叙事与现实生活的连线》带我们回到人们连穿衣吃饭、谈情说爱都要向电影看齐的时代,彼时叙事艺术的“无用之用”正绚烂绽放。如今我们大多数的观影行为,已经从大银幕迁移到了小屏幕,但属于叙事艺术的时代仍未远去。
(作者单位:中国作协创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