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读者的“期待视野”,让小说回归小说 ——“青春三部曲”创作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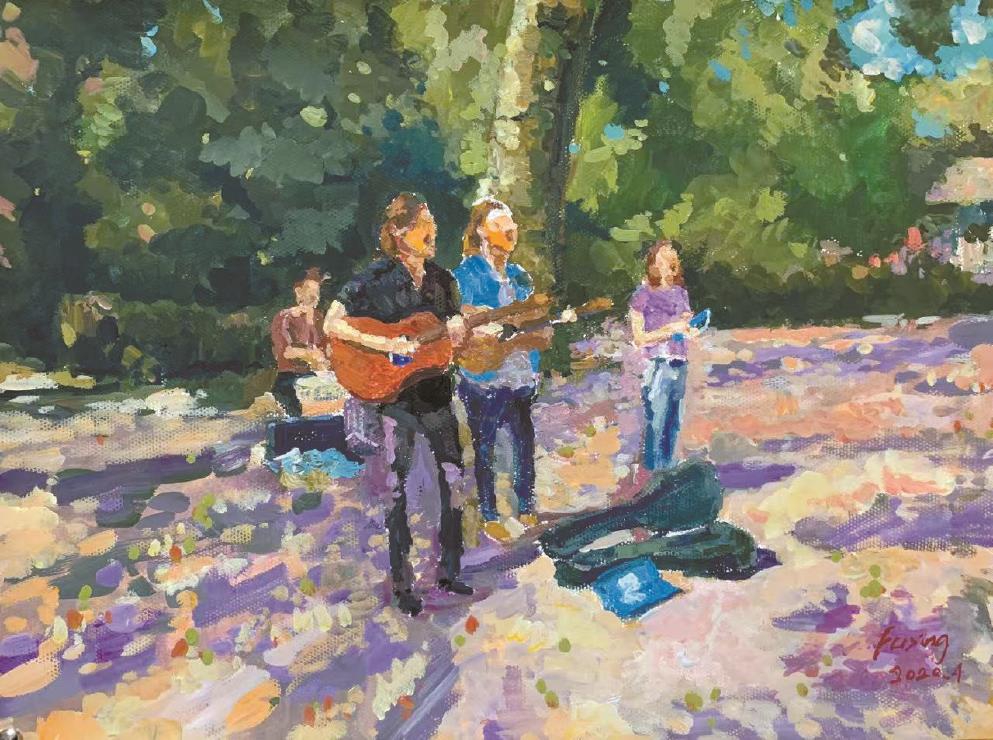
傅星画作《五月》
《怪鸟》:二十个故事的重组
父母亲离世,老房子要卖了,我看到了房子挂在链家网上,就想写两个短文纪念一下,可收不住了,竟写了二十个故事,后来又把二十个故事拼装成一个长篇,这个长篇就是个意外。
回忆是无边的,创作过程就是穿越。在那里,我与亲人和熟人们见面,又遇见了自己。这是一次真正的沉浸式写作,状态好极了,像这样的好运不是说有就有的。
小学时,一位苦大仇深的女工来做报告,女工在痛说身世时太过难受晕倒了,我们就看着她被急救去了医院。女工的口音太重,没有人知道她都说了什么,整个礼堂一直乱哄哄的。
奇怪的是,我在写这些故事时真的会想起这位女工。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轻一点,不要过度渲染,即便写死亡,也不要去展示太多的细节。这不是史料性的文本,它毕竟是小说,更重要的是审美性,它应该好读,再论其他。
好的故事在表层上一定是具有吸引力的。想象力、生动畅晓的文字、节奏、既意外又合理的转折、情感、笑点等等,但故事深层意义或许更为重要。我一直喜欢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卡夫卡、卡佛等人的短篇,那些故事,真是令人叹服。
上世纪六十年代,小三子在门前的林子里去弹击一只怪鸟,后来他伤到了“我”的一只眼睛,那年“我”十一岁,成了一个怪人。一只眼是伤感的,经常泪流不止,而另一只永远是火辣的,像在燃烧。
在一个雨天,“我”在高楼上爬行,从一个窗爬向另一个窗,因为那个窗里有“我”热恋的女神。后来在农场“我”收到了照片:“我”趴在高墙上,像个超人,又如同一只不怕死的大闸蟹,而“我”已经完全认不出那是自己了。
——这是《怪鸟》一首一尾的两个故事,通篇的创作风格差不多。小说出版后有各种解读:时代和成长,荒诞和恐惧,与父辈沟通的桥梁……也有读者带了书去旅行,并视其为清朗的夏日之风。
《培训班》:戏剧性和碎片化
我想写一个在艺术院校培训的故事。年轻时在农场,我曾任文艺宣传队创作员,并有两次被推荐到戏剧学院学编剧。回想起来,那段生活真是很丰富。最初的想法是,表现艺术院校的题材应该套用一个完整的戏剧性结构,起码在风格上可以保持一致。会是什么呢?一个荡气回肠的中心事件?或者是一个别致的俄罗斯套娃式的剧情?哪怕来一个最古老的三一律模式的故事也可以呀。但是我差不多等了一个季节,却什么都没有等来。有一度真是泄气得想放弃了,但是人物已经活了,我感觉到了人物的温度。
后来还是动笔了,是那种自然的书写。有人提倡这么写,理由是可以跟着内心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创作方法,在我看来小说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门技术活,它需要更多的文学素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造力。
无论如何,哪怕是在自然流的小事件的堆砌中,有一些关键部分我也不敢忽视。
性格尽可能丰富的人物,以及命运的不可知:主人公苏威廉原以为是来学作曲的,却阴错阳差学了编剧,他的人生剧本就此被改写。晓霁爱上了老师,但老师深陷在失去前女友姜美丽的悲痛中,两人是悲剧性结局。无论台上台下,唐高潮始终是如同英雄人物般的存在,但是农场来的女友揭示了他极度伪善的一面。诗人赵青不再写诗,去乡下学了浦东说书“老阿奶养猪”,他获得了成功。
悬疑的设置:《贝克论技巧》一书作为小道具贯穿始终,书的消失在班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宿舍门前的牛奶箱都被贴上了“悬疑”二字的标签,扮演列宁的特型演员由此受到了巨大伤害,而谜底却在半个世纪后男主不经意的一个动作里被揭开。某几天,培训班一些同学的家里有骗子出入,骗钱骗物,警察甚至怀疑是一个行骗集团所为,包袱抖开了,原来是同学亚雯的分身。她的表演风格受到嘲弄,然后亚雯就天才地完成了她的杰作,她说她要进入校史和艺术史。
场景太重要了:小楼、平台、深夜饮食店、燠热的剧场,幕布破烂的前台以及有个绿色更衣柜和硕鼠乱窜的后台;红楼、白楼、灰楼、红楼前的苹果树和草坪长椅;学校食堂、小鲁削土豆如同威米尔的一幅画,海边;他们坐在那里暗自伤心,远处有小号在吹奏,图兰朵,夜的海水是漆黑的,呢喃着;五十年后的上海马路,孔乙己的家,洛可可风的住宅,时尚地标,而老克勒差不多就在那个空间死去。
台词:好的台词可以表现人物的个性,而且推动剧情的发展,一些背景前史的交代性文字也可以在台词中消解掉。台词要短,一来一去要有弹性,明快并富有节奏感。当然,如果需要,长篇台词也无妨,写上几页也是可以的。那个中午,在闸北孔乙己的陋室里,主人酒后大谈戏剧,语言酣畅淋漓,一泻千里,且兼有很强的动作性。写着如同爽文,又像在写话剧的高潮部分,演员走向台前,追光聚在他的脸上,角色台词的每一个字都是打出来的,击向剧场的各个角落。
可是当我写下这一切之后,再看,感觉上收获了一盘大杂烩。我不再理它,扔在一边。又过了些日子,某天心情不错,把这个文本打开再看,竟见到星星点点的如同碎片般的闪光之处。
我删去了四五万字,居然一点都不心疼。瘦身后的文本轻盈了许多,倒是我想要的样子。整个过程就像建楼,没有一张完整的结构图纸,但还是弄成了。
评论家杨扬为《培训班》一书写了序,最后他是这么说的:这是非常奇特的阅读体验,有不少小说家从自己的创作经验中感受到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是结构。但傅星《培训班》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结构而是情绪,它一点一点越来越大,像冬天的雾霾,弥散空间,莫非这迷雾一般的情绪就是结构小说的最有力的支撑?
杨扬自然无从知晓作者的折腾,但是他的确看到了什么,并表示出疑惑。我以为这是一个课题,在排除了传统戏剧结构之后,那么碎片化的叙事方式是否也具备了戏剧性修辞的表达空间?关键点又在哪里呢?
《毕业季》:岁月里丰富的调子
偶然刷到了一个小视频,高中毕业,男生手持花束,摁响了门铃,女生开门,惊喜连连。男生约女生去参加毕业舞会。这个时候,玫瑰色的阳光勾勒出青春,如此美好。我注意到下面的诸多留言,有人在问,我的青春在哪里?
在写《毕业季》时老是想到这个小视频。我上世纪中学毕业,那时高考还没有恢复,去农村,或是留城,每人都有一个档次,档次是难以跨越的。中学毕业,人生的轨迹就被指定了,如同宿命。机会转瞬即逝,那么希望,挣扎,抗争,坠落等等,整个过程便滋生了文学,也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基本骨架。
小说的写作很顺。首先确定的是全知视角,群像,七个主要人物。有太多的内容要装进去:阿松有美术特长,可进美校试点班,又因偷画人体而被取消保送。文武打乒乓球,只要再赢一局,即可进专业集训队,可关键分的一个擦边球断送了他的一切。金河金麦是双胞胎,姐弟俩在分配的去向上纠缠不止,反转再反转。写作就是写不同的自己。没错,我把自己大卸八块,然后让其生成各种样貌,最后,我从一个典型环境走来,又成为一群典型形象。
全景下的七个人物,摆平就可以了。铺陈开来笔力均衡,人物之间互相缠绕,扯不清理还乱,有时候他们就如同一个板块,在时间的河流中若远若近,若有若无地朦胧地呈现。
小说初发《当代》杂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的时候,我想为图书画些插图。不想要冷暖对比太过强烈的对比色,纯度和明度都不要太高。我在调色板上挤出十余种颜料,调出了一些灰色。这些色彩是我喜欢的,它可以画出层次,让画面更为丰富,在色彩干湿不定时,轻轻地动笔,自然地轻扫出年代感的笔触肌理。
叙事语言的调性也是尽可能地白描,舒缓一点最好。有时候,我会觉得一切都很简单,他们长大了,算是毕业了,走上了预定的轨道,有的人挣扎了几下,无用,爬起来拍拍屁股继续前行。表达清楚就可以了,形容词和副词统统不要。图书责编沐沐那次跟我说,海洋一家真惨,看得太难受了。天啊,这可不是我要的效果。我鼓励她继续读,再翻几页就好了,你会感觉到这些故事还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很快地就融进了时代的洪流,且自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结局多半还是可以的。
朋友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写的都是好人。我想我避免的是那种史诗般的生死冲突书写,不过是完成了一种个体的散淡表达,还有一些任何时期都有闪现的人性之美和爱。
这本书我写了个序言,其中写了一个真实细节:离校后的那些日子很无聊,等通知。那日和几个同学去长风公园野餐,然后天黑了,大喇叭在呼叫游人离园,我们不管,还是喝酒,撒欢,疯疯癫癫地学狗叫,后来醉眼朦胧中见湖面上升起了一个红月亮。我想表达的意思是,那时候的年轻人有自己的状态,没什么选择也没什么好卷的,就顺着走吧,当然也有自己的景观。
我坐在阳台上,脚下是一堆书和杂志,想好好地读读小说,可多半很难读,甚至读不下去。有一些可能是创作中的问题:譬如那么多的宏大叙事,上来就是一座城,涉及几个家族三四代人,或者更多。为了一个小小的情节,竟要从五百年前说起,不见尽头的铺垫看得人累死。历史文化,民风民俗也是真伪莫辨,让人提不起兴趣。没完没了的史料性的考证考据,一旦交代完毕,故事就此结束。符号般的人物,扁平得就如同劣质卡纸,假人们在照片式的布景前跑来跑去,就是为了告诉你一个小学生都懂的理念。看上去是在讲故事,实际上在拗三观,拗过来又拗过去,作者好像从来就是真理在握似的。一点心思就敷衍成篇,让人不胜其烦,完全和时代脱节的,不搭调地去刻意营造某种古意。还有那些实验文本,所谓的先锋性,无论从哪个维度看,都找不到作者的更前卫的生活姿态和艺术主张,以及许许多多的陈词滥调。
写小说并不容易,要让读者接受,并有兴趣去完成最后的整合更难,在我看来应该高度重视读者的“期待视野”。本人在当文学编辑时,往往对青年作者多有苛求,可一旦自己操刀,就会落入已知或未知的坑里。一直在期待有更多的小说技术层面的探讨,要好好学习。读者的大量流失真是让人沮丧。我一直在告诫自己,切莫要拼了老命把小说写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