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巴黎的日与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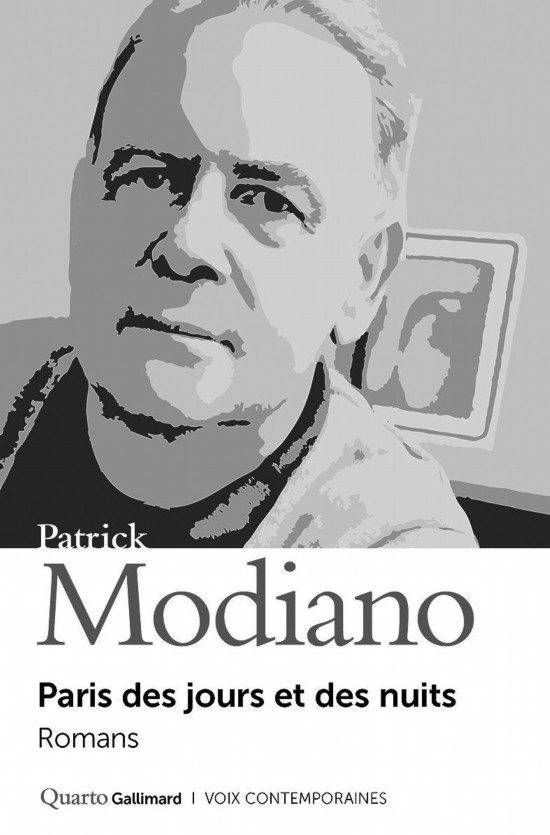
摄影师布拉塞和莫迪亚诺并非同时代人,但是布拉塞镜头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巴黎,让莫迪亚诺重新发现了一个逝去的时代,一个他正在寻找的时代,也是他希望让读者认识的时代。
法国作家、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曾说过:“我生活过的巴黎以及我在作品中描述的巴黎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写作,只是为了重新找回昔日的巴黎。这不是怀旧,我对过去不曾感到遗憾。我只是想把巴黎变成我心中的城市,我梦中的永恒之城。在这里,不同的年代相互重叠,恰如尼采所说的‘永恒轮回’。”对莫迪亚诺来说,巴黎的几个地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6区的孔蒂码头15号(15 quai de Conti)。莫迪亚诺在《户口簿》(1977)中写道:“1942年6月的一天傍晚,在一个和今天一样温和的黄昏,一辆三轮车停在了孔蒂码头的岸边,这里将货币博物馆和法兰西学院分隔开来。一位年轻的女士从车上下来。她是我的母亲。她刚从比利时乘火车抵达巴黎。”当时,莫迪亚诺的母亲路易莎·科尔贝刚到巴黎,落脚在孔蒂码头15号,几个月后,她遇到了阿尔贝·莫迪亚诺,生下了莫迪亚诺。两年后,弟弟鲁迪·莫迪亚诺出生。1949年至1953年,兄弟俩被父母送到法国南部城市比亚里茨,再是巴黎近郊茹伊昂若萨斯。1953年兄弟俩重新回到孔蒂码头15号。随着年纪增长,他们开始拓展外出探索的范围,他们过桥,从左岸来到右岸,在卢浮宫前的卡鲁塞尔广场玩游戏。然而,1957年冬天,一切变了样。1月27日星期天,莫迪亚诺从寄宿学校回到家后获知了弟弟去世的消息,而上一周兄弟俩还在孔蒂码头的卧室里一起整理邮票册。从这一天起,他在巴黎变得形只影单。
莫迪亚诺和孔蒂码头15号的关联远未结束。2002年出版的弗朗索瓦·维尔内《非典型短篇小说》的序言由莫迪亚诺撰写,标题就叫作《孔蒂河岸15号》。维尔内是一名抵抗运动成员,1945年3月死于达豪集中营,年仅27岁,直到60年后,这部作品方才问世。生前他曾暂住在孔蒂码头15号,莫迪亚诺在《马戏团经过》(1992)中写道:“早在我父亲住在公寓之前,这些书就已经存放在那里。之前的房客,也就是《围猎》的作者,把它们忘记了。其中有几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个神秘的弗朗索瓦·韦尔内的名字。”当莫迪亚诺住在孔蒂码头15号的时候,弗朗索瓦·韦尔内如同一个看不见却挥之不去的幽灵伴其左右,以至于莫迪亚诺在序言中写道:“我花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找到这个人的踪迹和他的真实身份……”
16区的洛里斯通街93号(93 rue Lauriston)曾是二战期间法国盖世太保的所在地,为首的有亨利·拉丰和皮埃尔·邦尼等人,他们从事着鲜为人知的神秘勾当。《夜巡》(1969)里有:“一辆浅蓝色的塔尔博特从洛里斯通街开了过来”,《缓刑》(1988)里写道:“安德烈经常和洛里斯通街的那帮人来往。”之所以“洛里斯通街的那帮人”始终萦绕在作家的心头,那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德占期间和那帮人有着微妙的联系,为了在战争中生存,他的父亲混迹于黑市之中,干着投机倒把的事情。莫迪亚诺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1966年彻底决裂,之后再无联系。1977年,莫迪亚诺的父亲在瑞士去世,很久以后他才得知这一消息,于是关于父亲的诸多谜团变成了无解之谜。
18区的库斯图街(rue Coustou)在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暗店街》(1978)里就已经出现了,它连接着克利希林荫大道和莱皮克街,附近是布朗什广场。十年后,在《缓刑》里,莫迪亚诺又写道:“在后来的年月里,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除了有一次,我重新见到了让·D,我那时二十岁。我住在布朗什广场附近库斯图街的一间房间里。我在尝试写第一本书。”《小珍宝》(2001)中的地址由于多了门牌号而变得更加具体:“第一天晚上,我猜想我母亲可能就住在我现在这个房间。就在我打算租房的那天晚上,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地址——库斯图街11号。”在《这样你就不会迷路》里,主人公在库斯图街11号写了20多页《布朗什广场》,与此前的《缓刑》形成了呼应。
14区的奥德街28号(28 rue de l’Aude)也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里。在《夜的草》(2012)中,“我”曾生活在这条小巷,“我在奥德街28号收到阿加穆里寄来的一封信时很吃惊,我在那里租了一个房间,但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地址?从丹妮那里要到的吗?我带她去过几次奥德街,但好像是很久之后的事情。我的记忆都扭结到了一块。”又或者,在《地平线》(2010)中,“博斯曼斯一时无法作假,就说出自己真实的出生日期,并说他住在奥德街28号。”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名字都是“让”,而“让”正是作家最开始的名字。莫迪亚诺还经常在书里提到63路公交,这条线路今天依然存在,往返于东边的里昂火车站和西边的米埃特门,途径巴黎植物园、拉丁区、圣日耳曼德佩街区、亚历山大三世桥、特罗卡德罗、布洛涅森林。莫迪亚诺回忆说,每到周日,父亲会带着他们兄弟俩来森林散步,一直走到湖边,直到傍晚6点,他们再搭乘公交返回。
莫迪亚诺认为自己“是唯一一个将当时的巴黎与今天的巴黎联系起来的人,唯一一个记得所有这些细节的人”。如果说莫迪亚诺笔下的人物大多是虚构的,那么代表作《多拉·布吕代》中这位和标题同名的小女孩则确有其人。
1988年,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1941年新年前夕的《巴黎晚报》上,看到一则寻人启事:“寻失踪少女多拉·布吕代,十五岁,一米五五,鹅蛋脸,灰栗色眼睛,身着红色外套,酒红色套头衫,藏青色半身裙和帽子,栗色运动鞋。有任何消息请联系布吕代先生和夫人,奥尔纳诺大街41号,巴黎。”登报寻找多拉的是她的父母。这个犹太少女在那个冬天离开天主教寄宿学校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莫迪亚诺锲而不舍地搜寻着关于多拉的资料,展开了一系列调查。作家像侦探一样,回到奥尔纳诺大街41号,询问了多拉的邻居,查阅了很多官方文件资料。他还在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的《关押在集中营的法国犹太人回忆录》(1978)里找到了“多拉·布吕代”这个名字。克拉斯菲尔德还向莫迪亚诺提供了其他珍贵的资料,包括几张多拉及其亲人的照片。
莫迪亚诺竭尽全力将多拉从虚无的遗忘海中打捞出来,试图还原多拉的真实面貌及其心路历程。当然,《多拉·布吕代》绝非单纯意义上对多拉这一人物的传记写作,而是杂糅了纪实与虚构的文学形式,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作家对多拉的生活图景进行了大量的想象,甚至试图在文学空间内让多拉和自己的父亲建立某种联系。2015年,也就是莫迪亚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次年,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决定在18区设立一条名叫“多拉·布吕代”的长廊,莫迪亚诺自然受邀出席落成典礼。他在致辞中说道:“这是第一次将一位无名少女永远铭刻在巴黎的地理中。多拉·布吕代已经成为一个象征。在这座城市的记忆中,她代表着成千上万名离开法国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惨遭杀害的儿童和青少年。”
2024年9月,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推出莫迪亚诺的合集《日与夜的巴黎》,收录了作家于1982年至2019年间出版的九部精选作品和一篇文章《夜晚的布拉塞》。布拉塞,本名久洛·豪拉斯,生于1899年,是一位知名的摄影师,他和莫迪亚诺曾于1990年合作出版了《巴黎的温柔》,这部作品集结了布拉塞20世纪30至40年代在巴黎拍摄的照片,并附有莫迪亚诺撰写的文字。2022年,莫迪亚诺对文字进行了修改和压缩,作为《布拉塞:100张新闻自由照片》序言。莫迪亚诺回忆说,他曾经在朋友罗杰·格勒尼耶的家里见过布拉塞,在他看来,“布拉塞的设备很简单,他属于不会被技术所淹没的真正的艺术家。只需要灵机一动就能创造出神奇的效果。布拉塞可以非常自然地融入巴黎的夜色之中。”布拉塞和莫迪亚诺并非同时代人,但是布拉塞镜头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巴黎,让莫迪亚诺重新发现了一个逝去的时代,一个他正在寻找的时代,也是他希望让读者认识的时代。
摄影写作风格是莫迪亚诺作品中不容忽视的特征之一。在《多拉·布吕代》中,照片作为一种物证,起到了推动情节的作用。莫迪亚诺不惜用了两部分篇幅描写得到的照片,从而形成一种“散文式图片”写作手法。第一部分描绘了战前拍摄的八张照片,作家选用一般现在时客观地介绍了多拉及其父母的服饰、姿态及周围装饰,而且每张照片的文字描述之间没有连接词或过渡词。这段时期于多拉而言,是一段难能可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第二部分重点聚焦一张多拉以及她的母亲和外婆的三人合照。作家着重刻画了她们的面部表情,其中多拉“昂着头,目光冷峻,但唇边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这让她脸上有了一抹温柔的悲伤和桀骜”。作家猜测照片应拍摄于1941年或者1942年初春,彼时危机四伏,人心惶惶。作家使用“三个女人”的称呼,暗示了多拉已不再是个小孩,童年的幸福生活不再,“三个女人”也代表了三代人,甚至是千千万万那个时期的犹太人。莫迪亚诺笔下的照片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通过照片,作家真正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多拉一个人的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狗样的春天》(1993)的两位主角分别是年轻作家“我”和摄影师冉森。冉森拥有一间房间,充作摄影室或者办公室,而“我”帮他整理照片目录,眷写副本。在冉森决定离开巴黎之前的一个下午,他带“我”走在巴黎的街道上,给我指了他曾经住过的旅馆和工作过的地方。坐在长凳上时,“我”问冉森在拍什么,他答道:“我的鞋。”在咖啡馆,他突然让“我”别动,快门落在“我”手中的牛奶杯。冉森离开时,带走了三个行李箱,只留下来了一卷胶卷,都是那天下午他所拍的照片。在冉森眼中,“摄影师什么也不是,应该融入背景之中,隐匿身影,以便更好地工作,并如他所说,截取自然光线。”所谓“截取自然光线”,其具体做法是使用从美国引进的泛光灯,通过人工方法产生自然印象。
莫迪亚诺将主人公的职业设置为摄影师绝非偶然,作家曾在访谈中提到,他经常思考光线的问题,对伦勃朗的《夜巡》充满兴趣。莫迪亚诺的作品总是营造出一种半明半暗的环境和氛围,于是我们读到了没有开灯的卧室,读到了咖啡馆最里端的座位,读到了人人提心吊胆的德占时期。莫迪亚诺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中说道:“占领时期的巴黎对我而言永远都是最初的夜。没有它,我就不会出生。这个占领时期的巴黎一直纠缠着我,我的书都沉浸在它那被遮蔽的光中。”如果说布拉塞通过照片为我们呈现了过去的巴黎图景,那么莫迪亚诺则借助写作把我们带回到往昔岁月。在他的笔下,光与影相互交错,勾勒出巴黎的日与夜,这座人人深爱的永恒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