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雯:与路翎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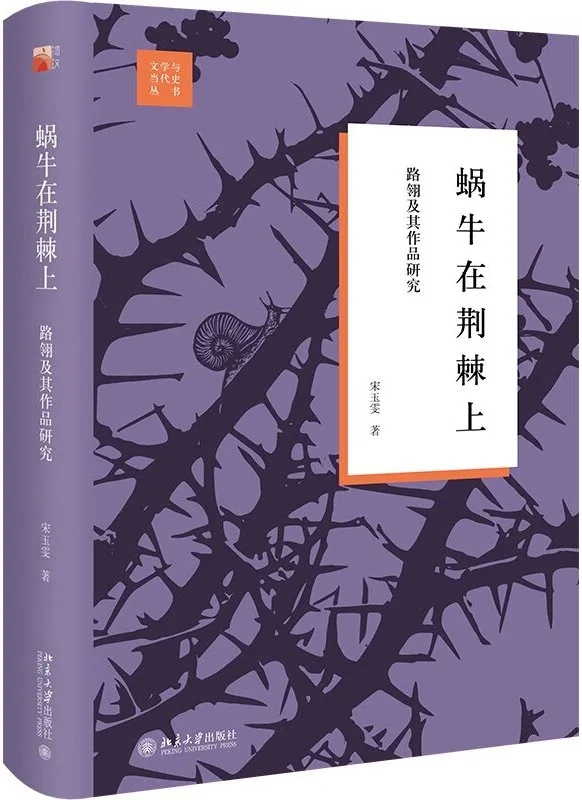
《蜗牛在荆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宋玉雯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
机遇之歌
是偶然开启了这则路翎研究故事。第一个偶然与施淑老师的一篇研究论文有关,这篇论文是发表在1976年香港《抖擞》杂志上的《历史与现实——论路翎及其小说》。[1]阅读的过程中,我隐约感觉到在批评的同时,青年施老师似乎也被路翎的作品深深吸引,评述间有种很奇特的张力,在第六、七节犀利的批判最后,以如下的话收束:
这样的小说,就像它在思想上是时代的放逐者的异端语言一样,它的形式,可能反映出某部分的时代精神现实,反映出被历史进程注定死亡的阶级在客观世界发展规律前的盲目的恐惧和战栗,因此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同样可能的是,它会被简单地盖上“恨人类、非道德、虚假……疯人的谵妄”[2]等等的验印,如果文学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某一权威和正宗思想之下的苦行僧侣的话。[3]
这篇论文里引述的每一则小说段落,都十分好看,于是我开始找路翎的作品来读,最初即是朱珩青老师编的《路翎》短篇小说集。[4]读着读着,我萌生进一步探究的兴趣,开始考虑撰写一篇期刊论文。2011年暑假,我尽可能地阅读此前的相关论著,主要是中国大陆的研究论文,其中,最让我不满的,是路翎中篇小说《蜗牛在荆棘上》所受到的批评。相对于80年代以来对于路翎40年代作品的重新评价和肯定,《蜗牛在荆棘上》从40年代到80年代,都被重要的评论家视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影的臆想之作:“不真实”。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想为路翎的创作辩护,特别是针对他一再被批评为描写“不真实”的作品。后来我才知道,“真实性”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制过程的一个重大争执点,环绕着“真实性”相关论题的不同看法,汇集成现实主义文艺内部的潜在矛盾。
第二个偶然得追溯到2009年洪子诚老师在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的一场演讲,讲题“大陆文学界的八〇年代反思”。记得那天下午,我走进交大的人社二馆,一贯是处在很累很累的状态,入门看见海报,刚好快到演讲时间,我决定放自己一马,听场演讲补充能量,就这样溜进教室找个位子坐下。此前我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认识极为有限,母亲生病,硕士班休学在家当看护期间,读过《持灯的使者》《八十年代访谈录》《七十年代》和一些朦胧诗——主要就是顾城的诗。[5]那天的演讲听得很愉快,获得了些许生活的力气。回去后,我寄了一本书给洪老师:卡尔·洛维特的《一九三三: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6]
《一九三三》是我任职台湾行人出版社期间责编的书,当时从书中择选的书腰文字是:“由于人们不断地被迫妥协,这种软弱扩大为一种普遍的人格特质,一种由于对善的荒废而来的罪行。”我直觉想,洪老师会对这本书感兴趣,可能我也想借此表达对演讲的谢意吧,于是就这样冒失地寄出。这个愚勇带来了一个惊喜,洪老师后来把这件事写进了《我的阅读史》。[7]演讲结束之后,我找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系列书《洪子诚学术作品集》[8]来读,就是当成睡前和醒来后的休闲读物(我想洪老师一定觉得很不可思议),慢慢地一本本读过去,觉得很有意思。洪老师的著述,让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相关重要论题有了初步的轮廓和认识,像是通过书本听讲,让前辈学者点拨了吧。
第三个偶然也同洪老师和彭明伟老师有关。2013年,洪老师至台湾交通大学任客座教授[9],讲《大陆当代文学生产与文学形态》。明伟老师是课程的组织者。他为大家的学习谋福利,请洪老师于课堂讲授之外,在另一个下午提供讨论时段。有一次,我正在《人间思想》的编务[10]中焦头烂额,突然发现隔壁的讨论室只有洪老师和明伟两人,迟疑了一会儿,决定丢下工作跑到隔壁,想说充个人场。我相对有较多认识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只有路翎,所以大概是以路翎作品为话题,和老师胡说了一通。散场洪老师步出讨论室时,对我说,如果你的“疯狂研究”一直做不出来,要不要试试做路翎研究。当时我就读于台湾清华大学博士班四年级,在刘人鹏教授指导下学习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的课题。考完资格考一年,博论想做“疯狂研究”,却迟迟未有具体进展。之后,同刘人鹏老师提起,刘老师觉得做具体的作家作品也很好,让我要把握机会多跟洪老师请教。洪老师很快写了千余字详实的章节规划建议信给我,这样,我便开始进入对路翎的研究。在修改专著(也就是《蜗牛在荆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以下简称《蜗牛书》)的过程中,洪老师的建议信几次重读,依然觉得十分受用。接着2014年春天,刘老师到北京和上海做移地研究,把我也拎捎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在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拼命找路翎作品的原刊。同年夏天,上海复旦大学召开“《路翎全集》发布及现代文学文献整理座谈会”和“左翼文学诗学研究前沿工作坊”,我前往发表了会议论文,并很幸运获赠《路翎全集》(上编六卷)。[11]
青春的祝福
施淑的《论端木蕻良的小说》(1972)、《历史与现实——论路翎及其小说》(1976)、《理想主义者的剪影——青年胡风》(1977)和《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1923—1932)》(1977)等文,是对“三、四〇年代中国左翼作家及文艺理论的一些试探性理解”[12]。而放回70年代台湾的历史语境,其时诸般艰难的研究和论说状态,更显为文立论的种种不易。《历史与现实》敏锐地指出:“路翎可能是第一个在作品里表现卡夫卡式的极权恐怖的中国作家”[13],将路翎小说辨识为“抗战后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的先声”[14]。该文深入路翎40年代小说中“叛逆与败北”的“劳动人民世界”,一方面肯定“这些作品是相当称职地表现出当时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新的历史现实的”[15],另一方面更检讨强调以“主观精神说明客观世界”的路翎,其创作方法和叙事意识的问题,指出路翎小说存在“个人狂热和玩味情绪”[16]的倾向,严词批评《蜗牛在荆棘上》《王兴发夫妇》部分的心理描写,认为在《两个流浪汉》和《程登富和线铺姑娘底恋爱》中,“现实世界几乎失去它作为实际行动的场所的意义,而只成了一些破碎的、乖戾的感觉和反应的赋形(incarnation)的舞台了”[17]。
不难读出《历史与现实》立足左翼的批判立场,对于现代主义流弊的高度警惕,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积淀,而对于路翎及其小说的严格度量,会否也有评论家未尝言明的自警和追求?“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所连缀指涉的文艺理论,内涵从不止及于“文艺”,也不仅止于“理论”,而更意味着“实践”“介入”和“改变”的念想,就因为奴役和不公义的存在,希望世界可以变好。相对于此(我刻意分殊二者),“现代主义”文艺同样感知着世界的不好,只是未必有同等强烈的愿望,有相信未来并投身行动的追求。而路翎成色不纯的现实主义创作,迫使二者交锋,让我们必须一同经历诸多创作者和评论家所面对的难题,持续追问:现代派能否容身于左翼文学的队伍?现实主义可否吸纳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多大程度可以、怎样的状态可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必然互不相容吗?虽然路翎不会愿意和现代派作家并列,也肯定会拒绝以现代主义的标准来肯定他的创作。
希望前述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内容,表达的是我的敬意而非自以为是。对我而言,青年施淑老师的文章,特别体现出特定时代视野下的“突围/限制”,没办法超然也不可能超然。超然需要物质基础、需要人身余裕,而不曾亲历恐怖年岁的我,难以真正体会那样的刻苦探索和挣扎。我只能想象,风雨行舟,每一下的划动,都是一次冒险,同时遭遇政治恶浪和桨身断裂的危险。这是一种“评论家的承担”,或者说,智识人的稀有品格吧。多年之后,在关于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一场基调演讲中,施老师这么说:“没有现代主义,不知何时现实主义才会出来。”[18]求索的旅途,何其修远迢遥。文学可以坦然不作为“某一权威和正宗思想之下的苦行僧侣”,后来者之所以可能“轻苦”[19],挣脱断然二分的思路,总是受惠于前人的披荆斩棘。
从博论到专著,施淑《历史与现实》着重时代思想和精神土壤的评述方式,赵园《路翎小说的形象与美感》(1984)、《未完成的探索——路翎与外国文学》(1983)和《蒋纯祖论——路翎和他的〈财主底儿女们〉》(1985)开辟“知识分子心灵史”的研究路径,从不同方面带给我深刻的启迪,也仿佛路标,让我免于歧行。针对路翎及其作品,我在《蜗牛书》中表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但两位老师的研究,对我来说始终是最好的路翎作品评论,极有个性,洋溢着评论家的个人风格,蕴有后来学院论文少见的感受性笔触。比喻来说,学院写作渐渐变得像是“盆栽”,规束于方寸之地,两位前辈学人的叙述则仿佛野地草木。而我想试着表达:学术书写可以是盆景修枝疏叶、缠线雕塑出的龙盘虎踞,也可以是在野地生长的露天峥嵘。
在《蜗牛书》里,我尝试用“落后书写”来标帜路翎创作。我的研究出发点,是全力为路翎创作辩护,这是《蜗牛书》的局限,或者说,不求持平也设限了我的论述视野,而这样的“偏颇”也因为:相较于路翎一生的创作成果,他所受到的肯定评价太不相称;相对于政治上的平反,路翎的文学尚未获得完全的平反。我希望通过对作品的研读,蠡测他和时代主潮的较量,尝试靠近路翎复杂的现实主义创作观,他的左翼世界观和立场,探索路翎“落后书写”的洞见和契机。那些干扰时代进步主调的杂音——或者借用日本政治思想史学家丸山真男的词语:“执拗的低音”[20]——让(左翼)文学的声纹更为丰富。
“攀住历史底车轮的葛藤”里面,“也有着历史力量底本身”[21]。通过一则则“落伍的故事”,路翎叩问“进步性”的内涵,结构着革命另一面的真实。路翎不认为革命能一蹴而就,他一生艰难的文学溯洄,正说明了革命之路的道阻且跻。阅读路翎及其作品的过程,糁入许多个人生活的时代感受,这是《蜗牛书》无可回避的时代刻痕。从40年代到90年代,承受长久磨难的路翎,通过创作实践一再表述着“相信人民”,在这个诸神远离不再有信、追求深思多疑的“个人时代”,如此的念想格外动人,这也是一种文学的力量吧。
之所以絮叨了这许多前世今生,也是想试着表达,“偶然”其实是研究和写作的一部分,论述的生产过程,或多或少都唱着机遇之歌。更且多数时候,研究和写作看似很“个人”,通常也归功于个人,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任何研究都不可能独力完成,恒常是“众志成城”才可能有些许推进。诚挚希望大家一起来阅读路翎的作品,也希望《蜗牛书》能充当路翎创作和读者、研究者之间的桥梁。这样一个终生努力创作、因创作获罪的作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不可取替的文学情感。路翎的创作或许总是不合时宜,但我相信他的作品,无论在怎样的历史时刻阅读,都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这是路翎通过创作所给予我们的青春的祝福。
感谢诸多前辈师友的指点和协助,特别是路翎研究的前行者朱珩青老师和张业松老师。感谢吕正惠老师、陈光兴老师、苏敏逸老师和贺桂梅老师在关键时刻的批评和肯定,驱策我继续前进。对于指导教授洪子诚老师和刘人鹏老师,以及施淑老师的感激,不在话下,是三位老师让我明白了专心致志的道理,还有书斋知识分子的力量。研究期间有赖张婧、温思晨、罗雅琳、许晓迪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何吉贤老师、北京师范大学的仝卫敏老师帮忙搜集研究材料,陈冉涌和吴宝林协助核实多笔路翎著作初刊本和书目资料,谨致谢忱。
感谢黄子平老师惠赐书序,让这本专著有个让人期待的开始。《蜗牛书》能通过北大出版社与大陆读者相遇,是极大的幸运,过程中黄维政老师细致的勘误和编校工夫,黄敏劼老师的支持和建议,衷心感谢!也必须感谢个人目前任职的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以及台湾阳明交通大学[22]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和台湾清华大学亚太/文化研究中心提供研究支持。陈筱茵在繁体版《蜗牛书》成形过程中的讨论与鞭策,许霖协助简体版书稿的文字修订,诚挚感谢。本书部分章节内容曾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和《现代中文学刊》发表,亦在此一并致谢。当然,书中所有的疏失和阙漏,都是我自己的责任。
注释:
[1]施淑,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文章原载1976年5月《抖擞》(香港)杂志。初收入施淑《理想主义者的剪影》(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1990年),后收入施淑《历史与现实:两岸文学论集(二)》(台北:人间出版社,2012年)以及施淑《两岸:现当代文学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此处有原注40,谓引自布洛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反对艺术中的自然主义》,金诗伯、吴富恒译,载《文学理论学习小译丛》第一辑第6分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第2页。原注文中并谓:“这是苏联文学评论批评西方现代文学,特别是形式主义的作品所加的卷标。”
[3]施淑:《历史与现实——论路翎及其小说》,载《理想主义者的剪影》,第156页。
[4]朱珩青编:《路翎》,香港:三联书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5]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北岛、李陀编:《七十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刘禾编:《持灯的使者》,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6][德]卡尔·洛维特:《一九三三: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区立远译,台北:行人出版社,2007年。
[7] 洪子诚:《我的阅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另有《阅读经验》(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和《文学的阅读》(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年)。
[8]《洪子诚学术作品集》共8册,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当代文学的概念》和《中国当代新诗史》。后来陆续也读了洪老师的《文学与历史叙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学习对诗说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以及《材料与注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和《读作品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
[9]洪子诚老师曾三度至台湾讲学:2009年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台湾文学研究所;2013年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2014年8月至2015年2月,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10]2013年2月至2015年9月,我在台湾交通大学亚太/文化研究室工读,参与《人间思想》(台北:人间出版社)的编务。
[11]“《路翎全集》发布及现代文学文献整理座谈会”,2014年6月6日,当天与会参与“世界视野中的左翼文学”座谈会,发言稿《小地方小政治的小阅读》;“左翼文学诗学研究前沿工作坊”,2014年6月7—8日,发表会议论文《解放了的大地上的“烂渣渣”——路翎四十年代的小说》之外,参与6月8日最后一场的圆桌论坛“左翼文学的诗学研究:问题与可能”,发言稿《戴着镣铐跳舞》。
[12]施淑:《理想主义者的剪影》后记,第269页。写于1990年4月。
[13]施淑:《历史与现实——论路翎及其小说》,载《理想主义者的剪影》,第145页。“作品”系指《财主底儿女们》。
[14]同上书,第152页。
[15]同上书,第181页。
[16]同上书,第151页。
[17]同上书,第156页。
[18]“文学论战与记忆政治:亚际视野”研讨会,2019年9月7—8日,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19]台湾有俗谚:“吃好做轻苦。”“轻苦”大概接近“轻松”之意。
[20]详参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该书简体字版于201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1]路翎:《〈求爱〉后记》,载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第206页。此后记写于1946年7月20日南京。
[22]2021年,台湾阳明大学与台湾交通大学合并为台湾阳明交通大学。
(本文选自《蜗牛在荆棘上:路翎及其作品研究》,宋玉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转载自“文艺批评”微信公众号。)


